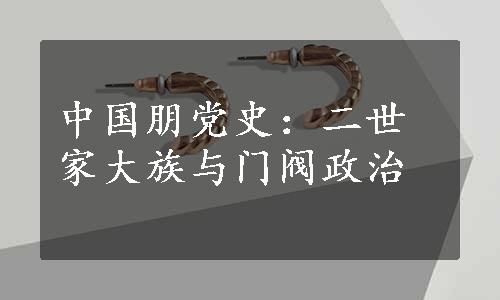
两晋南北朝以来,选拔官吏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实行九品中正制后,选官用人只看门第高低,不问实际才能,以致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85]的局面。士族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士族与庶族之间有着严格的界限。高级官员大都由高门士族担任,他们凭借世资,轻取公卿;高门的子弟,年纪很轻就可做职闲俸厚的官,并且升迁也很快。当时第一流士族“崔卢王谢子弟,生发未燥,已拜列侯;身未离襁褓,业被冠戴”。[86]而寒门庶族,有才华者到30岁才能以小吏试用。东晋时王沈,“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沉浮,为时豪所抑”,[87]即是一例。由于“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故寒门庶族要取得政治上的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趋炎附势,投靠权门,自称门生,以求提携。这里的门生,已经不是指传授学业的师生关系,而是“大抵入门必具资奉,免徭役,供驱策,主家吹嘘,或可入仕”的门徒之类了。这些门徒由于豪门大族的推荐和庇护,在仕途上有时也能捷足先登。比如,南齐时,王琨为吏部郎,“吏曹选局,贵要多所属请,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为用两门生”。[88]门生弟子与豪门士族之间,由私人恩遇结合在一起。他们在仕途上互为扶植,生死相依,往往名为门生,私为臣子。魏晋时期的门户观念,人身依附,使世家大族的势力急剧膨胀起来。门阀士族成了一个垄断政权,广占田地,拥有大批门生故吏、家兵部曲,独霸儒学阵地和世代簪缨、冠冕不绝的特权阶层。
由于高门士族长久地把持政权,就为朋党势力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土壤。魏晋士族的基础,就是东汉以来的大姓名士,这些名士大都经历了东汉党锢之祸的浩劫,而魏晋士族又是门阀的主体,所以在事实上,魏晋以来的门阀士族与东汉后期的党争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魏晋门阀士族就是东汉末年党争的一个结果。此种状况,一直延续至隋唐时期,唐人韦云起言:“今朝廷多山东人,自作门户,附下罔上,为朋党。不抑其端,必乱政。”[89]门阀政治更多地表现为高门阀阅家族的地望及血统,所以,以地缘、血缘关系与人身依附关系相结合的士大夫集团是魏晋隋唐时期朋党的主要特征,只要门阀政治的格局不变,在尚未出现军阀混战的形势下,朋党的产生和党争是不可避免的。
三国时期,江南地区吴姓士族势力十分强盛,孙吴政权之所以能长久地与北方曹魏抗衡,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吴姓士族,吴姓士族一般都在孙吴政权中任重要官职。在大族控制选举权的情况下,孙吴选官用人实际上与九品中正制无异,江东大族把持了政权。葛洪在《抱朴子·吴失》篇中指出,吴国的选官制度是“贡举以厚货者在前,官人以党,强者为右”。这就清楚地表明,只有世家大族结成的朋党中人才能在孙吴政权中担任重要官职。由于在江南大族中顾、陆、朱、张四姓势力为最强,所以孙吴的官场就成了吴郡四姓的天下,“公族子弟及吴四姓多出仕郡,郡吏常以千数”,[90]他们成了孙吴政权的主要支柱。
吴四姓中,陆氏家族势力最盛,陆逊为孙吴重臣,孙权称帝后,拜他为上大将军,“辅太子,并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军国”。吴国阃之外的军国大事,实际上都由陆逊裁决,其职责极为重大。顾雍死后,陆逊又代其为丞相,“总司三事,以训群僚”,[91]可谓集孙吴军政大权于一身。陆逊卒后,陆氏族人的权力并无丝毫削弱。陆抗以建武校尉“领逊众五千人”,以后稳步上升。孙皓在位时,官拜大司马、荆州牧,手中权柄,已不亚于乃父陆逊。陆凯是陆逊族子,孙皓初立时,任镇西大将军,后迁至左丞相。《世说新语·规箴》载:“孙皓问丞相陆凯曰:‘卿一宗在朝有几人。’陆曰:‘二相,五侯,将军十余人。’皓曰:‘盛哉。’”由此可见,陆逊一门长盛不衰,有吴一朝始终是执掌军政的重臣,为吴国历代君主所宠信。
著姓望族势力的发展,使孙吴群臣在政治上朋比结党,争夺权力。孙权立太子孙和之后,鲁王孙霸觊觎储君之位,围绕着孙权继承人问题,吴国“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92]导致了“二宫党争”的局面。
士族发展的高峰是在东晋王朝。东晋时期形成了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几家北方士族轮流执政的局面。东晋皇帝实际上没有多少权力,史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93]东晋王朝是士族政权,世家大族力量之强,成了与皇权相抗衡的离心力量。从东晋第一大族——王氏集团与东晋皇帝的关系就可见一斑。早在司马睿即位,建立东晋政权之时,因顾虑王氏声望之高,实力之强,故几次邀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虽然谦让,但实际上已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导在东晋政权中有着超出一般臣僚的特殊地位,元帝称他为“仲父”。明帝时,他受遗诏辅政,“依陈群辅魏故事”,后来又辅成帝。成帝“见王导,每拜,又尝与导书手诏,则云:‘惶恐言’,中书作诏,则曰:‘敬问’,于是以为定制。自后元正,导入,帝犹为之兴焉。”[94]居然在礼节上颠倒了君臣关系。(www.daowen.com)
王导虽然有异乎寻常的人臣特殊地位,但并无篡位之心,故他与元帝司马睿君臣间还能相安无事,而其堂兄王敦则野心勃勃,欲变王、马共天下为王氏一家之天下。当然司马睿也不甘心将政权拱手让给王氏集团,他逐步部署自己的亲信去占据军政要害部门,力图抑制王氏朋党势力。然而王氏集团已经尾大不掉,势强难制,结果终于爆发了王敦之乱,当王氏集团完全控制东晋政权时,司马睿无计可施,遂“忧愤成疾”而死。
在中国帝制社会的历史上,魏晋南北朝的君权相对削弱。但在这四百年中,又以东晋君权为最弱。曹魏、西晋及南北朝时期,尽管发生过权臣跋扈,甚至逼迫君主禅位之事,但毕竟没有出现君与臣共天下的局面,唯有东晋百余年,始终是君与门阀士族共天下。出现“君弱臣强”的局面,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士族集团势力太强的缘故。士族集团势力的构成主要有三个层次:其一,由若干个同姓家庭通过血缘关系构成宗族。其二,各异姓宗族之间再通过同乡、婚姻、师生、家兵部曲、门生故吏关系构成集团。其三,也是最重要的,门阀士族有九品中正制作为其世代高官、把持政权的政治保障,从而为其形成朋党势力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
总之,两晋南北朝的门阀政治是一种排他性很强的政权统治,其主要表现就是“举贤不出士族”,以及官位权力世袭制造成的“公门有公,卿门有卿”。[95]东晋大族王氏集团无非是利用了这一制度才能长期执掌政权,与司马氏共天下。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下,王氏士族几乎囊括了东晋政权中的一切重要官职。在王氏集团中,王导为尚书令、司徒,执掌朝政;王敦任大将军,雄踞上游,专制军权;王含为征东将军,都督扬州江西诸军事;王舒为荆州刺史,王彬为江州刺史,王邃为徐州刺史,王澄为湘州刺史,王廙又代陶侃为荆州刺史,而其他王氏子弟都“布列显要”,担任清要官职。王敦又用沈充、钱凤为谋主,以诸葛瑶、邓岳、周抚、李恒、谢雍为爪牙。史载“王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96]元帝时,琅邪王家达到了权势的高峰,王氏在朝中树立党羽,公卿州牧都是王氏族人或者与王家相关的人。由此可见,王氏集团的势力实际上已超过皇帝司马氏,已完全操纵了东晋政权。
士族势力的极度扩张必然打破统治阶级各派政治力量的平衡,引起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由于士族千方百计打击、排挤庶族,遂引起寒门庶族的强烈不满。在“士庶天隔”的等级制度下,寒门庶族和高门望族的矛盾极其尖锐。士庶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围绕选官制度展开的。魏晋以降,由于选官用人唯凭门资,不问才能,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庶族寒门的仕进之路。为了进入仕途,分享权力,庶族反对士族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南朝宋齐梁陈,庶族寒门开始抬头,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机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8“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云:“宋齐梁陈诸君,则无论贤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权于大臣。而其时高门大族,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虽然寒族势力有所上升,但由于九品中正制始终是为门阀政治服务的工具,庶族反对士族的斗争并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田余庆在其《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指出:“如果说西晋自武帝以来,士族名士是司马氏皇权的装饰品,那么东晋司马氏皇权则是门阀士族政治的装饰品;西晋尚属皇权政治,东晋则已演变为门阀政治。东晋皇权既然从属于门阀政治,皇帝也就只是士族利用的工具而非士族效忠的对象,‘贞臣’自然是少而又少了。史家每诟病《晋书·忠义传》,言其人物事迹多有于晋不忠不义者,原委之一,即在于此……士族权臣可以更易,而‘主弱臣强’依旧。当琅邪王氏以后依次出现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权臣的时候,仍然是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由此可见,王与马的结合所开启的江东政局,奠定了东晋一朝政局的基础,影响是深远的。至于琅邪王氏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终于不能篡天下,这应当从门阀士族之间彼此牵制和南北民族矛盾这两方面求得解释,而不能只从权臣个人忠奸求之。”[97]田余庆总结的这个观点对学界继续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极具启发意义。其实,不仅琅邪王氏只能与司马氏“共天下”,而不能篡天下,其他大族掌权之后,也只能与司马共天下。出自谯郡龙亢的桓氏至桓温时已掌控了东晋朝政,篡晋积谋甚久,但终未成功,不是军事力量不足,不是皇室反抗,而是几家头等大族作梗。桓温子桓玄不识时务,亡晋建楚,自立为帝,旋即失败。这就充分证明了东晋士族集团力量的强大(当然还有晋末寒族势力的兴起),谁突破“共天下”的这道红线,就必然身败名裂。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