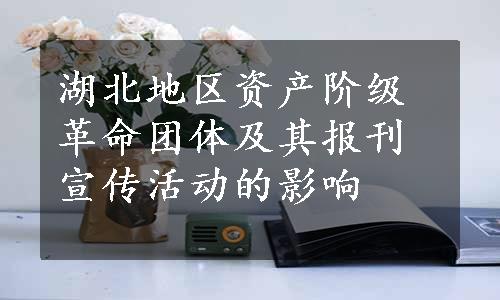
第十节 湖北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和它们的报刊宣传活动
以武昌、汉口为主的湖北地区,是这一时期国内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的又一个中心。
湖北地区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早在1903年前后就开始了。1904年起,革命党人先后在武昌、汉口两地建立了科学补习所、日知会、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一大批革命小团体,这些小团体后来都并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领导和影响下,为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和其他省份的情况不同,湖北地区的革命党人并不急于发难,而是从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入手,通过办学、充当路工和投身行伍,在清朝政府的新军部队中充当士兵和下级军官等方式,联系群众,积蓄力量,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和这相配合,他们在武昌、黄州等地创办了昌明公司、乐群印刷社、教育图书社、鸠译书会等出版机关,秘密翻印了《猛回头》、《警世钟》、《黄帝魂》等大量的革命小册子,在新军士兵、筑路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免费散发。此外,他们还在武昌创办了圣公会阅报社,在黄岗创办了坪江阅报社,在汉川创办了汉川阅报社,利用教堂、祠堂为掩护,陈列从外地秘密运送来的革命报刊出版物,供众阅览,播撒革命的种子。这是他们早期活动的情况,当时,他们自己还没有创办报纸,但是,已经十分重视革命的宣传工作了。
1905年以后,湖北当地的革命党人开始自己办报,在1905至1911这六年内,先后办有《楚报》、《武昌白话报》、《湖北日报》、《商务日报》、《雄风报》、《大江报》、《政学日报》、《夏报》、《鄂报》等近十家报纸(注一),全部集中在武昌、汉口。此外,同盟会本部也有在武昌、汉口办报的计划,曾经派遣陈其美到武昌、汉口进行筹备,社址选定在汉口英租界,报名也已确定为《大陆新闻》,一应设备都已购置停当,正在准备发刊之际,突然遭到清吏的破坏,才被迫中止,没有办成(注二)。已经创办起来的几家报纸当中——
《楚报》 创刊于1905年。创办人冯特民,开始是科学补习所的所员,后来是日知会的会员,日知会的“章则文告”,“多出其手”。主办《楚报》期间,他用鲜民的笔名,“纵论鄂省政治,不避嫌疑”(欧阳瑞骅《冯特民传》),并曾在报纸上披露了鄂督张之洞与香港政府秘密签订的赎回粤汉路借款一百一十万镑合同的全文,配发评论,对张进行掊击,因此遭到查禁,受到拘留处分(注三)。协助冯担任主笔的陆费逵,也是日知会的会员。
《武昌白话报》 创刊于1908年。主编陈少武,是军队同盟会的会员。先一年被捕的同盟会会员李亚东,经常以上逸的笔名在狱中为该报撰稿。出版后,“传递于军学两界,收效甚宏”(《中国革命二十六年组织史》164 页),不久即停。
《湖北日报》 创刊于1908年夏。创办人郑江灏,号南溪,襄阳人,是董必武在两湖师范的同班同学,1907年留学日本,加入共进会,被推为参议部长,1908年回国,在汉口一码头创办该报。协助他办报的李介廉、王柏森、董祖椿、杨宪武等,也都是共进会员。1909年春,该报以刊载漫画和评论对鄂督陈夔龙进行嘲讽,被后者封禁(注四)。
《雄风报》 创刊于1910年春。创办人杨玉如,字藻香,沔阳人,共进会员,经常以古复子的笔名,在报上发文章,“鼓吹革命”(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24页)。《雄风报》是一个小型日报,只出版了几个月,即因经费困难停刊。
《政学日报》 创刊于1911年春。是郑江灏继《湖北日报》之后创办的又一份报纸,协助他办报的有他的同学向炎生。创刊不久,即以所刊漫画嘲讽湖北新军统制张彪被封(注五)。
《夏报》 1911年前后出版。创办人高汉声。出版不久即被封(注六)。
《鄂报》 1911年前后出版。创办人汪康平。只出五天即被查封(注七)。
这些报纸大多是活跃在武汉三镇的湖北革命党人,以个人名义,纠集同志,自发地创办起来的。它们的主编人绝大多数都是革命团体的成员,但是,它们还不是这些团体的正式机关报纸。在宣传上,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多数报纸也还“未能畅所欲言”(注八)。
影响较大,较有特色的是《商务日报》和《大江报》。
《商务日报》 创刊于1909年10月8日,社址在汉口英租界大马路致祥里8号,原是一份普通的民办报纸。创刊不久,原主人病故,宣告辍业,由革命知识分子日知会员宛思演、詹大悲、温楚珩等集资接办,宛任总经理,詹任总编辑,成为一份宣传革命的报纸。这以后,经过串联,和新成立的革命团体群治学社建立了联系,所有经费统由该社在社员缴纳的会费中拨付,成为该社的言论机关。协助宛、詹等人担任编辑和发行工作的刘尧澄、蒋翊武、李抱良(六如)、何海鸣、查光佛、杨玉鹏、梅宝玑等,都是群治学社的社员,其中除查、梅两人外,都是新军第二十一协四十一标各营的下级士兵,是投身新军从事秘密反满活动的革命知识分子。1910年夏,以报道湖南饥民抢米事件和支持反对借款筑路运动,被清政府串通租界当局查封,是湖北革命团体主办的第一个正式机关报(注九)。
《大江报》 创刊于1911年1月3日,社址在汉口新马路52号(注十),是湖北革命团体主办的第二个正式机关报。
这个报纸初创时原名《大江白话报》,三日出一小张,后删去“白话”两字,迳称《大江报》,日出两大张,由同盟会员胡石庵所办的大成印刷公司负责承印。首任经理是胡为霖。不久,胡退出,改由詹大悲兼任。编辑部的主要负责人是詹大悲和何海鸣。
詹大悲 (1887—1927) 名瀚,又名培瀚,号质存,大悲是他的笔名,湖北蕲春人。黄州府立中学学生。毕业后,即参加湖北地区的民主革命活动,是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主干。在这些团体中,他主要负责宣传工作,先后担任过《商务日报》、《大江报》等报的编辑、主笔,是辛亥革命时期湖北地区革命宣传战线上的一员主将。武昌起义后,他一度担任过鄂军军政府汉口分府的主任,嗣被选为湖北省议会的议长。以后,又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任孙中山在广州的大本营的宣传员和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政府的湖北财政厅长等职,1927年12月17日在武汉和李汉俊同时被桂系军阀枪杀。在《大江报》工作时期,他是这个报纸的总经理兼总编辑,“语言文章,犀利隽妙”,最后又因《大江报》事件锒铛入狱,以此名噪一时。
何海鸣 (1890—194?) ,原名时俊,笔名海、海鸣、一雁、求幸福斋主等,湖南衡阳人。青年时期投入新军当兵,在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一营前队充当副目,并参加了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和文学社的活动。《商务日报》创刊,他应邀担任编辑,开始了办报生涯。此后,他相继在汉口《大江报》、上海《民权报》、北京《又新日报》等报担任编辑主笔,同时为沪、汉的其他几家报纸撰稿,开始只写评论,后来除评论外,也写一些哀感顽艳的言情小说,成为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的一员健将。何海鸣青年时代是倾向民主革命的,写过一些激昂慷慨鼓吹革命的文章。民国以后,渐入颓唐,先是附袁,继而附逆,终于沦为文化汉奸,潦倒而死。在《大江报》工作时期,他担任了这个报纸的副总编辑,是报纸的“半个主体”,报上的论说和时评,由他和詹大悲“轮流包办”,最后又和詹一道,同样为《大江报》事件入狱,为此,“小小出了一点名”(注十一)。
协助詹、何两人参加过一个时期的编撰工作的还有查光佛、宛思演、梅宝玑、黄侃、温楚珩、胡瑛、凌大同等。其中有同盟会员,有共进会员,有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的社员,不少人还参加过《商务日报》的工作。
《大江报》创刊不久,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在振武学社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文学社,从事革命发动工作。詹大悲是文学社的筹备人和社章起草人之一。起草好的社章首先在《大江报》上发表,筹建文学社的几次有新军各标士兵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也是以《大江报》的名义召集的。在文学社筹建的过程中,《大江报》曾经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在武昌黄鹤楼举行集会,宣告成立,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詹大悲被选为该社文书部部长,《大江报》也被确定为文学社的正式机关报。在《大江报》被封以前,这个报纸不仅是文学社的重要言论机关,也是文学社的重要联络机关。文学社与新军士兵和其他革命团体的联系,都通过《大江报》进行,文学社领导人和筹备中的中部同盟会负责人的几次会谈,就是在《大江报》举行的。
文学社成立初期的主要工作之一,“为利用报馆宣传革命”(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刊《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124页)。《大江报》在这方面发挥了它的特殊作用。
《大江报》出版的时期,正是昏谬庸暗的清朝政府尸居余气、苟延残喘,而各阶层人民的罢工、罢市、抗税、抗捐、抢米斗争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席卷全国的时候。《大江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反映了处在“上山”阶段的那一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面貌,歌颂叛逆,追求理想,对压迫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及清朝封建政府和一切腐朽反动的事物,发动了大胆的攻击。
1911年1月21日,汉口发生英国巡捕无故殴毙人力车工人吴一狗事件。次日,汉口人力车工人千余人,聚集在汉口英租界捕房门前,向英方提出抗议,又被英国驻军枪杀十余人、重伤数十人。两次血案引起了武汉人民的极大愤慨。《大江报》在事件发生后,立即以头号字标题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消息,并以《洋大人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为题,发表社论,抗议英帝国主义者的血腥暴行,支持武汉人民的斗争。当时,清朝的司法机关在英方的压力下,曾经宣布吴尸并无致命伤痕,妄图为行凶者开脱,并威胁《大江报》“勿言车夫有丝毫伤痕”。《大江报》公布了清朝司法机关对该报进行威胁的经过,拒绝了后者的乱命,并在评论中暗示读者:媚外残民的清朝政府不足恃,只有推翻这一政府,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缚。这是《大江报》创刊伊始所进行的第一个宣传战役。
在这以后,《大江报》继续集中力量和清朝政府作斗争,进行过以下几方面的宣传:
一、连续报道广州将军孚琦和凤山被刺事件,悼念死难烈士,赞扬他们的英勇献身精神。
二、支持两湖地区的保路运动,反对清廷借“国有”名义,把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鼓动社会,团结抵抗”(1911年8月18日《申报》)。对力主把“商办”铁路“收归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奉派接收“商办”铁路的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和参与出卖路权活动的洋务大员郑孝胥等,都进行了强烈的讽刺和谴责。端方南下道经湖北的那几天,几乎“无日不作讥讽之评论”(1911年8月10日《时报》)以刺之。
三、揭发清朝地方官员阴鸷狡险妄图镇压革命的种种罪行。湖北藩司余诚格曾命度支公所以高息秘借洋款五十万元,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大江报》设法觅得秘密借款合同的副本,全文在报上披露,舆论大哗,使余诚格极为狼狈。
《大江报》的这些宣传,振聋发聩,不畏强暴,改变了内地报纸在清朝政府的高压下不敢大胆放言的状况,引起了社会上的瞩目。
文学社的基础在新军。《大江报》的不少评论和报道是面向新军,直接以新军的下级士兵为对象的。
它经常站在新军下级士兵的立场,同情他们的遭遇,反映他们的疾苦,诉说他们的不平。它大胆地揭发了新军长官“视兵士如奴隶,动辄以鞭挞从事”;镇统“吞蚀军款百万有奇”;标统、协统“花天酒地,广置姬妾”等事实(注十二);并点名指责新军第二十九标标统李襄邻克扣军饷;维护了下级士兵的利益,受到了他们的欢迎。
当时的新军绝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知识分子,多数人“粗通文字”,较少旧式绿营军队的兵痞习气,有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基础。为了争取这一部分力量,《大江报》在文学社的领导下,很重视在他们当中的工作。它在武汉地区新军的每个基层单位,几乎都设有分销处(注十三),除每营赠送免费义务报一份外,还在士兵中发展个人订户。为了加强和新军士兵们的联系,它鼓励他们投稿,“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即登载”(注十四)。同时在新军中培养了一批特约记者、特约编辑和特约通讯员。如新军第三十标前队士兵张挞伐,就是它的特约记者(注十五);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马队士兵陈孝芬在调至陆军特别小学当学兵的一段时期里,“每晚必到(《大江报》)报馆去一趟,编编报,作作短评”(注十六)。正因为这样,《大江报》和新军士兵的关系十分密切,士兵们把这个报纸看作是自己的报纸,有什么事情都愿意找它商量,“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注十七)。当报社经济发生困难的时候,“军中同志月出资少许,由各标营代表汇送报社,以助经费”(注十八)。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宣传活动当中,像《大江报》这样能够和新军士兵建立起这么亲密关系的报纸,是不多见的。
《大江报》在湖北新军中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它的宣传教育影响下,不少新军下级士兵都愿意和它“共图革命”(注十九)。文学社在新军中发展得很快。1911年1月文学社初成立的时候,在新军中只有八百多个社员,半年以后就发展到三千多人,基层组织遍及于第二十九标、三十标、三十一标、四十一标马、炮、工各营队。到了武昌起义的前夜,湖北新军一万五千士兵当中,已经有五千人,即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加入了各革命团体,成为在湖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的一支很大的力量。
然而,最使《大江报》享有盛名的还是它所刊载的两篇著名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和《亡中国者和平也》。以前一篇的影响为尤大。
《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是一篇二百字左右的短评(注二十),刊载于1911年7月26日《大江报》的“时评”栏。原文如下:(www.daowen.com)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然自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钜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国之健儿乎!和平已无可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所谓的“大乱”,其实是“革命”的同义语。短评的作者告诉读者: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媚外的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是致中国于“死境”的“膏肓之疾”;立宪党人所鼓吹的和平改革道路绝对行不通;中国需要有一个“极大之震动”和“极烈之改革”;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向爱国的“志士”和“健儿”们发出了踊跃献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号召。对所谓的“无规则”的“大乱”,这篇短评虽然有“深创钜痛”和“至于绝地”之惧,暴露了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既要人民支持,又害怕人民起来革命的矛盾心理,但是整个基调是奋发的,对“大乱”即革命是抱着热烈颂扬的态度的。在写作上,这篇文章由沉痛悲愤而激越昂扬,质朴无华,一气呵成,别有一种感人的魅力。尤其突出的是它的标题,它奇崛豪壮,鲜明生动,毫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四平八稳,给这篇短评增添了不少颜色。这是这篇短评刚一发表就脍炙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篇短评的作者是黄侃。
黄 侃 (1886—1935)原名乔馨,字梅君,又字季刚,湖北蕲春人,日知会员、同盟会员。他青年时代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学习,以参加反清革命活动被除名,转赴日本留学,并师事章太炎,曾经以病蝉、运甓、乔鼐等笔名为《民报》、《国粹学报》、《民声日报》等报撰稿,并协助章太炎担任过《民报》的编辑工作,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报刊宣传活动的积极参加者。辛亥革命后,他潜心学术,不问政治,专任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以迄去世,像章太炎一样用自己砌的一道墙,把自己和世界隔开了。这篇短评是他在《大江报》担任特约撰述时写的,发表时署名奇谈。当时,他刚从日本回国不久,来到武汉,受到詹大悲等人的欢迎,请他写稿,他乘兴命笔,一挥而就,经詹大悲编定后,第二天就见了报。这篇轰动一时的短文就是这样产生的(注二十一)。
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并称于时的另一篇短评《亡中国者和平也》,署名“海”,是何海鸣写的,发表于1911年7月17日的《大江报》时评栏,先于《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十天。这篇短评也鼓吹“大乱”,但重点在驳斥保皇和立宪派分子企图用请愿等“和平”手段来抵制革命的反动主张。短评愤激地斥责清廷颁布的宪法大纲,为“摧抑民气之怪物”,指出:一切企图用“伏阙上书”以及“不承认,不纳税”等手段促使清廷改革的做法,都是愚蠢的,行不通的,“和平”是“亡中国”之道,只有革命才能拯救中国。
当时,各地人民的抗捐、抢米、争路斗争,正在激烈进行,推翻封建专制政府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正在积极准备,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火药气味。《大江报》的这两篇富于鼓动性文章的发表,鼓舞了革命者的斗志,不啻在一触即发的火药堆中投入了一剂强烈的催化剂,不能不使清朝政府感到极大的震惊。
湖北地区的清朝官吏对《大江报》的工作人员早就有所怀疑(注二十二),对这份敢于揭他们的疮疤,批他们的逆鳞的报纸,更是畏之如虎,恨之入骨,务以去之为快。《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等两文发表后,他们决心对这个报纸施加毒手。1911年8月1日,是他们下手的日子,这一天晚上,汉口巡警二区区长覃兆率领所部巡警数十人,高执巡警灯笼,如临大敌地包围了《大江报》社,勒令停刊,并逮捕了詹大悲。何海鸣当时不在报社,闻讯自行投案。经过一个时期的审讯后,詹、何两人被判十八个月的有期徒刑,《大江报》也以“言论激烈,语意嚣张”,和“淆乱治体,扰害治安”等罪名被封。
事件发生后, 《大江报》立即向全国各报馆发出了呼吁的通电(注二十三)。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纷起对清廷摧残言论的暴行进行指责。汉口各人民团体和汉口报界公会都曾分别集会,向清政府提出抗议。参加革命团体的新军士兵和同情革命的各阶层爱国人士,也纷纷对《大江报》表示声援。被封后的《大江报》门口贴满了他们所写的慰问纸条和哭吊的短文。湖北官方原来打算把詹、何二人“从重置典”,慑于舆情,才不得不从轻判刑结案。
《大江报》的寿命不长,只出版了半年多时间,但是,它给读者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它的那些发奸 伏的新闻报道,神旺气壮的时事评论,震电惊雷般动人心弦的文字标题,都久久地铭刻在读者的心中,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使他们的革命激情达于沸点。它被封以后,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伏的新闻报道,神旺气壮的时事评论,震电惊雷般动人心弦的文字标题,都久久地铭刻在读者的心中,深深地打动了他们,使他们的革命激情达于沸点。它被封以后,不到三个月,武昌起义就爆发了。
从1905到1911年,湖北地区的各革命团体开展了近六年的报刊宣传活动。这期间,革命的组织活动,时有涨落,而革命的宣传活动,却从未衰减。两个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在不少方面存在着矛盾,但在宣传战线上,还是能够紧密合作,互相支援的。除了自己办报外,不少革命党人如胡祖舜、朱峙三、蔡良臣等,还用投稿的方式,利用在当地出版的一些老牌“商业”报纸作为阵地,进行宣传,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为1911年的武昌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湖北地区的革命发动工作相对地说比其他地区要好,报刊宣传工作在这方面是有贡献的。
但是,湖北的这些革命团体,从科学补习社到文学社,都从来没有制定出一个完整的民主革命的纲领。科学补习社的会员们,“仅心记革命排满而已”;群治学社也只是含糊地提出了“研究学识,讲求自治,促睡狮之猛醒,挽狂澜于既倒”的主张;共进会算是接受了同盟会的纲领,但却错误地把“平均地权”,擅改为“平均人权”;文学社则是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才和同盟会挂上钩的,因此不少社员对同盟会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除了革命排满之外,并不十分了解。这种情况在它们的报刊宣传中也自然地有所反映,主要表现为:过多地在种族复仇和反满革命的问题上做文章,不大注意完整的民主主义纲领的深入探讨,系统的理论宣传尤其不足。这是这一时期革命派报刊宣传上的通病,只是在湖北地区的这些报刊当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注一):据秋虫《武汉新闻史》及贡少芹等所编《中西报万号纪念刊》,这一时期在武汉地区出版的报纸还有《汉报》、《公论报》、《中西报》、《公论新报》、《繁华报》、《汉口消闲录》、《扬子江日报》、《趣报》、《现世报》、《汉江日报》等。除《中西报》、《公论报》是所谓老牌“商业”报纸外,其余的多数是以刊载行情、戏目、诗词为主的小报,或专登花事消息的“花报”。
(注二):据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217页引《陈其美传》。
(注三):见1911年8月9日《时报》。
(注四):《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164页注七引陈少武语云:“1909年新春,《湖北日报》刊有插画一则,画一龙伏于石上,题词云:‘这石龙,真无用,低头伏处南山洞;镇日高拱不动,徒劳地方香烟奉。奉有王爷撑腰也是空,勿怪事事由人弄’。陈夔龙极为恼怒。接着《湖北日报》又载《中国报纸于官场有特别之利益》一文,陈更愤恨。因陈妻拜庆亲王为干父,陈是借庆亲王奥援,做到督抚的。插画、题词、论文,皆挑了陈氏之眼。适金鼎(湖北巡警道)来见,陈向金鼎说:‘湖北日报讨厌得很’!金为迎合意旨,即将《湖北日报》封闭,并逮捕经理郑南溪。”
(注五):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记《政学日报》以漫画嘲讽张彪事云:“其骂张彪也,画一猫似虎形,刊之,题云:‘似虎非虎,似彪非彪,不文不武,怪物一条’。民众争购阅之。”(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146页)又据该书编者注称:“谢楚珩先生谈:其下尚有四句曰‘因牝而食,与獐同槽,恃洞护身,为国之妖’。又‘不文不武’一作‘不伦不类’。”
(注六)据秋虫《武汉新闻史》及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前书谓《夏报》系“革命党人”报纸,朱文谓《夏报》“亦同情革命者”。
(注七):据朱峙三1962年3月24日告本书作者。
(注八):这是朱峙三在《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一文中对《雄风报》的评价,对这一时期出版的其他革命报刊也同样适用。
(注九):据《辛亥革命》第五辑《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之历史》;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10页;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37页《潘怡如自传》。
(注十):据1911年1月17日上海《民立报》所刊《大江报》出版广告。又据1911年8月18日上海《申报》报道,该报社址在汉口苗家码头巷。后者可能是该报后期的社址。
(注十一):引文见求幸福斋主《民元报坛识小录》刊1936年2月《越风》半月刊第七期。
(注十二):据1911年9月2日《民立报》,1911年9月30日、10月17日《时报》。
(注十三):据万鸿阶《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刊《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辑119页。
(注十四):见潘康时《记文学社》。《大江报》尤其鼓励新军中的文学社社员为该报写稿;1911年3月15日召开的文学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即曾通过一项决议:“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言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见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22页。
(注十五):据鲁祖轸《第三十标辛亥首义事略》。
(注十六):见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
(注十七)(注十八):见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
(注十九):见李西屏《武昌起义纪事》,刊《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辑15页。
(注二十):关于这篇时评的题目历来有三种说法:一说是《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李西屏《武昌起义纪事》、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李白贞《我所参加的辛亥革命工作》、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等主之,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从其说。一说是《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蔡寄鸥《鄂州血史》主之。一说是《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等主之,陈旭麓《辛亥革命》从其说。证以当时上海报纸上所刊《汉口商埠地方审判厅判决大江报之判词》,以第一说为确。
(注二十一):这篇文章向来误传为詹大悲所作,其实詹大悲在被捕受讯的时候就已经明白声明,这篇文章“系外间来稿”,因为“经我过目”,“选定登载”,所以“不能问作稿之人”,既不卸责,也不掠美,态度非常磊落,其非詹作,至为明显。见当时上海各报所刊报道。解放以来,不少辛亥老人在所写回忆录中,也有谈到这篇文章写作经过的。如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云:“(文学社成立后)革命力量已经成熟,同志热情也达沸点。同年夏,黄侃由汴返鄂,詹款留报社,设宴欢迎。黄醉后写一时论曰《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翌日刊出,当局大骇。”朱峙三《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亦谓系黄手笔,足为旁证。也有不少回忆文章沿用旧说,指为詹作,但大抵系耳食之言,不足为证。温楚珩与黄侃有郎舅之谊,又曾参加过当时的革命宣传工作,所说当更可信。
(注二十二):据1911年8月9日上海《时报》载称:“《大江报》馆总理、主笔、校对、会计诸人均皆剪发,与别报馆人不同,今春有人密禀,谓该报同人形迹可疑,……因无实据,含糊了结。”
(注二十三):1911年8月3日上海《时报》刊有《大江报》向全国呼吁声援的专电,文如下:“各报馆鉴,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大江报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