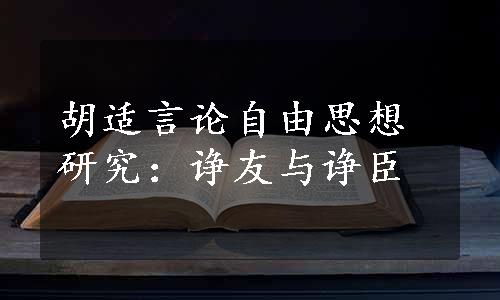
五、《独立评论》——“诤友”与“诤臣”之间
1956年,寓居纽约的胡适为已逝世二十年的挚友丁文江作传,回忆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的心绪,如是写道:
总而言之,大火已经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救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在君在几年前曾很感慨的对我说:“从前许劭说曹操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怖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我们这些“乱世的饭桶”在这烘烘热焰里能够干什么呢?[62]
“九·一八”以后,国事日蹙、警报频仍,中国朝野陷入“国难时期”的悲愤中,身处北方危城的知识分子更是感受良深。离沪北上之后,胡适与蒋梦麟等人忙于借助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源,希望重振已陷入山穷水尽境地的北京大学昔日的荣光。经过九个多月的努力,北大中兴曙光初露;1931年9月14日,“新”北大开学。一丝中兴的微光抵挡不住事变的浓密阴云,胡适失望异常,后在该日的日记中补写一笔——“我们费了九个月的工夫,造成一个新‘北大’,九月十四日开学,五日之后就是‘九一八’的一炮!日本人真是罪大恶极!”[63]
战争阴霾日益浓重,毁灭威胁迫在眉睫。“书生报国无他物,惟有手中笔如刀”,身处“烘烘热焰”里的知识分子救国之道不外乎办刊物造舆论。“九·一八”事变后12天,俞平伯即致信胡适,指出“今日之事,人人皆当毅然以救国自任,吾辈之业惟笔与舌”;建议由胡适出面领衔在北平办“一单行之周刊”。他在信中写道:“大祸几近眉睫,国人仍如散沙,非一时狂热供人利用,即渐渐冷却终于弛惰,此二者虽表面不同,为危亡之症候则一也。故现今最需要的,为一种健全、切实、缜密、冷静的思想,又非有人平素得大众信仰者主持而引导之,窃以为斯人,即先生也。以平理想,北平宜有一单行之周刊,其目的有二:(一)治标方面,如何息心静气,忍辱负重,以抵御目前迫近之外侮。(二)治本方面,提倡富强,开发民智。精详之规划,以强聒之精神出之;深沉之思想,以浅显之文行之,期于上至学人,下逮民众,均人手一编,庶家喻户晓。换言之,即昔年之《新青年》,精神上仍须续出也。救国之道莫逾于此,吾辈救国之道更莫逾于此。以舍此之外,吾人更少可为之事矣。”[64]的确,在以武力作为维护“中心”地位或者进阶“中心”手段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能够有所作为的空间非常有限;否则颇自信是“治世之能臣”的丁文江,也不会自嘲为“乱世之饭桶”。不过,他们并不因身处边缘就丧失那一份担当,希望能通过办刊物尤其是政论刊物的路径来实现自己的救国愿望和政治理想。所以,俞平伯的这番话很能表达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心声。胡适后来就回忆说:“《独立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要发起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65]
当时积极主张办刊的是蒋廷黻,他扮演了热心的推动者角色;《努力周报》时期丁文江也起到过相似的作用。据蒋氏回忆:“我提议办一个刊物,适之大不以为然,觉得我的提议完全由我没有办过杂志,不知其中的困难;孟和也是这样的腔调,陈衡哲最热心,在君和孟真没有表示。”[66]胡适和丁文江都有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不是件容易事,所以他们二人“都不很热心”;而胡适则“更不热心”,《新月》其时还正在遭受官方的不断打压,他在那个时期“真没有创办一个新刊物的热心”。不过1931年底,因为几个朋友的热心,胡适也就不反对了。于是在聚餐会的基础上组成“独立评论社”,并由丁文江提议:仿照《努力周报》的办法,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以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67]因胡适生病住院的耽搁,1932年5月22日,酝酿近半年之久的《独立评论》才终于面世。
《独立评论》是在国难临头之际的产物,虽然知识分子期冀能以“笔墨报国”的心情无二;但他们在确定该刊的办刊方针时却有分歧和争端。1932年1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拟了一个办周刊的计划,送给聚餐会的朋友们看。蒋廷黻也拟了一个大政方针,分三项:一内政,二外交,三人生观。这方针不甚高明”。[68]在蒋氏所拟的方针里,内政方面“首重统一,次建设,次民治”,要点有五。其中,第一点指出“现在统一问题虽与历代不同,然中心人物及武力亦不能免,在二三十年内,一方式的专制——一人的或少数人的,公开的或隐讳的——是事实所必须”。第三点指出“民治在中国之不能实行,全由中国无适宜于民治之经济、社会及智识,倘统一能完成,建设即可进行,而适于民治之环境自然产生矣。短期之专制反可成为达到民治之捷径。目前在中国大倡‘天赋人权’、‘主权民有’等理论不但无益,而且有损。本刊物应根据中国历史及现状,努力产生中国的新政治理论。此可谓本刊物之主要使命。”[69]根据原稿的笔迹判断,这一方针已由人修改,不过主要反映的仍是蒋廷黻的思想。该方针认为“专制”是“事实所必须”、“民治”在中国“不能实行”;难怪从未动摇过“民治”观念的胡适认为这一方针“不甚高明”。这也为以后的“民主与独裁”之争埋下了伏笔。1935年5月,胡适在为庆祝《独立评论》三周年所撰之文中,披露当时他们公推蒋廷黻起草了一个方案;胡适个人也起草了一个方案:
廷黻的方案已够温和,我的方案更温和。大家讨论了许久,两个方案都不能通过:又公推两位去整理我们的草案。想合并修正作一种方案。结果是整理的方案始终没出现。我在那时就起了一个感想:如果我的一个方案不能一致通过这十来个好朋友,我还能妄想得着多数国民的接受吗?这是一个很悲观的结论。但我又转念一想:我有什么特殊资格可以期望我的主张一定成为大家一致接受的方案呢?我的主张不过是我个人思考的结果。我的思想有被接受的期望,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有接受的期望。最好的方法是承认人人各有提出他自己的思想信仰的自由权利;承认人人各有权利期望他的思想信仰逐渐由一二人或少数人的思想信仰能变成多数人的思想信仰。只要是用公心思考的结果,都是值得公开讨论的。[70]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者解决分歧的方式。在《独立评论》创刊号的“引言”中,胡适再次强调了这种自由主义者的行为理念: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正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71]
《独立评论》并非敝帚自珍式的同人刊物。“引言”中即表示“欢迎各方面的投稿”。果然几期之后,社外投稿逐渐增多,“直到后来有时候我们差不多可以全靠社外的文字出一期报,我们不过替他们尽一点编辑校对发行的责任,或者加上一两篇比较有时间性的政论文字”。于是一年之后,更申言“我们办这个刊物,本来不希望它做我们这十一二个人的刊物,也不希望它成为我们的朋友的刊物;我们自始至终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72]。《独立评论》四周年之际,统计发现:四年中社外来稿的比例分别为占42.7%,55.3%,61.8%和59.6%。对此,胡适不无自豪地说:“这个刊物真能逐渐变成全国人的公共刊物了。四年之中,社外的朋友供给了六百篇文字——六百篇不取稿费的文字——这是世界的舆论机关绝对没有的奇事。”[73]二十年后,胡适还很感慨地将那个时代称做“Pamphleteering journalism(小册子的新闻事业)的黄金时代”,因为“《独立评论》共出了二百四十四期,发表了一千三百零九篇文章——其中百分之五十五以上是社外的稿子——始终没有出一文钱的稿费”。[74](www.daowen.com)
《独立评论》的发行量很是可观,当时负责该刊校对的章希吕在其1936年3月23日的日记中即记载:现在《独立》每期印一万三千册,可销一万二千五百册。[75]胡适在1936年亦说:“关于销路这一层,我们自己也感觉到很大的欣慰。我在第一五一号(三周年纪念号)曾提到‘我们的七千个读者’,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的一万三千个读者’了,在这一年之中,销路增加一倍,其中有好几期都曾再版,这是我们最感觉高兴的。”[76]这一发行量在当时所出的近400余种杂志中独树一帜,与清末风行海内的《新民丛报》(1902—1907)相比亦不逊色,因为后者发行量最高时亦未超过一万份。
胡适初始虽对创办《独立评论》并不热心,甚至在1932年4月一封给丁文江的信中还写道:“总觉得此次办报没有《努力》时代的意兴之十分之一!”[77]其实胡适经常是一个人独立支撑刊物,每周一往往终日为杂志工作,夜间写文章总是到次日凌晨三点钟乃至更迟。[78]1934年9月18日夜,欧游途中的蒋廷黻在给胡适的信中不无愧疚地写道:“当初我们办《独立》,你有点老成持重,不愿轻试。我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总要干。殊不知这两年来,这个《独立》由适之一个人去立了,实在对不起你。”1935年除因事离开北京才由他人短期代编外,作为主编的胡适一直劳心劳力;尽管家人对此多有抱怨,但他却毫无怨尤,并将在国难之中维持刊物一事理解为对“公家”尽责。胡适在1935年1月9日复周作人的信中曾写道:“三年多以来,每星期一晚编撰《独立评论》,往往到早晨三四点钟,妻子每每见怪,我总对她说:‘一星期之中,只有这一天是我为公家做工,不为吃饭,不为名誉,只有完全做公家的事,所以我心里最舒服,做完之后,一上床就熟睡,你可曾看见我星期一晚上睡不着的吗?’她后来看惯了,也就不怪我了。”[79]
在胡适等的努力之下,《独立评论》维持了5年,前后共出244期。发表文章1309篇,加上通信类,共1317篇。学者陈仪深将这些文章按照与“民主思想”的相关性程度划分为三类。A类为“民主思想本身或与民主直接有关部分”,共392篇。此类可细分为:“民主与独裁的讨论”59篇、“有为与无为的建设”21篇、“唤起权利意识”22篇、“反对内战拥护统一”20篇、“对国民党的期望与共党问题”42篇、“宪草、宪政与国大选举”54篇、“行政改革”26篇、“乡村建设讨论”40篇、“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42篇、“民族文化与西化问题”66篇。B类为“与民主思想间接有关部分”,共379篇。此类可细分为:“中日关系与挽救国难”153篇、“日本情势”25篇、“国际联盟”27篇、“纪念丁在君”27篇、“对青年讲话及教育思想”26篇、“国内各地见闻”89篇、“国外旅游见闻”32篇。C类为“与民主思想无关部分”,共546篇。此类可细分为:“一般教育问题”89篇、“科学研究”68篇、“财经社会农业”136篇、“书评”24篇、“译文”23篇、“小说”13篇、“杂文”105篇、“国际关系与外国情势(日本除外)”57篇,“地理国势”35篇。胡适个人发表123篇文章,是为《独立评论》撰稿最多的人,其中A类文章59篇、B类文章51篇、C类文章13篇。[80]
由上述统计可知,抗日问题与民主问题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核心关怀所在。在这两类问题上,作为主编的胡适坚守“独立”的办刊宗旨,主张言论自由,鼓励意见交锋。他撰稿时更以“敬慎无所苟”的议政理念要求自己,不囿于成见、不趋附时髦,阐述富有建设性的见解。以“中日关系与挽救国难”论题为例,胡适相继发表《上海战事的结束》、《汪精卫与张学良》、《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究竟那一个条约是废纸》、《全国震惊以后》、《日本人应该醒醒了》、《我们可以等候五十年》、《我的意见不过如此》、《保全华北的重要》、《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国际流言中的一个梦想》、《“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今日的危机》、《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整整三年了》、《中日提携,答客问》、《“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沉默的忍受》、《苏俄革命外交史的又一页及其教训》、《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答室伏高信先生》、《冀察时局的收拾》、《我们要求外交公开》、《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敬告宋哲元先生》、《中日问题的现阶段》30篇文章。这些文章平实而又深刻,虽不乏书生之天真,却闪烁出理性的光芒。
1934年4月,时在上海的傅斯年致信胡适,写道:“此间读书的朋友对先生在《独立评论》所做的文章(特别是国际形势及中日问题)均极佩服,认为是此时稀有的一个道德力量,此力量颇对政府外交政策有好影响。”[81]胡适的对日言论不仅为“读书的朋友”所佩服,更对当时的社会和政府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从日本侵略者的反应可窥一斑。1936年5月23日,翁文灏在信中写道:“日本大使佐佐崛内干城日前来‘随便’谈谈,言及中日外交虽日言亲善,而事实颇有困难及阻碍。所谓事实者,(一)报纸言论;(二)中国军事进行;(三)走私事归罪日本。所谓言论者,首提及兄在《大公报》之论文,谓恐引起国民反感。”[82]这篇被日方认为会妨碍“中日亲善”的文章是《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4月12日首发于《大公报》“星期论文”栏目,文末警告:“如果日本的政治家到今日还认不清我们两个民族的关系日日恶化的倾向,如果日本的政府国民还不肯做一点‘釜底抽薪’的努力,如果日本的政府军部到今日还梦想中日关系的调整只是中国单方面的屈服,那么,我们深信我们两国间的关系是无法调整的,只有大家准备扮演同文同种相屠杀的惨剧而已。”此文发表后,天津一家汉奸报纸公然主张要“驱逐胡适出华北”;《大公报》亦因此文被日本驻屯军部严重警告。6月18日,王世杰在信中劝告胡适要有所提防——“弟所得负责方面之密报,日人对兄极注意”。[83]
《独立评论》时期,胡适的基本立场是处于国家的“诤臣”与政府的“诤友”之间。这一立场既体现在他的言论中,更体现在他是否“出山”的问题上。1933年3月31日,汪精卫恳切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部长。4月8日,胡适委婉而坚决地拒绝:
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决不是爱惜羽毛,实在是想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84]
胡适看重清誉、爱惜羽毛,是无可隐晦的事实;不过他希望养成“无偏无党”之身,不想参加政府,亦非虚言——他与国民党政府的心理距离甚远,在思想哲学上存在深刻歧异;对国民党政权的治理能力乃至合法性,他亦只是有条件地承认。胡适常常批评“南京政府的大病在于文人无气节、无肩膀”。1934年2月5日,在与孙科的谈话中,他更从制度上对国民党进行批判——“今日政治制度皆是不懂政治的人所制定,止有空文,而无实施手续,所以彼此之间全无联络,又无有相互制裁的办法”[85]。
1935年开始,翁文灏、蒋廷黻、吴景超等《独立评论》同人相继参加国民党南京政府。胡适对知识分子介入实际政治虽持保留态度,但在国难之际,他不能不认可朋友们服务政府的行为。对于这些“出山”的人士,胡适连续致信,希望他们保持清誉,勉励他们做“诤臣诤友”。1936年1月21日,他写长信给翁、蒋、吴和顾季高,希望他们不做“伴食”之官员,并引《孝经》中“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一语劝勉。[86]1月26日,他又写信给翁、蒋和吴,指出:“我对于你们几个朋友(包括寄梅先生与寄高兄等),绝对相信你们‘出山要比在山清’。但私意总觉得此时更需要的是一班‘面折廷争’的诤友诤臣,故私意总期望诸兄要努力做educate the chief[教育领袖]的事业,锲而不舍,终有效果……兄等皆当以宾师自处,遇事要敢言,不得已时以去就争之……”[87]
“七七”事变后,战争以排山倒海之势降临,《独立评论》因此于1937年7月25日毫无预告地停刊,胡适也只得放弃“在山”的立场奔赴国难。约在1937年8月间,胡适与钱端升、张中绂三位北大教授受蒋介石的征派,他们的共同使命是赴美、英、法等国宣传抗日、寻求援助。9月26日,胡适辗转来到美国争取同情。1938年9月17日,他正式被任命为驻美大使。对于担任大使一职,胡适其实并不乐意。7月30日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他埋怨国内友人在此事上没有积极提供意见——“我自己受逼‘上梁山’,你们当有所知,何以都不电告你们的意见。万不得已,我只得牺牲一两年的学术生涯,勉力为之,至战事一了,仍回到学校去。”[88]任命令发布以后,对一向不赞成他从政的妻子,胡适解释:“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89]
概言之,《独立评论》在其五年零两个月的生命历程中,虽然数次因言论犯忌而屡屡遭受查扣等干扰,甚至是长达四个多月的停刊查禁,却依然令人钦佩地在当时黑暗焦灼的气氛中保持了创刊时的特征。《独立评论》的“灵魂”人物胡适亦在动乱中坚持民主,在混乱中赞颂理性。1934年,在《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一文中,胡适曾写道“信心只是敢于肯定一个不可知的将来的勇气”。在那个外敌入侵、内战频仍的艰难时世里,他是为数很少能富有这种信心的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