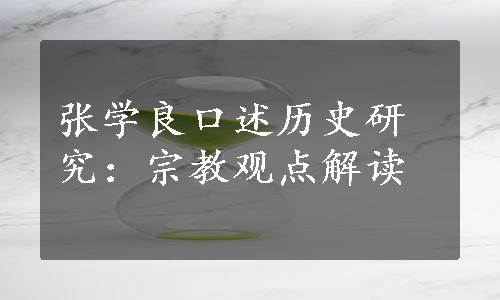
王海晨 解红丽
张学良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政治“流星”,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虽然活了一○一岁,用他自己的话说“政治生命到三十六岁就结束了”。他因发动西安事变,“政治生命”戛然而止,也因此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巨大贡献。对他三十六岁前政治人生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而对其漫长的宗教人生的研究却未见一篇学术论文问世。究其缘由,有主、客观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人们将其视为政治人物、“民族英雄”,不愿意触碰他的宗教人生,一提他“执迷”宗教似乎有损于他的政治形象,多数学者主观上不愿意谈此话题;另一方面,关于他与宗教的关系,资料寥寥,学者因困于“无米之炊”而作罢。笔者有幸参与了当代中国出版社即将出版的、以存藏于哥伦比亚大学150多盘口述录音为主体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全集》的整理工作,发现了大量他与宗教的珍贵史料。为此,本文试对其漫长的宗教人生及其特色鲜明的宗教观做一梳理与探讨。
一、始于被动,终于执著的宗教信仰历程
张学良最开始接触宗教源于1912年他家里发生的一喜一悲两件大事,一件是他父亲张作霖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一跃成为奉天举足轻重的人物;一件是张学良母亲去世,他因而离开家乡,第一次来到了奉天城。当时的奉天城,虽比不上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却也是东北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他父亲张作霖虽置高位,却不通文墨,置身于中西文化碰撞时代的他,深感读书和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他不想文墨不识的窘迫在他儿子身上重演,特请人教张学良英语。张学良学了几年英语,偶然间,发现基督教青年会是个学习外语的好场所,开始出入青年会。由于他思维敏捷、现代,加上他父亲的地位,在青年会里很快交上了一些朋友,也使他与基督教结下了一世情缘。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1914年,青年会组织者来自美国、苏格兰和丹麦,经费来源主要靠在当地募捐。由于最初青年会名气小,会员少,经费缺乏,会所是临时租赁的老房子。“很简陋一个地方,是我给他帮忙,省政府给建的,钱也是我给他募来好多”(1)。新会所中设演讲大厅、教室、书刊室和游艺室,其规模足与京、津、沪等地的青年会媲美。“我没有事情做的时候都在club里待着”,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种学术演讲会、读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以及各种比赛,不仅练得一口地道的英语,生活态度、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我在这里受他们影响很大”。十九岁那年,因张作霖安排他进奉天讲武堂学习,他也就离开了青年会。“当了军人之后,可以说关于宗教,完全像抹掉了一样”。和青年会“没有时间来往了”。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失去了自由,开始读《明儒学案》。“我读《明儒学案》,不是我要读,是蒋先生(蒋介石)要我读《明儒学案》”。从1937年至1946年幽禁大陆期间,他“专心”研究宋明理学和明史,还写了好几大本读书笔记。逐渐他发现宋明理学离现实太远,根本不能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后来,我就把这个事情放下了。我不想再研究了,没有那个兴趣了”。因为在大陆被幽禁的地方多为人烟稀少、交通不便的深山古刹,张学良能见到的人除了身边的“监护”,就只有庙里的和尚了,耳濡目染,佛心渐萌。在溪口时,幽禁地与雪窦禅寺为邻,他常和寺里的和尚来往。“认识了最有名的和尚,太虚法师”。“我就跟他谈佛教”。到了台湾后,他对佛教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和监护队长刘乙光等谈论佛教,还买了许多佛教方面的书阅读。直到1953年的一天,“蒋夫人到高雄看我的时候,她问我,我就随便给她讲佛。……她待了会儿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她就跟我解释说,你大概想我是混蛋(傻瓜),蒋夫人就是说他自己啊,为什么要信基督教呢”?“上下几千年,永恒几万年,有地位高的国王、有渊博学问的人,这些人为什么都信基督教,我是傻瓜,难道这些人全是傻瓜”。张学良为难地说:“我对基督教,早年我年轻时也有过接触,我现在上哪儿研究啊?我一个人怎么研究啊?”
为了让张学良信基督,宋美龄先后为他安排了三位家庭教师:曾约农、董显光、周联华。曾约农和周联华在台湾岛内神学界颇负盛名。曾是晚清重臣曾国藩嫡系曾孙,台湾东海大学创办人,与张私交甚笃。但他因有高血压,行动不便,便换为国民党前中宣部长董显光。“董显光对基督教也不是鼎深的”。那为什么安排他做张学良的家庭教师呢?最重要的原因,“董显光是蒋先生(蒋介石)的老师。蒋先生当年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董显光在中学教英文。所以他跟蒋先生很接近,很密切”。把他安排在张学良身边,蒋可以通过董及时掌握“我这儿到底怎么样”?“后来董显光中风了,跟他太太到美国去了,这才派了周牧师来”。周牧师即周联华,周生于上海,时任亚洲浸会神学院院长、台北士林凯歌教堂牧师,曾为蒋介石、宋美龄的牧师。在周的建议下,张学良申请了美南浸信会的神学函授课程。“从此我就研究神学。一共读了十几年,才拿到毕业证书”(2)。“我过去跟基督教的人接触很多,也受到影响。但是我最后信,还是蒋夫人的关系”。宋美龄安排的三位家庭教师在张学良眼里都是“很好的基督徒”,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为了表示对三位家庭教师的尊敬,也为了显示信仰的虔诚,1964年受洗时起了笔名:“曾显华是我的笔名,曾是曾约农,显是董显光,华是周联华。”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从不讳言。他在台湾期间,写了《好消息》、《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等小册子宣传基督教;在电视上作节目,讲述他的宗教信仰。在夏威夷期间,自费出版《毅荻见证录》,追叙他信奉宗教的心路历程。
通过对张学良与宗教关系的梳理,至少我们可以确知他于1964年皈依了基督教。他为何在晚年虔诚地信奉基督,我们需要从更多的角度和更深的层次上来揭示这一现象背后的真正原因:一是缘于早年青年会的经历。张学良喜欢新鲜事物,十六七岁就在青年会接触了西方基督徒,因对基督徒产生了好感,对基督教也发生了兴趣,这为晚年的皈依打下了基础。二是缘于他被幽禁54年,54年的无所事事,为他专心研究宗教提供了条件。“我们念神学,念了19年。如果一天到晚打仗,怎么能念神学”?每个礼拜用一两天的时间,上教堂,做礼拜,“谁有这么长时间啊”?三是缘于基督教义和他对自己痛苦人生的某种理解有一个神秘的契合。基督教教义宣扬人类从其始祖亚当和夏娃起就犯了罪,只有信仰上帝人类才能获救。被幽禁期间,张学良经常反省,他认为自己有罪,参加内战,“我们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真是犯罪啊”。“我杀人也杀了很多”。这种心理正好和基督教教义的原罪说有一种契合。四是缘于无奈和宋美龄的“引导”。
由此可见,尽管张学良信奉基督,固然是在宋美龄的“引导”、三位“家庭教师”的影响下乃至他当时被幽禁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只是表面的、直接原因,而他既往的特殊经历、基督教义本身的内容特质和他对人生的理解与追求产生了某种契合,才是他真正走向神学之路的最深层、最根本的原因。
二、多元、开放的宗教观
张学良自幼师从当地名儒,国学素养十分深厚。53岁以后,开始研习基督教,开口闭口不离上帝,买书看书,皆与基督相关,并渐入虔诚之境。由于经历了中、西两种文化的熏陶,使张学良以独特的视角游刃于两种世界之中。53年积聚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使他抛弃了许多西方神职人员及宗教徒那种排斥异质文化的狭隘观念,48年研究基督教历程中形成的执著追求使他更加鄙视东方“官文化”中封建意识,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开放的、多元的宗教观。
在他看来,无论是信儒学、道教、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是一种信仰。他强调“做人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仰”,他批评现在有些人什么都不信,只信钱,“所以社会才这么乱七八糟”,“不管信佛也好,信道教也好……你就不同”。人没有信仰,“就是一个浮萍。你有了信仰,你无论有什么信仰,你就有一个根”。“我是三教九流,我什么都不(排斥)”,而且他对各家思想都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
他对儒家思想有褒有贬,褒其宣扬待人忠厚,贬其压制科学,只为做官。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就是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深入中国人的思想之中”,“这儒家思想对我做事有很大的关系”。“儒家思想……是一种忠厚的思想……任何事宁可自己吃点亏”。不过,他认为儒家思想是“一种政治的学说,不是一种整个的社会学说”。“我认为中国到现在都不能强就是(受)宋儒的思想(影响)”。因为它压制科学,不在科学技术上下功夫。“这种思想在我看完全是落伍的玩意儿”。“中国儒家的思想完全是一种做官的思想。……你怎么能做官?你怎么能当官僚哇?完全是这种思想。我是看不起”。
他崇拜老子的道学,认为道教是与佛教互相融合又长期斗争的产物。东汉末年,道教创立之初和佛教传入之始,两教的关系十分密切,后来“佛教、道教分开了”,一般人“也不知道佛教跟道教有什么联系”。道教的教主是老子,实际上“老子并没传教”,“一部分人,要跟佛[教]斗争,制造出了一个道教”。在他看来,老子是一位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认为老子思想深奥,风格迷人,“老子这个道德经是非常的深啊,他一开始就说得很深,道可道,非常道,就是这种,中国有句话,玄呢”。张学良特别欣赏老子的道学。
张学良曾经沉迷过佛教,但他拒斥了佛教教义中求福的观念,欣赏“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救世精神。“你要是为救人,存佛心救人,你可以杀任何人”。“你杀错了人,你就要下地狱”,因此,菩萨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认为佛教和基督教一样,也是讲救人的,但讲得“狭窄,不真切”。佛教也讲“求”,“佛教他最后求的还是自己的福。那么基督教不是,不是求自己的福。”佛教和基督教的出发点,即对于罪的承认及对人类苦难的关切是接近的,但脱离苦难的方法不同,基督教靠上帝,“佛教不讲神,不讲神学,讲的是社会学”。讲“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他对佛教的结论是:“在我们现在看,这都是没意思的事。”
在张学良的宗教观中,他最推崇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比佛教高得太多了”,“我说这句话是站在社会学的宗教观念上来说,不是站在宗教的地位上来说”。站在社会学的宗教观念上,他推崇基督教什么呢?
第一,他推崇基督教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我对宗教,我对马丁·路德那是很佩服的。”最佩服马丁·路德为宗教改革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过去都是天主教嘛。是他改教……那个时候改教是犯罪的,犯很大罪”,主张改教的人被“烧死两千多人哪”,“他说为正业,为道,他说火我敢走过去”,“我为真理我不在乎。基督徒就是这样”。“我情愿死”。
第二,他推崇基督教追求心灵自由的观念。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是最为宝贵的,对张学良而言,自由是他最大的渴望。他对自由有自己的理解,“所谓自由,就是你不为你那个私心拘束了”。人最大的私心莫过于对生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他认为基督教解决了这一问题。“一般人怕死……基督徒没有死的思想”。“我们死的思想是什么?不过是我们搬搬家就是”。“死是很光荣的,不仅是光荣,是很快活的”。关于如何实现自由,他认为只要信上帝就能实现,即“得救”。“我不过是上帝一个仆人,一个工具”。“上帝是窑匠,我们都是泥巴……那个泥巴就由窑匠捏就是了”。“他要把我们做成个杯子,我们就是个杯子”。“他要把我们做成尿盆,我们就是尿盆”。基督徒的自由来源于对上帝的“信”,他说:我“为什么有自由?就是有耶稣与我同在。我什么都无所畏惧”(3)。
第三,他推崇基督教的“博爱”观,“宗教信仰就是一个爱字”。爱是信仰的核心理念。爱包括:(1)爱自己的祖国。1990年,他在台北祝寿会说:“现在,我虽然是老迈了,假如上帝有什么意旨,我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我必尽我的力量,我所能做得到的,我还是照着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4)(2)爱自己的工作。“有个人说得好,我非常佩服这句话,他是一个基督徒,他说:‘我做什么事我都给上帝做事。’他是干什么的,他是一个纳鞋底的,做皮鞋的,他说:‘我拉这个绳子,拉得紧紧的,等于给上帝做一样。’简单说,恪尽职守”。(3)爱自己的身体。“我们基督徒,是[相信]我的身体是殿,我们要清洁我们的殿,准备上帝的圣灵来居住”,“我自己保护我的身体,不是为了我自己多活几天,或者享受,我完全是为(完成)上帝的使命”(5)。基督徒的“爱”有三种境界,一是爱人如己,他晚年给人写信、题词,用得最多的词汇就是“爱人如己”,二是超越世俗之爱,他认为为了金钱、肉欲、名利而产生的爱都不是真爱。他晚年写的“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子汉,磊落光明度余年”一诗是他对超越世俗之爱的最好注脚。三是舍己爱,“爱就是牺牲”。耶稣的爱就是舍己之爱。
第四,他认为基督教是真实的历史。“我承认这是一千九百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实在真的事情。我信仰耶稣基督,我们信仰他真有这么一个人,是他所做的事情,而由他身上显示出来上帝的实在。另外,我们从教义上说,他就是上帝的化身”(6)。这一认识足以证明张学良对基督教的信仰是虔诚的,因为“假如上帝不存在,那么,你崇拜他或向他悔罪,便无任何意义”(7)。
中国是一个宗教情感比较淡漠的国度,虽然世界三大宗教在中国都有信众,中国自己也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到处都有人烧香礼佛、磕头拜神、唱圣歌、读圣经,但宗教在一些人心中担负的是过多现实的、政治的功利。张学良的宗教观并不是功利性的,剔除了实用主义的功利性,对宗教本质进行理性阐释,是张学良宗教观的一大特征。
张学良宗教观的另一大特征是它的包容性。他的宗教观中既有对儒学现实主义的重视,又有对道教崇尚自然、看淡名利的赞扬,还兼对禅学“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担当精神的称道,更有对基督教“平等自由”、“爱人如己”和为真理而献身精神的赞美,这种中西交融、多元开放的宗教观,尤其是他对佛教与道教关系的阐述、对佛教与基督教理性的比较,一方面为我们研究他的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也为他不自由的人生插上了飞向自由的精神翅膀。
三、宗教观对其口述历史的影响
张学良的宗教观为他晚年人生总结提供了一把打开心扉的钥匙和一把衡量是非的标尺,同时也提升了他对往事认知的高度和思想意蕴。张学良的人生如同一部狂想曲:二十八岁以前是他的人生序曲,以流浪、异想天开为主题曲,揭开了他短暂而壮烈的政治人生;二十八岁时奏出人生的第一乐章:东北易帜,分裂了16年的中国形式上复归统一;“而立之年”,他的一纸通电拉开了第二乐章的帷幕,100多万人厮杀了200多天的中原大战戛然而止;三十六岁那年,第三乐章西安事变开场,这是他以全部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演奏出的最壮烈的乐章。接着便是54年的“锁嘴”,直到1990年才开口说话,奏响了他人生的最后一个乐章——口述历史。这最后一个乐章是对前三个乐章的总结;没有前三个乐章,这第四乐章不会精彩,没有54年的“锁嘴”,第四乐章不会如此之珍贵。还有一点,没有他对宗教的痴迷,恐怕他的嘴不会锁得这么久,也不会在此时打开,也不会对往事有一种宗教式的宽容,思想意蕴恐怕也不会那样“圣洁”而丰厚。可以说,张学良的宗教观对他的口述历史是有较深影响的。
首先,口述历史的动机与常人不同,有传播宗教信仰,为上帝“传福音”的因素。口述动机是口述者接受和完成口述历史的原因与内部动力,直接关系到口述历史的价值。自1936年底南京军法审判后,张学良就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外界听不到他的一点声音。张学良性格耿直,是位有话憋不住的“东北汉子”,他何以能“锁嘴”54年?当然,他“锁嘴”首先是政治处境不允许他说。关键是他一肚子话憋了54年,居然没有憋出毛病来,还活了一○一岁,这就与他的信仰有关了。儒家的“小不忍,则乱大谋”、道家的“多言多败”,佛家的“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基督教的“爱是恒久忍耐”等观念,使他走向顺从、忍耐、忏悔、谦卑之路。他在口述历史时说:“我这个人为什么不说?明白的人用不着和他辩,你和他争辩干什么。人啊,为自己申辩最无耻,评论是别人发出来的,不是你自己。”“我是个基督徒……不用为过去的事情抱不平,上帝会报”。
那他为什么后来又打破了“锁嘴”梦魇,开口说话了呢?一是他认为“要问山下路,须问过来人”(8)。他是“过来人”,应该给“问路人”指个路。二是他在“锁嘴”期间,读了一些书,深感“最近之现代史,疑案重重,记载上多有不真实之处。然此并非皆由写史者,有意歪曲,而真实之史料,实在是难得访求也。有之传闻失实,有之记述讳隐,有之自我夸张,或者泯灭无可察考。此之对于后世之人,诚为重大之遗憾”(9)。三是他把口述历史视为“证道”。“所谓证道,就是你给那件事作个证”。“给上帝做见证”。他是过来人,有给迷路人指路的义务;其他人说的有失真之处,他有纠正的责任;传播宗教信仰、为上帝“传福音”、“做见证”是基督徒的“天职”。所以,当新闻记者问他为什么开口说话时,他回答:“我接受日本NHK电台访问,我是要对日本青年说几句话,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不要再存过去日本人那种思想……我是劝现代的日本青年,世界上大家都应该和平相处。”为什么要对年轻人说几句话?他认为“现在的教育是相当的失败,使我们念书的,不论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你问他们脑子里是什么?就是没有宗教信仰……若脑子里有的信仰就是金钱,那问题就大了”(10)。劝青年学生爱国、树立信仰,是他开口说话的原因之一。赵一荻解释张学良为何做口述历史时说,“我们传福音就是人得悔改了,叫人不要再崇拜金钱肉欲了”。张学良和采访他做口述历史的张之宇、张之丙多次说过,“我们现在谈话,就跟传福音一样”,口述历史,绝不是“来宣传我自己,我是借着这个来传福音”。“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讲给人们听”(11)。从他做口述历史的动机看,已经注入了宗教因子。
其次,他以“上帝那有本账”自设威慑,增强了口述历史的真实性。真实性问题一直是史家漠视口述历史的主要因素,认为口述历史是口述者的个人记忆,它比文字史料的失真性更强。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阿瑟·马威克就认为:“不以文字史料为依据的历史虽然也是历史,但不是严谨的和令人满意的历史。”(12)史学家对口述史学的漠视,主要是对口述历史的可信度持怀疑态度。影响口述历史可信度的因素固然很多,但口述者的信仰和人格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张学良口述历史时,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上帝那有本账”,说假话是对上帝的不敬。“我都九十多岁了……无事不可对人言”。“我从不对人说假话,我顶多不说,我说的话,我自己负责”。他说他搞口述历史“不是为着搞什么辩冤白谤,只是替历史留下一点真实的故事”(13)。
当然,他的口述历史是否真实不能以他自我评价为标尺。不过,是不是“辩冤白谤”,是可以验证的。历史上的名人最重视名,涉及名声问题是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刻意维护,确实是判断名人口述历史可信度的试金石。涉及张学良名声的问题主要有:中东路事件是谁挑起的?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谁下的?西安事变后他被判刑是对错?一般学界都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挑衅所致,九一八不抵抗的命令是蒋介石下的,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判刑是蒋介石背信弃义。而张学良说:中东路事件“不是人家挑衅,是我们挑衅”。“这件事我们做得很不好”。“没什么证据,叫人搜集什么呀?”提到九一八不抵抗问题,他说:“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14)关于西安事变后被判刑,他说:“那蒋先生也没说假话,他后来真是(不剿共了)……所以自己请罪,那么我应该受死刑,等于叛变了,劫持长官在我们军队里是最厉害的罪,那就是叛变。”采访者对判刑不理解,说:“不是有将功折罪吗?”他说:“那也不能那么讲,我没有功啊,没有去打仗。”“我自己做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任,我不往这人身上推,也不往那人身上推。”一斑可窥全豹,不护己短,不隐己污,常人所不能;揭世人不知之短,晒他人不知之污,纠对己有利成说之误,只有深具宗教情结者方可做到。他以“上帝那有本账”自设威慑,使他在回望历史的同时将探求真理的目光投向了人生彼岸,这使他的口述历史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包括阎锡山、李宗仁、孔祥熙、宋子文等人的更加客观、真实而有价值。(www.daowen.com)
再次,他的口述历史充满了宗教情怀。“我也是受中国旧教育,儒家教育的”。年轻时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具有强烈历史使命感,而在强烈使命感的精神寻求中,他在晚年仰慕基督伟大的人格和崇高精神,耶稣成了最终追求的精神楷模。
他在口述历史时极力赞美基督是正义的化身。“日本失败,日本投降了,那我心里很安定,我没有什么。我自己总想圣经上讲的两句话,‘申冤在我,报复在我。你不必为失去抱不平’,那么我就想,日本所得到的什么,两个原子弹,这不是申冤在我,报复在我?谁能让(日本)变成原子弹实验场,死了那么多人,谁招的呢?自己招的。谁主张,那是上帝主张,谁能做得到呢?怎么两颗原子弹都投到日本,日本死几十万人,所以,申冤在我,报复在我。何必呢?我们人做不到的事情,那么神,他的能力比我们大很多”。像这样赞美正义的话语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比比皆是。
他在口述历史时或赞颂宗教式的牺牲精神或以宗教的牺牲观念自喻。在谈到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时,他慨叹:“我在法国,有一次,看见刺客枪杀一位亲王。枪一响,那些警察、老百姓都向前跑,去抓那个刺客。而我们中央党部那次刺杀汪精卫时,枪一响,人全向后跑了,刹那间人就没有了。”回忆西安事变时,他提到宋美龄对他的评价:“她说,‘西安事变不要钱,不要地盘,要什么呢?要去牺牲。……’所以蒋夫人对我很好,很了解我。她说我是Gentleman(君子)。”他以宗教的牺牲观念自喻,以宗教的情怀解释自己以往的行动,以此呼吁人们燃烧自己,温暖他人。
他用以德报怨的宽恕精神来化解个人恩怨。他在口述历史时以回忆的方式奏响了对宽恕精神的赞歌。他对监管他的特务们宽容。“他也是受命令所做的,我得原谅他”。他对不理解他的人宽容。“我向来什么事情,尽到问心无愧就完了,旁的我不管。我不但不管,我还要原谅别人,人家也是人啊,人家不能像我一样傻瓜,人家不能不为自己打算打算”。在命运的拨弄面前,他以宗教的胸怀宽以待人,他用一腔的真诚讴歌着宽恕精神。
在对宗教人格进行赞颂的同时,他以宗教忏悔情结所内含的批判精神为武器,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拷问,对宗教的阴暗面进行了挞伐。如他说:“我这个人放荡啊,我不愿意受拘束。”“我没有女人差不多我不能活啊。”纪晓岚的一句话影响我很大,他说“‘生我的我不敢,我生的我不淫,其余无可无不可’”。“我这一生啊,没有坏的事情,就这个事情乱七八糟的。所以我跟我的部下,部下太太不来往。一个是我躲避嫌疑,一个是我这人乱七八糟”。他以自我反省的方式,忏悔着情欲的迷狂,以自我晾晒的方式鞭挞着灵魂的丑恶,这种不留情面地自我解剖,恐怕在所有口述历史中是绝无仅有。他还对有些基督徒的虚伪进行了挞伐。“你别认为基督教徒都是好人,基督徒也是人,他也有野心”。“他一样的犯罪”,“不犯罪只有耶稣基督一个人”。他还对来华的传教士进行了揭露,说有些传教土就是为了钱,不给他钱,他也不会来。
结论
一位民族功臣居然在成熟的壮年信奉起宗教,而且达到了痴谜的程度;一位自称“我就是共产党”(15)的唯物主义者,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之后,笃信起基督教,这确实是发人深省的现象。究竟如何解释这一现象,他皈依基督就有损于他的形象吗?
笔者认为,张学良是基督徒,还是基督教研究者,是真的相信上帝,还是他信奉基督纯粹是为了寻求一种精神寄托,都无损于他作为一位爱国者的形象。爱国和信教并不是一对矛盾,相反,它更使我们感觉到张学良是位可亲、可爱、率性、易于接近、不刻意维护“名誉”的伟人。既然人们并没有因为孙中山曾皈依基督而否定他创立民国的功绩,既然人们并没有因为牛顿“视《圣经》为至高无上的哲学”而看轻他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既然人们并没有因爱迪生深信上帝的存在而贬低他在科学发明史上的地位,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人们不会因为张学良在被幽禁期间信奉宗教而损害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光辉形象。
在看待张学良信教的问题上,有一点是不应该忽视的,那就是他信教的背景。如果不把这一问题放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去考察,不考察他信教的背景,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历史问题放回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条件之下。对张学良信教问题,我们应给予充分的理解。他痴迷佛教、皈依基督都起于政治压力,是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研究基础上走向痴迷和皈依的。宗教的力量人所共知,善良的人、弱势群体、追求信仰的人们是宗教生根开花最肥沃的土壤。
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提升人们的品位,也可以消沉人们的意志,消磨人们的进取精神。对于张学良来说,更多的则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他信教虔诚,但他没有失去理性,更没有陷入狂热和偏执。他信教虽然起于被动,但很快即在研究的基础上将信奉纳入了完善个人人格和追求真理的轨道。他将信教作为一种信仰,但从未滑入盲目崇拜的地步;他对佛教、基督等教义既有汲取,也有舍弃,甚至是批判;他对佛教徒、基督徒既有赞美,也有善意的批评,甚至是激烈的抨击;他信奉外来宗教,但不排斥本土宗教,更不拒斥中国的儒家文化。在他的宗教生涯中,他始终没有因为信奉哪一种宗教而丧失自己鲜明的主体意识和冷静的理性精神。他对宗教的这种态度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地对待西方先进文化,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注释】
(1)文中所引用未注明出处的张学良原话,均根据张学良口述历史录音整理而成。
(2)窦应泰编著:《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51—252页。
(3)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253页。
(4)张学良:《在台北祝寿会的讲话》,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9页。
(5)张学良:《在台北祝寿会的讲话》,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9页。
(6)张学良:《答台湾〈华视新闻杂志〉记者问》,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二),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8页。
(7)斯温伯恩:“一个自然神学家的使命”,克拉克主编:《作为信仰者的哲学家——11位思想界带头人的精神历程》(PhilosophersWhoBelivee——theSpiritualJourneysofllLeadingThin kers,InterVarsityPress,1993),第181页。
(8)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79页。
(9)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42页。
(10)张学良:“对台视观众谈人生信仰”,毕万闻主编:《张学良赵一荻合集》(六),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5页。
(11)毕万闻主编:《张学良赵一荻合集》(六),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
(12)阿瑟·马威克:《历史学的性质》(ArtherMarwich,TheNatureofHistory),1981.141.转引自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5期。
(13)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4)访录者(美)唐德刚,著述者(美)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431—435页。
(15)张学良原著,张之宇校注:《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著》,台北历史智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74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