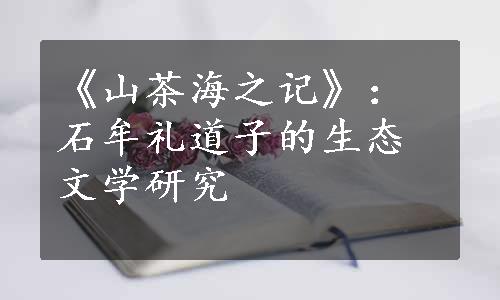
在与我们同时代的作家当中,也有不少写与动物相互感应的。作为其中之一,我想先介绍一下石牟礼道子的作品。石牟礼道子的作品《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yǔ)病》描述了日本战后最大的公害事件——水俣病,因此她早就很出名了。这部作品深入描写了生长在同一个地方饱受水俣病折磨的患者内心深处最深切的共鸣,作为日本环境文学的代表作品,现在引起了外国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山茶海之记》这部自传性作品伴随着童年的记忆,再现了石牟礼道子生长的地方——水俣的风土人情。主人公是四岁左右的作者“小美”。
这里,我想读一下这部作品的第七章“大弯塘”。“大弯塘”是水俣河与大海相接的河口附近的地名。“塘”指的是堤坝一类的地方。有一天,年幼的“小美”离开家,朝着海边的“大弯塘”走去。通向那里的不是最近开始繁华起来的大路,而是“旧路”、“田野中的羊肠小道”。
这个年幼的女孩很久以前就觉得“路”这个东西很不可思议。觉得路是有生命的。关于这个,作者写道:“道路让人觉得好像是一个运动的咀嚼食物的东西”。“我刚会走路的时候看见路上全都是酒后的呕吐物,狗、马、牛的排泄物,老鼠和虫子的死尸。这一场景对一个幼儿来说太惊异了。”“道路是大地和生物的活动中可见的一条痕迹。”
不过,这里所说的道路是人们往来频繁的大路,接下来小女孩要走的是通向海边的路,与因工厂而繁华的大路(不久将成为产生水俣病的近代化的舞台)相反,是一条萧索的旧路、小路。是一条穿过田埂的“冷清的路”。那么,让我们和这个小女孩一起走吧。
首先,最先遇到的是游着成群的鲫鱼和豉虫的“沟河”。小美在这里停了下来。继续描写河里的小动物。出场的有鲫鱼、豉虫、鮠鱼、鲤鱼、虾、淡水螺、泥鳅、河蚬等。小美被这沟河的“繁华”迷住了,边看着边说:“巧遇了住在河里的生物的栖息地,真是太惊讶了。”我眼前浮现出看着河里的生物世界的小女孩的样子。
原本,石牟礼道子的作品世界里,充满了浓密的自然色彩。从某种意思来说,虽然是虚构的作品,也好像是各种各样的自然生物与出场人物、故事联系在一起,或者引出人物和故事一样。这就好像在说人的内心或行为已经和自然共同存在一样。“河里的生物的栖息地”也是诱惑年幼时的作者的自然吧。小美沿着沟河走了一会儿,来到了叫做“盐场的观音堂”的地方。这里能够听到从海上吹来的风的声音。作者如此写道:
不知为什么来到这个佛堂的附近,就被它那凄凉萧条所吓到。佛堂建在了村头、田边和原野边,那里的风景有一些仿造边境或是疆界那样的感觉。不明白这界限想隔开什么,不管是松枝还是佛堂外廊下,走到哪都能看到荒凉的景象。
接下来继续写道:
我在佛堂前驻足,静静地站立了很久,常常面向权现山的方向鞠躬,那是城市中有人居住的方向。再见,再见了。
然后朝着那个“大弯塘”的方向走去。
这样,幼小的“小美”和自己熟悉的“城市”或“人世间”告别,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周围的风景在发生着变化,“稀疏地排列着的房子看上去有点儿像渔村”。因为靠近海,堰川的水里混杂着海潮的味道,水草变成海草。之前我向生活的城市和人世间告别,大自然也由河边的风景向海边的风景转换。这个女孩子能从自然万物的变化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界限的变化。
“小美”好不容易走到了“大弯塘”,已经是秋季的过午了。“大弯塘”被厚厚的芒草覆盖着。“被芒草穗浪的光芒所吸引”,继续前行,那里是这样的地方:
野生的胡颓子林出现在眼前,很小很小就像红色珍珠颗粒那样大小的果实,在荆棘之间一闪一闪忽隐忽现地摇曳着。在背阴处,金泥色的兰菊、野菊,在黄昏之际的天空下连缀起来。就像转瞬即逝的彩虹一样,堤坝消失在大海里。
“小美”走向胡颓子林,就像被邀请似的走进去,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于是我变成了白狐的幼崽,在弯了枝干的胡颓子下,屈着两个前腿放在胸前,缩成了球,“叽叽”地叫着,一下子跳到道路中间,歪着头静静地听沙沙的芒草微微波动的声音,和下面的石头墙脚处波浪迫近的声音。叽、叽、叽,脚下杂乱丛生的野菊散发着诱人的清香,我被这香味所迷住驻足而立。听奶奶们说,一到了晚上,大弯塘边挂满了狐狸出嫁的灯笼。我拔了很多漂亮的小野菊撒在头上。自己是不是真正变成了白狐的幼崽?之后是否又化身为人类的孩子?
秋天的午后,“小美”变成了白狐的幼崽。四岁左右的女孩不知怎么想的离开了家,没想到走到海边就变成了白狐的幼崽。英译这本书的加拿大学者利比亚·莫奈把这个变身的故事叫做“和大自然的同化”,虽然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故事,但我还是要说:“那个啊翻译起来很难”。之所以很难翻译,或许是变身为狐狸的故事在已经流失了的日本传统民俗社会中已经根深蒂固,要是没有相同的知识背景的话,就不会知道为何“小美”能够变身。并且把摘下的野菊往头上撒,这一举动也令人费解。
生物之村
“小美”变为了狐狸。“小美”是狐狸,还是狐狸是“小美”,没有明确的界限。当然这要是只是幻想而已的话,很容易理解。“小美”是存在于幻想中的吧。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其一是因为“小美”年龄小。其二是“小美”所存在的地域社会。作者写道:“大弯塘一带是这片土地的土俗神,以及家眷们特别喜欢聚集的地方”。让我们试着挑出所谈及到的神仙及妖怪们:
山神(老猴、大蛇)、山童、井神、荒神、川太郎、船灵、Gago(一种妖怪)
“小美”的周围,特别是老人们讲述的围绕着这些神仙的传说非常多。换言之,“小美”变身为白狐的幼崽绝对不是幻想。以祖母为首,“村里的老人们各自都有遇见令人喜爱的各路神仙的经历”,把那样的“珍藏的故事”讲给年幼的孩子们。因为作者生长在那样的社会里,是真实的地方,不是幻想什么的。或者说是因为周围的大人们这样深信这实际上是真实的故事。(www.daowen.com)
让我们从小孩的角度来重新思考这个变身故事。心理学者山田洋子(Yamada Yoko,1948—)举了一个例子,幼儿静静地凝视随风摆动的窗帘,被沐浴着阳光的秋天时节枯叶飘落的情景吸引了目光,并进行了如下说明:
那里流动的,是和有节奏的循环世界的节奏一起呼吸的、万物皆有神灵的感觉。是产生于人类和自然只身赤裸地互相接触的地方,并即时地感应到非生命的动态和律动的感觉。是突然惊讶于一些什么变化,忘却了自我,无意识地看得入迷,被吸引的那种生动的感觉。而且是只有生活在自己和他人尚未分化的有共同感觉的世界里的幼儿才能看到的并不特殊的感觉。
山田把这种同调感觉叫做“和环境世界里摆动的生物一起‘唱歌’”。而且,只有“像这样产生共鸣地唱歌”可以说成交流的原点。自己的动作和对方的动作同步协调的现象。回想一下“小美”化身为狐狸的过程,不觉得这确实与“和环境世界里摆动的生物一起‘唱歌’”有关系吗?再试着重新读一下下面的部分:
秋天的过午时分,被芒草穗波的光芒吸引住,野生的胡颓子林出现在眼前、很小很小的就像红色珍珠颗粒那样大小的果实,在荆棘之间一闪一闪忽隐忽现的摇曳着。在背阴处,金泥色的兰菊、野菊,在黄昏之际的天空下连缀起来。就像转瞬即逝的彩虹一样,堤坝消失在大海里。
我们明白了是“芒草穗波的光芒”和胡颓子果实的摇摆吸引了这个少女,将她引入到狐狸的世界。当然也不只有这些,之前沿途看到的污水河里的鱼、生物们,因为它们的摆动,小女孩难道不是已经被诱惑住了吗?这个小女孩,一边沉浸在老人们过去的故事里,一边和周围的自然“一起唱歌”。只有这个“一起唱歌”的经验才可以叫做“交感”,而且这是和自然交流的样子。山田洋子这样说:
人出生在不只有人的声音,而且还有鸟、虫、光、风、土和树的声音混合在一起的余音缭绕的“声音森林”里,被那些多种生物的声音所吸引,在心灵深处合为一体,混合在一起回响。
所谓“声音的森林”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词语。最好也可以认为,年幼的“小美”这个时候进入“声音的森林”,在林中唱歌。那时小美和狐狸之间的界限消失了,相互融合在一起,产生了共鸣,存在于同一首“歌”当中。这个小姑娘和周围的自然一起在唱歌。
在此,我们再稍微地思考一下山田洋子的“声音森林”的概念。重要的是在“声音森林”里不只是人的声音,而是“多种生物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我们说到交流,是人类之间的事,也常常狭义地理解为语言之间的对话。实际上人类交流的对象也包括自然,岂止那样,对于幼儿来说,与人类的声音一样,“鸟、虫、光、风、土和树的声音”也成为交感和交流的对象。
可是这个变成狐狸的故事,并不是亲眼见到实际的狐狸,或许只是从地域社会流传的故事中吸收而来的。因为无论何处都没有描写实际的狐狸。但是,最近,这位作家所写的一篇抗议文《从水俣病来思考生物的村落——从反对产业废弃物最终处理的立场来看》(平成17年12月)中,是这样描述的:
站在水俣河的河口思考。可以看见南边高处的矢筈山。从半山腰的汤鹤河水源到河口有十五公里,穿过水俣市的左边,有一条平静的河流。这条河哺育了这里的人们。祖先们也从这条河得到了身体以及内心上的滋养。并试着稍微写了一些死者们遗物的声音。
若从岸边看,河口的大弯塘高高低低有如波浪一样向前移动。芒草花穗的光芒点缀着各色的野菊。狐狸的家眷在其间穿梭往来。捡贝壳的时候,人与狐狸如同熟人一般。只看脸就能够知道是哪里的狐狸。不同地方的狐狸长得不一样。对面河岸的天草狐由于是长崎血统,所以是通天鼻子。猿乡狐体型较小,如同小猫一般。连叫声也是这个地方的口音。狐狸们聚在一起玩耍,一只狐狸搭话说:“今天去哪儿呀?”另一只狐狸回答说:“噢,现在是去岩滩的好时候。”
由于后半部分写的是死者们的声音,所以会掺杂些方言。为了让人一读就明白,关于大弯塘的故事,也是狐狸的故事在这篇文章中重复提到。水俣市的“生物村”,由于处理厂的建设而消失了,从这一危机感来看,这篇文章是作为抗议文来写的。但化身为狐狸的这个寓言故事,正是由于这一地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生物村”的缘故。石牟礼道子称所谓的“生物村”就是一个把狐狸不叫做狐狸,而是叫“那些人”的地方。而且她还这样写道——“该地区的村民与山、海边的‘那些人’现在也有往来。像这样失去‘民俗’的日本难道不会成为更加刻板的国家吗?”
人类称狐狸为“那些人”,看狐狸脸便能辨别是哪个地方的狐狸,而且还可以互相打招呼。在这里我们能看出在传统社会中人类与动物的共生关系。作家石牟礼道子是以这样的“生物之村”为起点,引出水俣病,而现在正在针对想要在水源处建立工业废物处理厂的现代化社会问题给予尖锐的批判。因为《山茶海之记》讲的是作者小时候的经历,所以人们认为小说的舞台是昭和初期,但是作者将批判水俣病问题的出发点,放在了当地居民和山里、海边的“那些人”来往的“民俗社会”上。
据石牟礼道子所说,化身为狐狸的故事在现代的日本文学当中是极为稀少的,是因为人类化身于动物的这种寓言故事的成立,多半得需要一定的条件。石牟礼道子把它总结为“民俗”。社会必须是“土俗神或者他的家眷”作为“那些人们”同动物或自然共存的社会,并且,住在那里的人们必须坚信那些。但是,近代社会是把这些存在当作迷信来否定它们的社会。近代社会是在切断自然与民俗关系的世界之间的联系之时成立的。英国的美术评论家约翰·伯格在刚才所举的随笔《为什么看动物?》中如此说道:
因20世纪的企业资本主义而得以完结的急剧动荡是从19世纪的欧美开始的,因此连接人与自然的传统全都被破坏了。在这崩坏发生之前,形成包围人类的最初的社会的是动物。这件事情本身大概是在暗示着那其中有很大的不同吧。动物曾经和人类一同存在于这世界的中心。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并且直到不到一个世纪之前,经常和人类一同生活的动物同人类之间交错的视线逐渐消失了。
石牟礼道子所说的“生物之村”这一概念,大概同此处所暗示的“动物曾经和人类一同存在于这世界的中心”这一个想法交相辉映吧。约翰·伯格也认为,在近代化社会以前的社会里,人与动物之间曾有亲密的视线交错。那视线突然消失了,动物们被“边缘化”,也就是被排挤到人类社会的外围去了。
伯格先生的观点中有趣的一点是,动物的“边缘化”的“最终结果”是动物园。因为在动物园中,人与动物的视线是错开的。去动物园的时候难道不是常常听到孩子们说:“在哪儿呢?”“为什么不动了?”“是死了吗?”等等。为什么孩子们是这样认为的呢?那是因为虽然动物园里有各种各样的动物,但是由于人与动物之间并没有构建起任何具体的“关系”,动物与人之间并没有视线交错,不过像是在博物馆参观标本罢了。
伯格先生指出了“动物曾经和人类一同存在于这世界的中心”。由于我们所生存的社会是与这完全不同的社会,所以我虽然不认为我能正确理解其意思,但至少可以说石牟礼道子的世界所讲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这种以动物为中心的社会所特有的。并且这个作家认为不可以破坏“生物村”,至今仍然为此而战斗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