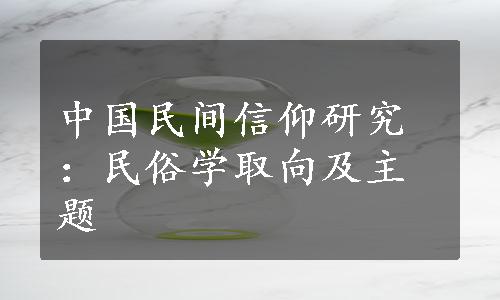
二、民俗学研究取向
中国民间信仰的民俗学研究取向,系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在学科意识尚未精细化或细碎化的年代,中国民俗学内生的传统便是兼顾文本与田野、考古与考现、文化与生活的。民俗学者更是学科上的多栖者。出于“到民间去”、“唤起民众”的文化自觉,他们一开始便将触角伸向了当时社会弥漫的反迷信的意识形态中,从而铸就了现代民俗学执着切入现实生活的品格。如顾颉刚在《妙峰山》中感言“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朝山进香的事是民众生活上的一件大事”,“绝不是可用迷信二字抹杀的”[2]云云;容肇祖在《迷信与传说》中强调研究民俗学离不开中国的迷信,“拼命高呼打倒某种迷信的时候,往往自己却背上了一种其他的迷信”;[3]江绍原在《中国礼俗迷信》中坚称,应该详加考察“迷信”这个概名的“来源和历史、意义与内容”。[4]当然,诸如杨得志所译的Charlotte Burne《民俗学问题格》昭示着民间信仰问题原本就内生于学科意识当中。因此,“民俗性”或“民间性”(迷信)而非“宗教性”成为大家的先入之见。盖缘于“宗教”与“迷信”同属于西洋的舶来品,中国现代民俗学最初并无“民间信仰即宗教”的文化自觉。
尽管说“信仰民俗”或“俗信”研究是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学统之一,改革开放前中国大陆学界毕竟无法避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窠臼,故而期间的成果可略而不论。改革开放以来,民间信仰研究的民俗学取向并未脱离三种研究或写作范式。
(一)“通论性研究范式”的得失
在研究基础薄弱、左的意识形态影响依在的处境下,通论性研究天然而必然地缺乏解释力,但毕竟属于基础性的知识介绍工作,故理应获得一定的历史定位。其中有两种写作模式的得失值得注意。
1﹒民俗学概论模式。在各种版本的《民俗学概论》中,“信仰民俗”或“俗信”成为重要的板块或民俗门类,类同的叙述焦聚于民间信仰的范畴、内涵及外延、性质与特征、类型与功能等问题。这些重复性的文化生产最大的附带功能就在于拨乱反正、文化启蒙、意识形态脱敏:一是民间信仰作为“封建迷信”、“迷信”、“原始遗留物”的紧箍咒日渐解套;二是民间信仰作为“民间文化”的特性获得自明性、合法性的确认。其中,乌丙安《中国民俗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陶立潘《民俗学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钟敬文《民俗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具有典范性的意义。特别是乌丙安突出了民间信仰之“民俗性”而非“宗教性”的本位,几乎成了民俗学界的通识。
近年来,在区域民俗学研究蔚为大观之际,概论式的写作范式克隆迅速,并以“村落民俗志”的形式获得新的生命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颇受重视的今天,他们真诚地达成了地方民俗工作者的再启蒙任务。诸如山东推动的村落民俗志系列,地方教化颇丰,如王君政、王振山编著的《安丘市王家庄镇民俗志》。
2﹒民间信仰通论模式。有关中国民间信仰概论性的研究作品,大多冠以“中国”、“XX省区”、“XX民族”等称谓,带有宏大叙事的特征,在深度、广度方面也有所突破,从而较全景式地展现了本土民间信仰的实态相和存在方式,诸如神灵谱系、历史源流、作用功能、文化特征等。这类作品大多侧重于文本研究和线性描述,亦辅以丰富的田野资料,普遍受到进化论思维的洗礼或西方“宗教”概念的影响,故而立论偏向民间信仰的“民俗性”层面;纵使兼谈“宗教性”者,亦视之“原始宗教的遗存物”,“较低等级的宗教形态”云云。如乌丙安秉持“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区别,金泽最初系以原初宗教形态考论民间信仰。
其中,像李乔的《中国行业神崇拜》,宗力、刘群主编的《中国民间诸神》、金泽的《中国民间信仰》、宋兆麟的《巫与民间信仰》、姜彬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习俗》、何星亮的《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王景琳、徐陶的《中国民间信仰风俗辞典》、乌丙安的《中国民间信仰》、徐晓望的《福建民间信仰源流》、林国平、彭文宇的《福建民间信仰》、汪毅夫的《客家民间信仰》、林国平的《闽台民间信仰源流》、林继富的《灵性高原———西藏民间信仰源流》、范荧的《上海民间信仰研究》、文忠祥的《土族民间信仰研究》都较有代表性。其实,如果我们观察再细腻一些,这一系列书名本身就是现代学术体系的隐喻和记忆,诸如国族(中国)、地域(福建、西藏)、族群(客家、土族)、民族等构成公民社会的共同体想象,已然是研究者的文化表情了。有关民间信仰概论的研究系列由此诞生了现代学术的意义。
(二)“民俗事象研究范式”的重心
近年来,信仰民俗事象研究一直是历史民俗学和比较民俗学的厚爱,并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该取向的成果充分吸纳了史学之重视考辨和文化重建的传统,当然也不忽略寻找史料的田野功夫。这些作品通过描述和比较信仰民俗事象丛,厘清了诸多民间信仰的实态相及其相关的传承性问题。当然,任何范式都不是圆满自足的,诸如欠缺“问题史学”对历史处境的敏锐性、社会人类学对“结构”的敏感性,终究是这类范式的切肤之痛。其中,一贯的“直线思维”(整体只是部分的相加)而非“非线性思维”(整体并非部分的简单相加)的思考和写作模式,无疑大大限制了民俗事象研究的表现力度。作为中国民俗学之不可或缺的学术传统之一,民俗事象研究对于作为民俗学核心的“民俗”的表述力度,事实上从来未过时过。因此,如何拓展该研究取向的路径和方法,从而克服“民俗学在回避生活,生活也在淡忘民俗学”[5]的批评,尚值得期待。
在民间信仰的民俗事象研究取向中,有几个主题值得关注。
1﹒神灵崇拜类型的事象研究。这种研究范式的作者群,涵盖了一批活跃于民俗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学圈的学者,研究范围则涉猎了被称为“汉族”及“少数民族”(其实应该是“族群”)的诸多地区。像上海三联书店“中华本土文化丛书”涉及门神、雷神、水崇拜、自然崇拜等项;刘锡诚、宋兆麟、马昌仪主编的《中华民俗文丛》、刘锡诚主编的《中国民间信仰传说丛书》,几乎囊括了民间典型的神灵类别及相关的传说故事。朱天顺主编的《妈祖研究论文集》、刘慧的《泰山宗教研究》、杨利慧的《女娲的神话与信仰》和《女娲溯源》、邢利的《观音信仰》、叶春生、蒋明智的《悦城龙母文化》、巴莫阿依的《彝族祖灵信仰研究》、姜彬主编的《中国民间文化》1994年“民间俗神信仰”专题、1995年“地方神信仰”专题,堪称这类研究范式中水准之较上乘者。而北京民俗博物馆主持的“东岳论坛”,也有效地推动了华北民间神灵类型的研究。
2﹒特定信仰习俗的事象研究。在涉及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生产方式等信仰习俗方面,学者也投入颇多。有几个系列颇具有特色:
一是丧葬信仰习俗研究。从中国知网检索,仅以“丧葬”为题名的论文达千篇之多,大量涉及丧葬祭祀和祖先崇拜问题。有数篇著作系以东南区域比较见长,也重视文献与田野,以及域外的视野。如郭于华的《死的困扰与生的执著———中国民间丧葬仪礼与传统生死观》对丧葬习俗背后的文化模式的探索,何彬的《江浙汉族丧葬文化》对丧葬习俗的田野比较研究,陈进国的《隔岸观火:泛台海区域的信仰生活》对闽台及南洋地区独特的祖先崇拜现象及买地券习俗的考现学研究,周星一系列文章对福建和琉球丧葬信仰习俗的文化关联性研究。[6]
二是节庆信仰习俗研究。在推动传统节庆纳入国家法定节日的博弈中,节庆信仰习俗成为众多民俗学者关注的对象。诸如中国民俗学会组织出版的《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堪称是民俗学者强化自身“公民性”的一种集体表达,以期彰显节庆之承载民族的历史记忆的教化功能。此外,萧放的《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高丙中的《端午节的源流与意义》、《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7]等文,皆试图清理传统节日民俗复兴中的信仰因素及其现代象征的意义。(www.daowen.com)
三是生产活动中的信仰民俗研究。顾希佳的《东南蚕桑文化》、姜彬主编的《稻作文化与江南民俗》、王荣国的《海洋神灵:中国海神信仰与地方经济》、王元林的《国家祭祀与海上丝路遗迹:广州南海神庙研究》都涉及农耕文化、海洋文化的神灵崇拜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联。
四是民间信仰的图像、器物研究。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关于图像文献研究的方法》一文曾经对于图像在宗教史及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做了深入的分析。近年来,杨郁生的《云南甲马》、汪洁、林国平的《闽台宫庙壁画》、巴莫曲布嫫的《神图与鬼板:凉山彝族祝咒文学与宗教绘画考察》、鞠熙的《碑刻民俗志———北京旧城寺庙碑刻民俗分析及其数据处理》(2007)、[8]叶涛的《泰山石敢当》都从信仰图像或器物的视角做了一些开拓性的讨论。
(三)“民俗整体研究范式”的实践及其限度
我们所谓民间信仰的民俗整体研究取向,是指从活态的信仰民俗事象入手,参与观察在特定语境下的信仰主体的存在方式和生活状态、历史心性和文化表情。其研究特点是重视当下的、日常的信仰生活,透过语境(context)看信仰民俗变迁,既审视信仰民俗事象活态的生成机制,也关照信仰生活的历史、社会、文化背景。在突出民间信仰的“民俗性”、“民间性”、“生活性”、“社区性”、“地方性”的同时,该研究取向也关注“宗教性”要素,诸如仪式过程、象征体系、主体灵验经验或体验、社区性的祭祀组织等。
如果说民俗事象研究取向更关心历史和现实中的信仰者说什么(比如通过经典或文本表达的),则民俗整体的路径更加关注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们如何进行信仰的实践,也就是说,更关心人们在做什么。因此这种研究取向也使得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志成为可能。这表明了当代民俗学的反思能力和自觉性的创新勇气。
当然,当民俗学者倾其热情和心力,注目于民俗中的“民”的日常生活和本土信仰时,同样会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即在努力成为异乡的“熟人社会”的一员的过程中,作为民俗研究者与民俗参与者的身份、立场,多少有混沌化和模糊化的道德风险,甚至可能相互结成一个“话语共谋”的关系。作为一个“被卷入的他者”,“到民间去”的他或她,又将如何面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关联性和互渗性,以及在场的仪式———象征实践对此的潜在强化呢?因此,在一个个活态的民俗表演面前,局里局外,可能都会面临着颇具后现代意味的问题:“哇,民俗学家都到哪儿去了?”是走在希望的田野中,抑或“告别田野”?一个没有了“异乡人”在场的田野图像,将如何辨识“成为他者”的方向感和相对感呢?问题的关键毋宁是,作为一种反思性或批评性的民俗志,如何真诚地叙述这种角色的互渗及民俗再生产。
毋庸置疑,一批“民俗学的叛徒”[9]是在真诚地思考、真诚地实践、真诚地转向,并深入进行社区、村落的民间信仰活动及组织形态的调查的。因为没有村落或社区的民间信仰,也就没有日常生活、民俗生活甚至本土文化价值观、文化个性本身。民间信仰现象俨然成为了检验民俗学整体研究取向得失的试金石。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者群正是这种路径选择的试验者,我们姑且冠以民俗学的“华北学派”。
“华北”,还有民俗学者的“家乡”,因此成为和“华南”一样热闹的田野工作场和想象共同体。诸如刘铁梁倡导在有限的民俗单位中进行整体研究的学术自觉,[10]书写“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并组织跟踪调查河北范庄龙牌会,从而在当代民俗的象征构建及文化再生产的过程中扮演了富有标志性的角色。高丙中更是诗意地描绘了当地以集体崇拜为目的的博物馆的合法化过程,宣称这是“传统草根社团迈向公民社会的历程”的标志云云。在龙牌会这个当代信仰事象的双向构建中,民间智慧与精英智慧珠联璧合,精英的话语在灵巧地解释并消费着、建构着地方知识;年度的大广场加博物馆式的公共仪式展演,成为民俗学者参与构建地方意识的关键象征,中央与地方从此不再遥远。因此,“到民间去”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种态度、一种信仰、一种实践。[11]
在这个共同体的范式中,“语境”是民俗学者在“华北”及“家乡”从事民间信仰整体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和常识,他们从不同的方面深化了对“语境”的理解和阐释。为此,刘晓春曾经以斩截的方式总结陈词:“语境中的民俗学”开始了![12]比如,参与引进这个话语的杨利慧,因为意识到从文本研究神话的局限,尝试贯通女娲神话与女娲信仰,把神话的文本与语境结合起来研究。近年来,她更关注文化语境、社会语境以及历史语境等的综合分析,即民间传统在当代社会和文化中的变迁与重建,及其与历史和当下的各种诉求之间的互动关系等。[13]
因此,有关庙会、祭祀组织、口头叙事等民俗学的传统话题,重新在“语境”中喜临甘露。民俗学家作为另类的“故事的歌手”,显示了“口头叙事”的诗性魅力。民俗志书写的对象,重心已然不在“民之俗”而是“俗之民”在语境中的在场。诸如刘晓春的《一个客家村落的家族与文化———江西富东村的个案研究》、吴效群的《北京的香会组织与妙峰山碧霞元君信仰》、《妙峰山:北京民间社会的历史变迁》、巴莫曲布嫫的《鹰灵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安德明的《天人之际的非常对话———甘肃天水地区的农事禳灾研究》、岳永逸的《庙会的生产:当代河北赵县梨区庙会的田野考察》、王晓莉的《碧霞元君信仰与妙峰山香客村落活动的研究》、尹虎彬的《河北民间后土信仰与口头叙事传统》、叶涛的《泰山香社研究》、杨树喆的《师公·仪式·信仰》,已然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关于信仰研究的系列文本。
诚如刘晓春指出的,“就具体的民俗事象来看,时间、空间、传承人、受众、表演情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不同因素共同构成了民俗传承的语境”,[14]民俗学者对“语境中的信仰民俗”的关注,无疑使得信仰民俗事象的呈现得以纵深化、立体化了。因此,诸如高丙中、巴莫曲布嫫、刘晓春、安德明、岳永逸等的整体的研究,已经很难简单地用“学科”来规定其属性了。
当然,由于一些研究成果的关注点在构成信仰底色的“语境”、“生活”、“整体”等之上,难免忽略了民间信仰的关键要素———“宗教性”本身的整体性思考,如宇宙观、崇拜体系、仪式与象征体系、个体信仰体验(如灵、验)等,特别是针对本土文明体系和地方原生文化的结构关联更因此欠缺整体的观照。由于较为欠缺“宗教性”的反思维度,以及未将民间信仰放在社区的宗教生态处境中考察,其中有些民俗志的立体深度难免不如传统的民俗事象研究本身。
有意思的是,两位“家乡”民俗学者巴莫曲布嫫、安德明已经充分意识到地方信仰民俗志写作的反思性要素以及主体间性的表述本身。前者提出口头传统的田野研究模型———共时的“五个在场”:传统的在场、事件的在场、受众的在场、传承人的在场和研究者的在场;而后者在家乡的民间信仰研究中切身感受了“成为他者”的双向可能性———只有他者。因为陌生人不仅在所谓的“家乡人”当中,而且在我们身上。在“地方”的民间信仰研究当中,关注“语境”的民俗学家止于何处,非“民俗学的叛徒”止于何处,似乎远未成为问题的关键。
概而言之,有关民间信仰的“民俗整体研究”范式更多借鉴的是人类学提出问题的路径,代表了民俗学的人类学转向,[15]推动了人类学式的民俗学的探索进程。这当然是一个充满挑战也充满喜悦的田野之旅、家乡之旅。不过,乐观者可能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难题:民俗学者针对民俗整体的小地方研究时,因为自己心中先有“中国民俗”、“闽南民俗”之类的知识范畴,难免就会先在地假设他者心中都有这些民俗,并在这些范畴之下阅读关于小地方的描述,所以就难以预先评估这种地方语境中的民俗整体研究可能走向细碎化的风险。[16]毕竟民俗学的准确定位首先是研究“民俗之学”,而不是研究“俗民之学”,否则将继续存在着学科合法化的危险。
因此,有关民间信仰的民俗事象研究,如鸟之两翼,不可或缺,在参与构建民俗学的学科谱系亦贡献良多。如果说有关民间信仰的通论式范式和民俗事象范式关注的是一个个独立的苹果、梨、香蕉的形态,民俗整体研究范式则要关注整棵的苹果树、梨树、香蕉树,乃至生长的土壤和气候,而宗教人类学或宗教现象学的研究取向,甚至还应思考抽象的果树乃至森林自身。田野工作甚至未必是宗教人类学家当且仅当的使命和任务。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