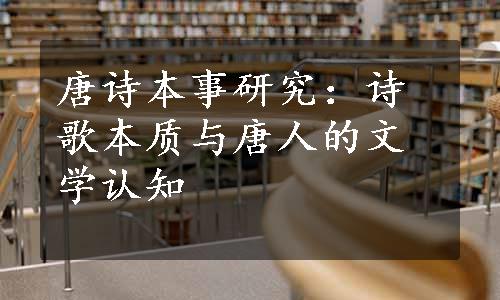
第一节 诗歌的本质
唐诗本事反映唐人对文学的本质,特别是诗歌本质的认识,其中,神理为文和情志为文的观念最为突出。
一、诗是神理的表现
唐诗本事中有一些梦得文才诗思的故事,如下列本事:
列子终于郑,今墓在郊薮,谓贤者之迹,而或禁其樵采焉。里有胡生者,性落拓,家贫。少为洗镜锼钉之业,倏遇甘果、名茶、美酝,辄祭于列御寇之祠垄,以求聪慧,而思学道。历稔,忽梦一人,刀画其腹开,以一卷之书,置于心腑。及睡觉,而吟咏之意,皆绮美之词,所得不由于师友也。既成卷轴,尚不弃于猥贱之事,真隐者之风,远近号为“胡钉铰”。……其文略记数篇,资其异论耳。《喜圃田韩少府见访》一首:“忽闻梅福来相访,笑着荷衣出草堂。儿童不惯见车马,争入芦花深处藏。”又《观郑州崔郎中诸妓绣样》曰:“日暮堂前花蕊娇,争拈小笔上床描。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江际小儿垂钓》曰:“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恐畏鱼惊不应人。”(《云溪友议》卷下“祝坟应”)
诗人许浑,尝梦登山,有宫室凌云,人云:“此昆仑也。”既入,见数人方饮酒,招之,至暮而罢。赋诗云:“晓入瑶台露气清,坐中唯有许飞琼。尘心未断俗缘在,十里下山空月明。”他日复梦至其处,飞琼曰:“子何故显余姓名于人间?”座上即改为“天风吹下步虚声”,曰:“善。”(《本事诗·事感第二》)
(郑)颢居戚里,有器度。大中时,恩泽无对。及宣宗弃代,追感恩遇,尝为诗,序曰:“去年寿昌节,赴麟德殿上寿,回憩于长兴里第。昏然昼寝,梦与十数人纳凉于别馆。馆宇萧洒,相与联句。予为数联,同游甚称赏。既寤,不全记诸联,唯省十字云‘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乃书之于楹。私怪语不祥,不敢言于人。不数日,宣宗不豫,废朝会,及宫车上仙,方悟其事。追惟顾遇,续石门之句为十韵云:‘间岁流虹节,归轩出禁扃。奔波陶畏景,萧洒梦殊庭。境象非曾到,崇严昔未经。日车乌敛翼,风动鹤飘翎。异苑人争集,凉台笔不停。石门雾露白,玉殿莓苔青。若匪灾先兆,何当思入冥。御炉虚仗马,华盖负云亭。白日成千古,金滕 九龄。小臣哀绝笔,湖上泣青萍。’”未几,颢亦卒。(《旧唐书·郑颢传》)
九龄。小臣哀绝笔,湖上泣青萍。’”未几,颢亦卒。(《旧唐书·郑颢传》)
《旧唐书·钱徽传》记载的钱起夜吟而得鬼谣的故事与上引故事同类。除本事中的梦得文才故事外,还有其他一些同类故事。如《旧唐书》卷一四九谓张 儿时梦见紫色大鸟,因有文章;卷九四记李峤儿时梦有神人遗之双笔,从此渐有学业;卷一八九记尹知章少梦神人凿开其心,以药纳之,于是尽通经义。又《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谓王勃“少梦人遗以丸墨盈袖”,《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谓李白少时梦笔生花,《太平广记》卷一八○引《闽川名士传》记林藻应举试珠还合浦赋,因假寐梦人告语,叙珠来去之意,主考谓有神助,等等。
儿时梦见紫色大鸟,因有文章;卷九四记李峤儿时梦有神人遗之双笔,从此渐有学业;卷一八九记尹知章少梦神人凿开其心,以药纳之,于是尽通经义。又《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二谓王勃“少梦人遗以丸墨盈袖”,《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谓李白少时梦笔生花,《太平广记》卷一八○引《闽川名士传》记林藻应举试珠还合浦赋,因假寐梦人告语,叙珠来去之意,主考谓有神助,等等。
梦得文才故事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即已大量产生,其中一些为著名故事:传说罗含梦五色鸟入怀,而有文章[1];江淹梦郭璞索还五色笔,因失文才[2];王珣梦人授以如椽巨笔,后作烈宗哀册谥议[3];谢灵运寤寐之间因见惠连,而成佳句。这一时期是梦得文才故事出现最多的时期。
这些故事都无一例外地宣扬文才神授,都认为文才的得失出于神灵的予夺。故事中,飞鸟入怀是神灵意志的体现,所梦之人也不过是神灵的化身。人之有文才,完全是上天的赐予,神灵的垂示[4]。
与文才神授观念相应的还有诗为预言的说法。唐诗本事中有诗谶一类故事,这类故事宣扬诗歌预示凶吉的神秘功能,认为诗歌可以预言人的败落、死亡,或职官的迁升改易。这种神秘主义的宿命思想无疑源于古老的天命论,是对主宰人类的超自然的神灵的信仰。在信仰者看来,谶诗是神灵对人的未来命运的暗中垂示或昭告。
不管是文才神授故事,还是诗为预言故事,都反映了人们对于文学起源和文学本质的认识,即文学源于神灵的启示,文学是神理的表现。
文学是神理的表现,这是战国后期至汉代以来的普遍观念。这种观念源出《易传》。《易传》中《文言》是对乾、坤两卦的解说,后世循名责实,以“文言”为言之文者。清代阮元相信汉人关于孔子作《易传》的说法,甚至认为“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文言说》)。那么,《文言》即是时人观念中的文学。后世对此虽无异议,但对其中所体现的文学观念解说不一。《经典释文·周易音义》云:“文言,文饰卦下之言也。”《周易正义》引庄氏曰:“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皆文饰以为文言。”都以“文”指文饰、辞采。但晋人姚信为《文言》作注时则从义理立论,他说:“乾坤为门户,文说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后《周易正义》引而申之,认为“今谓夫子但赞明易道,申说易理,非是文饰华饰,当谓释二卦之经文,故称文言。”把“文”归结为深奥的义理。清末章炳麟承袭此说,《国故论衡·文学总略》说:“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盖谓不能举典礼,非苟欲润色也。《易》所以有《文言》者,梁武帝以为文王作《易》,孔子遵而修之,故曰《文言》,非矜其采饰也。”亦谓孔子只是释乾、坤两卦经文,阐明《易》道,申说义理,并非文饰华采。此外,阮元《文言说》以“文”为声偶,但遭到章炳麟的有力辩驳。在对《文言》的诸多解说中,以“文为义理”说更能揭示《易传》的文学观念。《文言》虽只解说乾、坤两卦,但据姚信所注,其义理实统摄六十四卦,那么《文言》应该是阐明整个《易》道的。《周易》历来被视为谈天之书,是阐明天道神理的。《系辞》下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说卦》亦谓:“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文言》既是阐明易道,那么其中义理即是神理,《文言》之为言之文者,以其通于神理之故。《易传》实非孔子所作,各篇成书年代不一。一般认为《文言》成于战国后期,那么,神理为文的观念当在战国后期即已产生。
由《文言》引出的这一神理为文观念对后世文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刘勰对神理为文曾给予明确的理论表述。《文心雕龙·原道》在探讨文学的产生及其本质时说:
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玉版金镂之实,丹文绿牒之华,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
刘勰认为,《文言》之为文,是因为它体现了“天地之心”。在这里,“天地之心”喻指宇宙精神,即下文所谓“神理”。在《易传》中,“神”有不同意指,但是,作为神明作用的“神理”显然是指上天的意旨,即天命,《文心雕龙》正是在此意义上运用“神理”这一概念的。不仅如此,刘勰还把神理看成是神灵的授予。他认为“《河图》孕乎八卦,《洛书》韫乎九畴”,相信“玉版金镂”、“丹文绿牒”之说,肯定天命神授,把文学看作神灵的启示,将神理为文的观念建立在神授观念的基础上。刘勰的文才神授观受《易传》和谶纬之学的影响,是战国后期以来普遍存在的观念。
从前引神授故事看,文才神授观在唐五代仍普遍存在,这一普遍存在的观念对唐代诗人和诗论家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文才神授观具体表现为将人之难得诗才和诗之难得佳句视为神灵的赐予,唐代诗人和诗论家论诗多涉及后者,与前者较少关联。
受此观念影响的诗人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诗圣”杜甫。杜甫诗论明显受文才神授观念的影响,由下列诗句可见出这一影响: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诗镜铨》卷一《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但觉高歌有鬼神。(《杜诗镜铨》卷二《醉时歌》)
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诗镜铨》卷四《独酌成诗》)
诗应有神助,吾得及春游。(《杜诗镜铨》卷八《游修觉寺》)
挥翰绮绣扬,篇什若有神。(《杜诗镜铨》卷一四《八哀诗·赠太子太师汝阳郡王琎》)
所谓“有神”、“有鬼神”,与“有神助”意同。“神助”一语出自谢灵运寤寐间而得佳句的故事。钟嵘《诗品》卷中引《谢氏家录》记载:“康乐每对惠连,辄得佳语。后在永嘉西堂,思诗竟日不就。寤寐间忽见惠连,即成‘池塘生春草’。故尝云:‘此语有神助,非我语也。’”谢灵运梦得文思故事是时人文才神授观念的产物,杜甫诗屡屡言及“有神”、“神助”等,表达的也是同一文学观念。(www.daowen.com)
杜甫之后,受此观念影响的是诗人兼诗论家皎然。皎然《诗式》序云:“其作用也,放意须险,定句须难,虽取由我衷,而得若神授。”[5]卷一“取境”云:“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皎然认为,诗歌创作中佳句的获得并不单纯取决于创作主体的意识活动,也不完全受意识的控制。他不能解释这一现象,只好援引了传统的文才神授观念。皎然自称是谢灵运的后裔,论诗也以谢氏为法,他不仅称赞谢诗“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6],还特别欣赏谢诗中“池塘生春草”一句,并引梦得文思故事,谓诗有“神助”。由此不难看出《诗式》所谓“神授”、“神助”等语与六朝文才神授观念的关系。
除杜甫、皎然诗论外,类似的观念还出现在白居易的诗论中。白居易在《刘白唱和集解》中论刘禹锡诗说:“如梦得‘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句之类,真谓神妙。在在处处,应当有灵物护之。”[7]仍是推崇诗中佳句。所谓“神妙”,指诗句极妙参神,达到人力难以企及的出神入化的境界,而所谓“灵物护之”亦即“神助”之意。
文才神授观其实反映了前人对作家天赋及创作灵感的认识。因为不能真正了解天赋、灵感获得的原因,在解释天赋、灵感现象时,梦得文才故事将其归结为上天的赐予,并且采用了粗糙的神灵感应的形式。唐代诗人及诗论家虽承袭了“神授”的观念,但逐渐扬弃了神灵感应的原始形式,观念的把握趋于理性。在他们看来,天赋和灵感既超越人力,也基于人力。后者或得力于读书万卷的勤学,或出于冥思苦想,或由于逐渐磨练的艺术敏感。应该说,这些基于创作实践所获得的认识是接近真实的。
二、诗是情志的表现
唐诗本事专集《本事诗》和《抒情集》的编者是倾向于“诗以抒情”的。《抒情集》以“抒情”名其集,标明所集诗歌的抒情性质。《本事诗》对此则有明确的表述,《序》云:“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慨。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虽著于群书,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这一段话关于诗歌本质的认识源出《毛诗序》。《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序》接过“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同时基于诗、乐一体的观念,吸收乐论中乐生于人情的论述,形成情动言发、诗以言志抒情的观念。《本事诗》序重申《毛诗序》关于诗歌本质的观点,显然是强调诗歌的抒情性质,是将抒情作为本事诗最重要的特征。
这一观念也反映在《本事诗》的编纂中。《本事诗》将所选本事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其中“情感”、“事感”、“怨愤”中的本事诗均为“触事兴咏”的抒情诗。“情感”类本事为男女情事,其中诗歌为爱情诗,或吟咏男女情爱,“情感”之“情”专指男女之情。这一类目的确立当是受南朝文学观念的影响。梁萧纲和萧绎论诗主情,其所谓“情”已专指男女之情。萧统《文选》卷一九“赋癸”专设“情”类,收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及曹植《洛神赋》,所选赋篇均是描写男女情事。“情”下李善注引《易》云:“情者,外染也,色之别名。”《本事诗》中“情感”一类的设置当本于此,这一名目中的“情”与序中所言“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之诗情有广狭之分,并非同一概念。“事感”类本事诗所涉及的情感形式较为复杂。有人世兴衰,如明皇听唱李峤诗;有政治恩怨,如刘禹锡游玄都观诗;有朋辈聚散,如元稹题黄明府诗;有感物伤春,如白居易杨柳诗。等等。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均可入此类。“怨愤”类本事记宋之问《明河篇》故事、李适之《罢相》故事、贾岛题兴化池诗事等,多寓怨愤之情。其他几类本事中也有“触事兴咏”的抒情诗。《抒情集》今已散佚,现存佚文中的诗歌多抒情言志之作,叙男女情爱的“情感”一类本事也为数不少,编辑取舍与《本事诗》相近。
本事诗的抒情性质首先源于其“触事兴咏”的特点。中国古代关于音乐起源的理论中有所谓“感物”之说,《乐记》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这一理论影响到诗论。刘勰《文心雕龙·物色》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都认为人之感物生情,情形于言而为诗。唐以前的“感物”说又包含“感事”之义。《诗品序》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序中“春风春鸟”等,乃物之感;“楚臣去境”等,乃事之感。钟嵘之前,班固认为诗歌的创作乃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对诗歌与诗事、诗歌与诗情的关系作了明确说明。感物理论以情之感发为其枢机,物感事感必表现为情之感,《本事诗》序所谓“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即明此意。本事诗多是感于事而深于情的诗歌,因而最能体现诗歌的抒情性质。
“诗言志”与“诗缘情”内涵有所不同。一般认为,“诗言志”是言其心胸怀抱,所言情志必须符合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义”,其情多为世情,其诗关乎政教。“诗缘情”则多抒写一己私情,其情不受儒家伦理道德规范的约束。“诗言志”与“诗缘情”曾经判然为二,但在唐人那里,二者并不泾渭分明,有时甚至混而为一。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诗大序正义》云:“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文选》卷一七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李善注云:“诗以言志,故曰缘情。”李周翰注云:“诗言志,故缘情。”前者以“情”疏“志”,后者以“志”注“情”,“情”与“志”已统合为一。
这种“情”、“志”不分的情况在《本事诗》和《抒情集》中也有所反映。如《本事诗》所载李章武赠僧诗,对僧尼试经敕令提出委婉的批评;张九龄《海燕》诗以物自喻,明其与世无争的胸怀;贾岛题兴化池诗也借物兴咏,批判豪贵对百姓的侵夺。这些本事诗,或明心迹,或寓讽谕,乃“志意之所之适”的言志之作。《抒情集》中收有于 、唐备“颇干教化”、“咸多比讽”、“皆协骚雅”的诗歌[8],郑还古受谤被贬时所作《望思台》等诗[9],还有狄常侍因“拾遗孟昭图上疏切直,蹈于非罪”所作的伤悼诗[10]。这些诗歌涉及世道人心、伦理道德,关乎政教,可归入言志一类。这种“缘情”、“言志”互相参杂的情况正反映了唐人对“情”与“志”的理解。
、唐备“颇干教化”、“咸多比讽”、“皆协骚雅”的诗歌[8],郑还古受谤被贬时所作《望思台》等诗[9],还有狄常侍因“拾遗孟昭图上疏切直,蹈于非罪”所作的伤悼诗[10]。这些诗歌涉及世道人心、伦理道德,关乎政教,可归入言志一类。这种“缘情”、“言志”互相参杂的情况正反映了唐人对“情”与“志”的理解。
唐人对情志的理解较前人也有所深化。他们注意到诗中情志所反映的诗人所独有的禀赋气质、心胸抱负及其对人生穷达升沉的深刻影响,一些本事表达了这一认识:
咸通中,王建侍御吟诗寒碎,竟不显荣。乾符末,李洞秀才出意穷愁,不登名第。是知诗者陶人情性,定乎穷通。故韦庄补阙有《长安感怀》云:“大道不将炉冶去,有心重筑太平基。”此则苞括生成,果为台辅。长兴末,何仆射瓒有《蜀城书事》云:“到头须卜林泉隐,自愧无能继卧龙。”诗后十旬,得疾而卒。(《鉴诫录》卷九“分命录”)
杜荀鹤曾得一联诗云:“旧衣灰絮絮,新酒竹
 。”时韦相国说右司员外郎,寄寓荆州,或语于韦公,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即京兆大拜气概,诗中已见之矣。或有述李频诗于钱尚父曰:“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于诗句,苦哉!”(《北梦琐言》卷七“韦杜气概”)
。”时韦相国说右司员外郎,寄寓荆州,或语于韦公,曰:“我道‘印将金锁锁,帘用玉钩钩。’”即京兆大拜气概,诗中已见之矣。或有述李频诗于钱尚父曰:“只将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尚父曰:“可惜此心,何所不用,而破于诗句,苦哉!”(《北梦琐言》卷七“韦杜气概”)
朱勰,仕江南为县令,甚疏逸,有诗云:“好是晚来香雨里,担簦亲送绮罗人。”李璟闻之,处以闲曹。又有僧庭实献诗云:“吟中双鬓白,笑里一生贫。”璟闻云:“诗以言志,终是寒薄。”以束帛遣之。(《诗话总龟·前集》卷三引《诗史》)
这些本事都力图说明诗情与性分的关系。诗能陶冶人之性情,但诗之情志又是诗人情性的表现。人之性情各异,在本事作者看来,有的胸怀广阔,气概非凡,如韦庄、韦说等;有的生性寒薄,气度狭小,如王建、李洞、杜荀鹤、李频、僧庭实之流,或性情疏逸,如朱勰。性情不同,诗之情感志意亦有所不同。前者志向远大,可为“大器”,后者寒碎穷愁,毕竟为“小器”。由诗情诗意可推知人之情性,由此情性可定人之穷通。《鉴诫录》将此归入“分命”,认为这是性分决定命运。文学理论中有“性格即命运”的重要命题,其实,这一命题在唐诗本事中已有生动的表现。
诗是情志的表现,与此相关,诗还是欲望的替代性满足。感物感事,往往激发诗人潜在的本能欲求,这些欲求在现实中或难以实现,于是借助诗歌,在虚幻的想象中得到满足。这一创作倾向在有关男女情爱的诗中表现尤为明显。《云溪友议》卷中“谭生刺”记载:
真娘者,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行客感其华丽,竞为诗题于墓树,栉比鳞臻。有举子谭铢者,吴门秀逸之士也,因书绝句以贻后之来者。睹其题处,经游之者稍息笔矣。诗曰:“武丘山下冢累累,松柏萧条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
此一本事揭示世人题诗真娘墓的隐微心理。所谓“感其华丽”,就是感怀佳人的美艳,即谭生所谓“重色”。在谭生看来,武丘山下荒冢累累,在在处处萧条愁人,世人独于真娘墓树题诗,而不及其他,岂非重色心理作怪。唐人题真娘墓诗,本事未引,但从沈亚之《虎丘山真娘墓》诗中或可见其神貌风情之一斑。其诗云:
金钗沦剑壑,兹地似花台。油壁何人值?钱塘度曲哀。翠余长染柳,香重欲薰梅。但道行云去,应随魂梦来。(《全唐诗》卷四九三)
由真娘生前的风尘生涯生出即今神魂来去、为雨为云的想象,“翠余”两句将想象幻化为现实的景象,偏于感官感受。如果说诗以尽欲倾向在此诗中尚隐约朦胧,那么,在王轩遇艳故事中此一倾向显露无遗。王轩《题西施石》诗云:“岭上千峰秀,江边细草春。今逢浣纱石,不见浣纱人。”已露希艳之意。本事中的西施现身酬诗、共为鸳鸾之会的香艳故事是王轩诗歌内容的延伸,是对诗中隐含的娱情意图的揭示。当然,本事作者读其诗而心往神驰,因而造为此一艳想故事,通过自居作用,同样获得想象的满足。应该说,此一故事也是这一心理活动的外化。类似的故事还有李群玉《黄陵庙》诗事。《黄陵庙》诗本无希艳之意,但本事据诗中一些描写附会段成式诗“曾话黄陵事,今为白发催”两句,虚构娥皇、女英二妃现身、与李群玉约为云雨之游的艳遇故事。此一艳想完全出自本事造者创造性的诗歌解读,正像诗人通过想象与创作获得欲望的替代性满足一样,读者通过阅读和想象也能获得同样的满足,《黄陵庙》诗事也正是这种自我满足的产物。后来,《青琐高议》取此事为因由,恣意铺张,附会诗人李远收藏贵妃罗袜、心怀艳想的故事,其中人物具有明显的恋物癖及色情狂倾向,故事对性爱心理的表现较唐诗本事走得更远。
钱鍾书在《诗可以怨》中论及文学的慰藉和补偿功能,曾引李渔《笠翁偶寄》中的一段话:“予生忧患之中,处落魄之境,自幼至长,自长至老,总无一刻舒眉。惟于制曲填词之顷,非但郁藉以舒,愠为之解,且尝僭作两间最乐之人。……未有真境之所为,能出幻境纵横之上者。我欲做官,则顷刻之间便臻荣贵。……我欲作人间才子,即为杜甫、李白之后身。我欲娶绝代佳人,即作王嫱、西施之原配。”[11]这末一幻想可为上引诗歌及本事的注脚。唐人诗歌及小说好以后妃、神女及历代名姬为情爱的想象对象,原因也在此。西方文学理论将文学创作视为“白日梦”,视为受压抑的欲望的满足。弗洛伊德更把这一观点建立在一套深度心理学的基础上,认为文学艺术创作是对本能的情欲的疏解,是“本我”的升华。本事中的幻想故事正是这样的“白日梦”,正是受压抑的欲望的替代性满足。
与西方较为开放的创作态度不同,中国古代对此一创作倾向常常表现出不以为然的态度,如那些描写男女情爱的宫体诗因其香艳绮靡一直作为诗歌创作中引以为戒的厉禁。在当时的儒者观念中,为诗重色,非大雅之思,是不宜公行和倡导的。写男女之情,须寓教训,有寄托,非此则无益。下引本事即表现此一文学观念:
故太尉李德裕镇渚宫,尝谓宾侣曰:“余偶欲遥赋《巫山神女》一诗,下句云‘自从一梦高唐后,可是无人胜楚王’。昼梦宵征巫山,似欲降者,如何?”段记室成式曰:“屈平流放湘沅,椒兰友而不争,卒葬江鱼之腹,为旷代之悲。宋玉则招屈之魂,明君之失,恐祸及身,遂假高唐之梦以惑襄王,非真梦也。我公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亦恐非真。”李公退惭,其文不编集于卷也。(《云溪友议》卷上“巫咏难”)
段成式认为,宋玉著《高唐》、《神女》赋,并非是写男女情爱,而是隐含政治的深意。李德裕“作神女之诗,思神女之会,唯虑成梦”则背离这一隐寓传统。其语虽以“亦恐非真”委婉回护,但批评之意是明显的。李德裕自然是接受了这一批评,“李公退惭”等语与《谭生刺》中“经游之者稍息笔矣”乃出于同一心态,这就是对“重色”心理的避讳,对鉴诫、寓托观念的认同。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