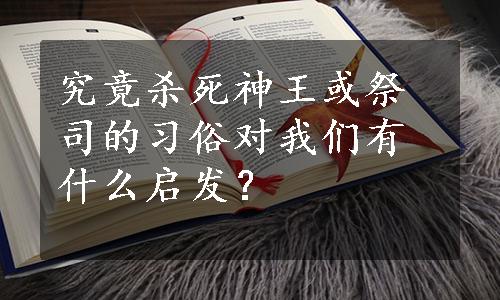
第一节 降灵节的化装游乐者
我们最后还需要弄清楚究竟杀死神王或祭司的习俗对我们所探讨的特定题目有什么启发呢?在本书前面一部分我们谈到有理由假定内米地方的林中之王是被看作树精或植物精灵的化身,在他崇拜者的信念里,作为化身,他就具有使树木结果、庄稼生长等等的魔力。所以,他的崇拜者必定非常重视他的生命,也许对于他的生命有一整套详细的预防手段或禁忌,像许多地方一样,人神的生命都有预防手段或禁忌来加以保护,防御魔鬼或巫师的恶意侵害。但是我们已经说到过,附属于人神生命的价值本身就需要他暴死,作为保存生命、避免年老衰弱的唯一手段。同样的推理也适用于林中之王,他也必须被杀死,为的是让附在他身上的神灵可以完整无缺地转入他的继续者身上。他可以为王,直到比他更强壮的人把他杀死。这条规定可以说是既保证他的神性与生命精力充沛,又保证一旦他的精力初见不济时就转给适当的继承者。只要他能用强壮的手保持住他的王位,就可以推定他的自然精力并未减退,而他之败于或死于他人之手就证明他的精力开始衰退,也正是他神灵生命该寄居在一个不那么衰朽的躯壳里的时候。这样来说明林中之王必须被他的继承者杀死的规定,至少能使这条规定完全可以理解。希卢克人的理论和实践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说明,希卢克人在神王健康退初露迹象时即将他处死,唯恐他的衰老会引起庄稼、牲口和人的精力相应衰退。还有,奇托姆的类似情况也能证实这种说明:世界的存在都被认为系于奇托姆的生命,所以,老弱迹象一出现,他的继承者就将他杀死。而且在较晚的时候,卡利卡特国王任职的条件与林中之王任职的条件是一致的,只不过后者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受到候补人的袭击,而卡利卡特王只可以十二年受一次袭击。而卡利卡特王只要能够对抗一切来人,保住自己,他就被容许继续统治下去,这是为了履行定期杀死他的老规矩所做的缓和手段,所以我们可以推定给林中之王的类似许诺,也是一种为了履行定期终结时将他处死的老规矩所做的缓和手段。在两种情况下,新规矩至少给神人一个活命的机会,照老规矩他是没有这个机会的。也许人民同意这种变更是由于想到只要神人能持剑对付一切攻击、保住自己,那就没有理由害怕他身体出现致命的衰颓现象。
如果能举出证据,证明在北欧有一个定期杀死林中之王的相应人物即化身为树精的风俗,那么从前在定期终结时原要处死林中之王不许他有活命机会这个假设就被证实了。事实上,这种风俗在农民的节日活动中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对于上述的说法,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吧!在下巴伐利亚的尼德波林地方,降灵节期间扮作树木精灵的人——人们称他为芬格索——从头到脚都披着树叶和鲜花。他头上戴一顶尖尖的高帽子,帽尖落在他肩上,帽子上只给他眼睛留两个洞,帽上铺满水藻,顶上覆盖着芍药花。他上衣的袖子也是水草做的,他身上其余部分也裹着赤杨叶和榛树叶。他的两边各有一男孩,牵着他的胳臂。这两个男孩还拿着出鞘的宝剑,其他参加游行队列的人也大部分带着宝剑。在每一个他们希望得到礼物的家门口停下来,人们躲着往披叶子的孩子们身上浇水,他湿透了,大家都高兴,最后他走进水深齐腰的河里,于是有一个男孩站在桥上,假装要砍掉他的脑袋。在施瓦本的瓦姆林根地方,一二十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降灵节的星期一那天穿上白上衣白裤子,腰围红巾,巾上系着宝剑。他们骑马到树林里去,两个吹鼓手吹着喇叭在前带路。在树林里他们砍下叶子多的橡树枝,把他们之中最后一个骑马出村的人从头到脚裹在树枝里。不过,他的两条腿是分开来包的,好让他能够再骑上马背。他们还给他按上一个老长的假脖子,上面装一个假头和一个假脸。然后砍一棵五朔树,通常是十英尺高的白杨树或山毛榉,给五朔树装上花手巾、绸布条之后就交给一个特定的“背五朔树的人”。于是骑马的队伍伴着乐声和歌声回到村里去。行列中出色的人物包括一个黑脸头戴王冠的摩尔王、一个铁胡须博士、一个班长和一个刽子手。他们在村里的绿草地上停下来,每个人物说一通押韵的话。刽子手宣布穿树叶的人已被判死刑,并砍掉他的假头。然后骑马的人们都跑到五朔树那里去,五朔树原已在不远的地方竖立好了,而头一个到达且把树拔起的人就得到树和树上的装饰品。这个仪式每隔两年或三年举行一次。
在萨克森[1]和图林根[2],有一个降灵节的仪式叫作“把野人赶出灌木林”或“把野人抓出树林”。一个小伙子穿着树叶或水草称作“野人”。他躲在树林里,村里其他的男孩出去找他。他们把他找出来,当俘虏牵出树林,用空枪对他开火。他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但是一个医生打扮的男孩给他放血,他又醒过来。他们见了大喜,把他紧紧地绑在车上,送他进村,他们在村里告诉所有的人他们是怎样抓野人的。每一家都给他们礼物。在埃尔茨吉伯奇[3]山区,17世纪初期每年忏悔节都有以下的习俗。两个人装扮成野人,一个披着灌木树枝和水草,另一个披着稻草,让人牵在街上走,最后带到市场上去,他们在那里让人追逐、射枪、刺杀。他们倒下之前,摇摇摆摆,做着怪动作,他们从随身带的囊袋里向人们喷血。他们倒下时,猎人把他们放在木板上,带到酒店去,矿工们走在他们旁边,用采矿的工具敲击出阵阵闹声,好像他们抓到一头好猎物。与此相近的忏悔节另一风俗还在波希米亚的施鲁坎诺地方流行。一个人扮成野人,被人赶过几条街,最后来到一条拦着绳子的窄胡同里。他被绳子拌住,倒在地上,让他的追逐者赶上来抓住。刽子手赶上来,用剑刺破装了血的水泡(野人原已把水泡带在身上),于是野人死了,流的血染红了地面。第二天一个样子扎得像野人的草人放在担架上,一大群人跟着,拿到池子旁边,由刽世手扔进池里。这个仪式叫做“埋葬狂欢节”。[4]
在塞米克(波希米亚),在降灵节的星期一那天流行斩王头的风俗。一群青年人打扮起来,每人都腰缠一根树皮,带一把木剑和柳木做的号角。国王穿一件缀满花朵的树皮袍子,头戴缀了花枝的树皮王冠,脚上缠着羊齿植物,一副假面具掩藏着他的脸,手拿一根山楂树嫩枝作王的权杖。一个男孩牵着他脚上拴的一根绳子,穿过村庄,其余的人则在他周围跳舞、吹号、吹口哨。每到一个农家,国王都被赶着绕屋跑,队伍中有一个人用剑击一下国王的树皮袍子,打得它发响,然后讨赏钱。砍头的仪式在这里有些模糊,在波希米亚其他地区则更近于真实。如在柯尼格拉兹地区的某些村庄里,在降灵节的星期一那天,女孩子们聚在一棵菩提树下,男孩子们聚在另一棵菩提树下,都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配上绸带。男孩子给王后编一个花冠,女孩子给国王也编一个。他们选出国王和王后之后,排成双行列队到酒店去,司仪的人从酒店阳台上宣布国王和王后的名字。这时一面奏乐,一面授予两人国王和王后的徽章,戴上花冠。然后有人站在板凳上,指责国王各种违法的事,诸如虐待牲口之类。国王求诸证人,于是开庭审讯,终结时,法官宣判国王“有罪”或“无罪”,法官带一根白棍子作为执法的标记。如判为“有罪”,法官就折断他的棍子,国王跪在一块白布上,所有的人都脱下帽子,一个士兵拿三顶或四顶帽子,一个叠一个地放在国王陛下的头上。于是法官三次高呼“有罪”二字,命司仪将国王斩首。司仪从命,用木剑击落国王的帽子。
不过,对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些假行刑中最有意义的也许是下述波希米亚的这样一个例子。在皮尔孙地区(波希米亚)的某些地方,当降灵节的星期一来到,国王穿上树皮,缀上花卉和绸带,戴一顶金纸王冠,骑一匹马,马身上也铺了花。他由一个法官、一个刽子手和其他人物随从,后面跟一队骑马的士兵,骑马到村里的场上去,在那里五朔树下用绿树枝扎了一个小屋或亭子,五朔树是棵杉树,新砍下来的,去掉树皮,缀上花卉和绸带。骑马的队伍在批评村里的妇女和姑娘,并将一只青蛙斩首之后,来到一条又宽又直的街上原先定好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他们划出两道线,国王开始逃跑。人们让国王先跑一步,他尽快地骑马跑开,整个队伍都追赶。如果他们没有赶上他,他就再做一年国王,他的伙伴在晚上必须在酒店替他付钱。但如果他们赶上他,将他捉住,就用榛树枝抽他,或用木剑打他,并强迫他下马。然后刽子手就问:“我要将这个国王斩首吗?”回答说:“斩首。”刽子手挥起斧头,并说:“一、二、三,让国王人头落地!”他于是砍掉国王的王冠。在旁观者的高叫声中,国王倒在地下。然后把他放在尸架上,抬到最近的农家去。
我们不可能看不出这些假装杀掉的人物中,大多数是代表树精或植物精灵的,因为人们认为它是在春天出现。扮演者所穿的树皮、树叶、花卉以及他们出现的季节都表明他们与草王、五朔树王、绿衣杰克,以及我们在本书前面已考察过的春天草木精灵的其他代表属于同一类。好像是为了在这一点上取消任何可能的怀疑,我们发现两个例子其中被杀的人都直接与五朔树有关,正如五朔王、草王等等是树精化成的人身一样,五朔树是树精的非人的化身。所以,用水泼芬格索以及他走到水齐腰深的河里,无疑都是求雨的巫术,正像我们提过的那些求雨巫术一样。
但是,如果这些人物确是代表春天的草木精灵,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要杀他们?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在春天最需要草木精灵尽力的时候,却将他杀掉,目的何在呢?对于这个问题,唯一可能的回答似乎就在已经讲过的有关杀神王或祭司的风俗的解释之中。由于神的生命暂时寄居的脆弱媒介物的软弱性,体现在物体或人体中的神灵生命易于被玷污、被腐化。它必然与体现它的人体的年龄增长一起变得日益衰弱,如果要挽救它,那就必须在人体表现衰退迹象之前离开他,至少也要在衰退迹象表现时立即离开,以便把它转给强壮的继承者。其做法就是杀死神的旧的化身,将神灵从他那里送给一个新的体现者。所以,杀神,也就是说,杀他的人体化身,不过是使他在更好的形体中苏醒或复活的必须步骤。这绝不是神灵的消灭,不过是神灵的更纯洁、更强壮的体现的开端。如果这种解释适合一般杀神王或祭司的风俗,那它就更加明显地适合每年春天杀树精和草木精灵的代表的风俗了。植物的生命在冬天衰竭,原始人自然把它说成是草木精灵的衰颓,他认为草木精灵变老了变弱了,所以必须更新且把它杀掉,并以更年轻新鲜的形式使之复活。因此,春天杀掉草木精灵的代表被认为是提高和加速植物生长的手段。因为杀树精总是或明或暗地与树精在更年轻力壮的形式中苏醒复活联系在一起。所以在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风俗中,野人被射杀后,医生又使他复活。在瓦姆林根的仪式中有一个铁胡须博士的人物,他也许曾经扮演同样的角色。在我们底下就要说到的另外一种春天仪式中,这个铁胡须博士的确装作能使死人复生。不过关于神的这种苏醒或复活,我们一会儿还要多谈一些。
这些北欧的人物和我们探讨的题目——森林之王或内米祭司——之间的相似点是相当突出的。我们在北方的这些假扮人物中见到有一些国王,他们的树皮、树叶、衣服,以及青枝搭的小屋和他们在杉树下面开庭审判的情形,都千真万确地说明他们跟意大利的相等人物一样,都是一些树林之王。和他一样,他们也会暴卒,但也和他一样,他们也可以凭他们身体的力量和敏捷暂时逃脱死亡:因为在几个这样的北方风俗中,国王的奔跑和被追逐是仪式的一个突出部分,至少在一个例子里,国王如能逃脱他的追赶者,他就可再保持一年生命和职位。在这个例子里,事实上国王任职的条件是每年逃命一次,正如在较晚的时候卡利卡特王任职的条件是每十二年有一次对抗一切来犯者,以保护自己的生命,也正如内米祭司的任职条件是任何时候都要对付任何人的攻击以保住自己。在这各个例子中,神人的生命都延长了,条件是他要在战斗或逃跑的一场严重的体力竞争中表明他的体力并未衰退,因而迟早会到来的暴卒也延期了。关于奔跑,值得注意的是,在林中之王的传说和实际中都是很突出的一点。为纪念这一崇拜的传统创始人奥列斯特的奔跑,他必须是一个逃走的奴隶,因此这些林中之王都被古代作家描写为“强壮的手,飞快的腿”。如果我们充分地了解阿里奇亚树林的仪式,也许我们可以发现,森林之王像他波希米亚的兄弟一样,是可以有一次逃命的机会的。我已经推测过罗马祭司王(regifugium)每年奔跑一事最初也是同样性质的奔跑。换一句话说,他原本也是神王之一,他要么就凭任期满后被处死,要么就是强壮的手和飞快的腿证明他的神性健壮无损。在意大利森林之王和他北欧的同类人物之间,还有一个类似点值得注意。在萨克森和图林根代表树精的人被杀后又被医生救活。这正好是传说中肯定的内米首任森林之王希波吕托斯或维尔比厄斯所遇到的,他在被他的马踏死后,又被医生阿斯科拉庇厄斯救活。这样的一个传说同关于杀死森林之王不过是使他在继承者身上苏醒或复活的一个步骤的理论是十分相符的。
第二节 埋葬狂欢节
到此为止,我已经提出了一个解释,借以说明内米祭司需要由他的继承者杀死的规定。只能说这个解释是可能的,我们关于这个风俗及其历史知道得很少,对于这个解释也只能说到这个地步。不过,它表现的动机和思想方式在原始社会的作用能证实到什么程度,它的可能性就增大到什么程度。到此为止,我们关心其死亡和复活的神,主要是树神。如果杀神的习俗以及对他复活的信念开始于——或至少存在于——社会的狩猎和畜牧的阶段,那时被杀的神是一只动物,它要继续到农业阶段,那时被杀的神就会是谷物或代表谷物的人,如果我能证明这些,整个解释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后面我还要试图证明这一点,在讨论过程中,我希望能够澄清某些模糊的地方,并答复读者可能想到的某些异议。
我们从我们中断的地方开始——前面说到农民欧洲的春季习俗。除了已经描述的仪式外,还有两类相近的做法,神灵人物或超凡人物的装死在这两类做法中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一类做法中,戏剧性表演的死去人物是狂欢节的一个人身;另一类中则是死神本身。前一仪式自然落在狂欢节结束的时候,或是在这个欢乐季节的最后一天,即圣忏悔节的星期二,或是在四旬斋的头一天,即圣灰星期三。[5]另一节日——抓出死神或赶走死神,一般是这么称呼的——日子并不是定得这么一致。一般说是在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日,因为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做死者礼拜日。但在某些地方,节日要早一个星期,另一些地方,如在波希米亚的捷克人中则晚一个星期。而在莫雷维亚的某些德国人的村子里,则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举行。也许像已经提示过的,日期原来就不一致,要看第一个燕子或某些其他春的信息第一次出现的时日而定。有些作者认为这个节日源出于斯拉夫。格林认为它是古代斯拉夫人的新年节,斯拉夫人一年开头是在3月。我们先举一些狂欢节假死的例子,狂欢节在日历上总在新年之前。
拉丁姆的弗罗齐诺内在罗马和那不勒斯之间大约正中处,这个意大利的外省城市生活之枯燥单调,在狂欢节最后一天被叫做雷迪卡的古老盛会所打破。大约下午四点左右,城市的乐队奏着活泼的调子,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向皮亚察·德尔·普勒比西托进发。本地区行政副长官的住址和其余的政府建筑都在这里。在这里广场的正中心,等待的人群见到一辆大军,缀着各色的彩饰,由四匹马拉着。车上放着一张大椅子,坐在椅上的是狂欢节的庄严人物,一个泥灰做的人,约九英尺高,脸色发红微笑,一双大靴子,一顶意大利水兵士官戴的锡盔,一件饰有奇怪花样的彩色上衣,这些都装点着这位庄严人物的外表。他的左手落在椅背上,右手则文雅地招呼人群,这个谦恭的动作是由一个人用绳子牵动的,他谦虚地躲在欢乐椅底下,不露面。这时人群在椅子周围激动地汹涌着,尽情地发出粗犷的欢呼声,而一群温和单纯的人混杂在一起热烈地跳着萨尔塔里罗舞(Saltarello)。这个节日的一大特点,就是每人必须手里拿一枝所谓的雷迪卡(radica,根),代表一片大沉香叶子,更准确些说,是一片龙舌兰的叶子。任何人不带这种叶子闯入人群,都会毫不客气地被挤出来,除非他拿一根长竿,长竿尖上挑一棵大洋白菜作为代替物,或用一把编得古里古怪的草代替。人群转了一会儿之后,伴随着慢慢走动的大车来到副长官府的门前停下,大车走过不平的地面,颠簸地进入庭院。这时人群安静下来,他们压低的声音,据听见过的人描写,像波动的海水的低吟。所有的眼睛都焦急地看着大门。指望副长官本人和其他代表庄严法律的人们会从门里出来礼拜当时的英雄。停了片刻之后,一阵雷鸣的欢呼声和鼓掌声,欢迎贵官的出现,他们列队而出,下了楼梯,站到行列中。这时,狂欢节的歌声雷动,然后在震耳欲聋的吼声中,沉香叶子和白菜旋入高空,毫无偏颇地落在正义和不正义的人的头上,他们开始自由格斗,使节日添增新的乐趣。当所有参加者满意地结束了这些序幕活动之后,队伍开始游行。由一辆车殿后,戴着酒桶和警察,警察愉快地工作着,把酒分给所有要酒的人,这时车后滔滔的人群中进行着凶猛的争夺,杂以大量的喊叫声、拳击声、辱骂声,他们深怕失掉了花公家的钱把自己灌醉的大好机会。最后,队伍壮丽地游过了主要的街道,狂欢节的偶像被拿到一个广场的中央,剥掉他华丽的外装,放在一堆木头上,在人群的叫喊中烧起来,他们又一次雷鸣般地唱着狂欢节的歌,把他们所谓的“根”抛到火堆上,无拘束地尽情欢跳。
在阿布鲁齐(Abruzzi)的狂欢节,纸板人像由四个掘墓人抬着,他们嘴上叼着管子,肩带上挂着酒瓶。在前面走着狂欢节的妻子,穿着丧服,流着眼泪。[6]队伍偶尔停下来,妻子对同情的观众讲话,掘墓人就在酒瓶子上吸一口酒,提提神。在宽阔的广场上,把假尸放在柴木堆上,随着鼓声,妇女的尖叫声,以及男子更粗犷的喊声,一把火点着了火堆。一面烧像,一面向人群中抛撒栗子。有时候,狂欢节老人用竿顶上拴的一个稻草来表示,由一队化装游行的人们在下午背着走过城市。黄昏时分,四个化装的人拿着一床被子或被单,各执一角,让狂欢节的像跌进被子或被单里。然后继续游行,表演着猫哭耗子似地流着泪,用小锅或饭铃来强调他们悲戚的痛苦。还有些时候,阿布鲁齐,由躺在棺材里的活人表示死去的狂欢节,由另一人伴随,他扮演牧师,从水桶里大量地洒圣水。
在加泰罗尼亚的莱里达[7]地方,一个英国旅行者在1877年亲眼看见过狂欢节的葬仪。在狂欢节的最后一个星期,大队的步兵、骑兵、各种戴面具的人,有的骑马,有的乘车,威武地伴送波·皮大人(偶像称为波·皮)穿过大街,一连三天,欢乐都在高潮,然后在狂欢节最后一天的半夜,同样的游行队伍又穿过街道,不过面目不同,目的不同。辉煌的大车换成了柩车,里面放着波·皮大人的尸体,一队戴假面具的人,他们在第一次游行时扮演蠢学生的角色,大说笑话,现在却穿着牧师和主教的袍子,慢慢走过,手举一只点亮的蜡烛,唱着挽歌。所有的人都披着黑纱,骑马的人都带着点燃的火炬。游行的队列哀愁地走过大街,街两边是高高的、多层的、带有阳台的房子,每一个窗子,每一个阳台、每一个屋顶都挤满了化装穿戴得稀奇古怪的观众。移动的火炬上发出闪烁的光影,映照着整个场景,红色的、蓝色的焰火不时地腾上天空,旋即又熄灭。在马蹄声和游行人群均匀的脚步声中响起了牧师高唱的安魂曲,庄严的隆隆鼓声夹杂着军乐声。队伍在主要的广场上停下来,在死去的波·皮旁边念一遍模拟似葬仪的演说,然后灭掉火炬。魔鬼和他的侍从从人群中立即冲出来,抓住尸体转身就跑,全体人群紧紧追赶,喊着,叫着,笑着。魔鬼们自然被赶上,被冲散,从他们手里夺过来的假尸首放入原来预备接纳他的坟墓里。1877年莱里达的狂欢节就这样死去了,被埋葬了。
普罗旺斯地方[8]在圣灰星期三那天也时兴与此同类的仪式。一个叫做卡拉曼特兰的偶像,打扮得稀奇古怪,用车拉着或担架抬着,由一大群衣着奇特的人陪伴着,他们带着盛满酒的葫芦,把酒喝掉,露出各种真的或假装沉醉的样子。队伍的前面是几个扮作法官和律师的人,一个又高又瘦的人物扮作四旬斋,他们后面跟着年轻人,骑在瘦弱可怜的马上,穿着居丧者的衣服,假装悲悼,等待着卡拉曼特兰的命运。在主要的广场上队伍停下来,组成法庭,把卡拉曼特兰放在被告席上。在一场形式的审判后,于人群的呻吟声中把他处死,为他辩护的律师最后一次拥抱他的被保护人。执行官执行任务,被处死刑者背靠墙坐者,用石头将他砸死。把他破烂的残躯扔到海里或河里。几乎在整个的阿登[9]地区,从过去一直到现在都有这样的风俗:在圣灰星期三那天烧一具代表狂欢节的偶像,同时围绕着燃烧的偶像唱着有关的歌。常常试图把偶像画成村里最不忠于妻子的丈夫的模样。也许事先就可以看出,在这种难堪的情景中被选为画像的称号里有着引起家庭不和的倾向,特别是一面在画像所代表的逗人乐的受骗者屋前烧掉像,一面有猫叫声、呻吟声以及其他嘹亮的大合唱,公开表明他朋友和他邻居对他私人道德所持的看法。在阿登的某些村子里,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人披着干草和稻草,扮演忏悔节的星期二(Mardi Gras)。人们事后都称他为狂欢节的偶像。他被带到假法庭面前,被判处死后,像一个士兵接受军事判处一样,让他背靠着墙,用空弹筒对他射击。在里涅瓦·布瓦,这些无辜的丑角中有一个叫锡利的,一不小心被放枪队的一支步枪里留下的子弹给打死了。当这个可怜的“忏悔节星期二”在开枪后倒下去的时候,掌声又响起且持续,他做得那么自然,但是当他不再起来的时候,他们跑上去发现他已经死了。自此以后在阿登地区再也没有这种假行刑的事了。
在诺曼底,当圣灰星期三的黄昏有一个习俗,举行所谓忏悔星期二的葬仪。一个肮脏的偶像,穿得破破烂烂,一顶破旧的帽子盖在它的脏头上,它的大圆肚子里填满稻草,代表一个名声不好且年老放荡的人,在长期放荡之后,现在要为它的罪恶受苦了。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背着这个民间狂欢节的偶像,还装作在重压下蹒跚的样子,最后一次狼狈地在街上走过。这个人物的前面是鼓手,伴着一群嘲笑着的人群,其中,城里的顽童和所有临时聚合的众人大举出动,这个人物的铲子和钳子、瓶和锅、号角和铁壶,杂以吼声、哼声和嘘声的一片嘈杂声中,随着火炬的闪光被带着各处游行。队伍时时停下来,道德的保护者控诉这个老朽的罪人所做的一切冒失行为,因此它现在要被活活烧死。罪犯没有什么可辩护的,于是它被扔到一堆稻草上,用火把点燃,火焰直冲天际,在周围跳跃的孩子们高兴极了,高唱有关狂欢节死亡的某些古老的民间歌曲。有时候,焚燃之前把偶像从山坡上滚下去。在圣洛地方,忏悔节的星期二的破烂偶像后面跟着他的寡妻,是一个高大壮实的粗汉,穿着妇女服装,面蒙黑纱。他用响亮的嗓子发出悲叹哀号的声音。偶像由一群戴面具的人抬在担架上游行之后,就被扔进维尔河里去。奥克塔福,富丽特夫人大约六十年前她幼时曾亲眼看见那最后的一幕,她作了如实的描写:“我父母邀请朋友从珍妮·库拉德的塔顶上观看葬仪队伍走过。就在这里,我们喝着柠檬水——因为斋期,这是唯一允许喝的饮料——看到一个场面,我毕生都会印象鲜明地记得它的。我们脚下的维尔河从它的老石桥下流过。在桥的当中,树枝编的担架上放着忏悔星期二的人像,周围是几十个戴假面具的人,跳着舞,唱着歌,带着火炬。有几个穿着五彩斑斓衣裳的人沿着栏杆跑,好像鬼一样。其他的人玩累了坐在柱子上打瞌睡。不久舞蹈停止了,队伍中有几个人抓起火把,点燃偶像,然后把它扔进河里,加倍地高叫欢呼。浸了树脂的稻草人继续燃烧着,顺着维尔河的溪水流走,用它的葬火照亮了上的树林和古堡的墙垛,路易十一世和弗朗西斯一世都在这古堡里睡过。当燃烧着的人形最后的火光像流星一样在河谷的尽头熄灭的时候,人群和假面人都退去了,我们才和我们的客人离开城堡。”
在图宾根附近,在忏悔节星期二的时候,做一个草人,叫忏悔节之熊,他穿一条旧裤子,嗓子里塞一个新鲜的黑布丁或两根装满血的喷水器。正式宣判死刑之后,便将他斩首,放在棺材里,于圣灰星期三葬在教堂墓地里。这叫做“埋葬狂欢节”。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中有将“狂欢节”吊死的习俗。如在布拉勒,当圣灰星期三或忏悔节星期二的时候,两匹白马和两匹栗色马拉着一架雪橇,上面放着一个缠白布的稻草人。它旁边有一个车轮,保持不断地转动,两个年轻小伙子装作老人,跟在雪橇后面悲哭。村里其余的小伙子骑上缀以绸带的马,陪着队伍走,队伍前头是两个女孩,戴一顶长青藤花冠,由车或雪橇拉着。在一棵树下举行审判,审判中由扮作士兵的小伙子宣布死刑。两个老人想救出草人,带着逃走,但未成功。两个女孩将草人抢去,交给刽子手,他把它吊在树上。两个老人想爬上树,将它取下来,总不成功,他们老是跌下来,最后他们在绝望中倒在地上,为吊死的人又哭又号。于是一位文官发表一篇演说,他宣布狂欢节已被判处死刑,因为他坑害了他们,使他们鞋跑破了,使他们又累又困。在莱希芮茵,“埋葬狂欢节”时,一个男子扮为妇女,身穿黑衣,由四个人抬在滑竿上或尸架上,有一些穿黑衣的男扮女装的人悲哭地,然后把它扔到村子的粪堆前,淋湿粪堆,把他埋在里面,用稻草盖上。在忏悔节星期二的晚上,爱沙尼亚人做一个草人,叫墨奇克,即“树精”。给它穿男子上衣,戴着礼帽,到来年就给它围头巾,穿女式上衣。这个人物被拴在一根长杆上,在欢呼声中带出村外,绑在树林里一株树顶上。这个仪式被认为是抵御各种不幸的保护手段。
有时候,在这些忏悔节或四旬斋的仪式上还表演假死者的复活。如在施瓦本的某些地方,在忏悔节的星期二,铁胡须博士假装给一个病人放血,他因此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不过医生后来用管子空气吹到他身上,使他复活过来。在哈尔茨山区,狂欢节过后,就把一个人放在和面的木糟里,唱着挽歌抬到坟墓上,但在坟里不埋人,只埋一瓶白兰地酒。演说之后,人们回到村里草地或聚会的地方,在这里抽着先前葬仪上所分发的泥质长烟斗,到第二年忏悔节星期二的早上把白兰地挖出来,节日开始时,每人尝尝酒,如俗话所说的,酒(精)又复活了。
第三节 送死神
“送死神”的仪式有许多和“埋葬忏悔节”同样的特点,只是送死神一般还要跟着一个带回夏天、春天或生命的仪式。如巴伐利亚的中弗兰肯省在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天,村里的孩子们常做一个死神的草人,他们带着死神做出隆重壮观的样子游街,然后尽量高声叫喊,在叫喊声中把它烧掉。一个16世纪的作家这样描写弗兰肯的风俗的:“四旬斋的中期是教堂让我们欢乐的季节,我祖国的年轻人做一个死神的草人,把它捆在一根杆子上,又喊又叫地把它拿到邻村去。有些人客气地接待他们,吃了这个季节通常的食品牛奶、豌豆和干梨之后,又送他们回去。不过,另外一些人对他们一点也不客气,认为他们是不幸的先导,也就是死亡的先导,他们用武器和辱骂把他们从村里赶出去。”在厄兰根附近的村子里,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天来到的时候,女孩子们都穿上她们最好的衣服,头上戴着花。穿戴好了就到附近的镇上去,带着用树叶装饰的木偶,上面覆盖着一块白布。她们把这些木偶,成双地带着挨家走,在他们指望得到东西的每家门口停下来,还唱几行诗,诗里说这是四旬斋的中期,她们要把死亡扔进水里去。他们得了一些微小的赏赐之后,就到雷格尼兹河边去,把代表死亡的木偶扔进河里。这样做为的是要保证丰收的年景。此外,大家还认为这一仪式能够防止瘟疫和暴死。在纽伦堡,七岁到十八岁的女孩子抬一个敞开的小棺材在街上走过,棺材里放着一个玩偶,藏在一件尸衣下面。另外一些人在一个打开的盒子里拿一根山毛榉的树枝,枝上拴一个苹果当作头。他们唱道:“这倒不错,我们把死神送进水里。”或是唱:“我们把死神送进水里,送他进去又取他出来。”在巴伐利亚直到1780年,有些地方还相信如果不遵守“送死神”的习俗就会发生致命的瘟疫。
在图林根的某些村子里,在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天,孩子们常拿一个用桦树枝做的木偶游村,然后把它扔进一个池子里,同时还唱:“我们从牧人的老房子后面送走老死神,我们得到了夏天,克罗顿的力量被摧毁了”。在格拉[10]附近的德布希维兹或多布希维兹,“赶走死神”的仪式现在或过去每年3月1日举行。年轻人用草一类的东西做一个人像,为它穿上旧衣服(从村里住的人家里讨来的),然后把它拿出去扔到河里。回到村里后,他们把这好消息告诉人们,得到鸭蛋或其他食物作为报酬。现在或是过去都认为这个仪式是为了洁净村子,保证居民不生病不罹患瘟疫。图林根另外有些村子,其居民原来是斯拉夫人,在这些村子里,一面送木偶,一面唱歌,歌词开头是:“现在我们送死神出村,迎接春天进村。”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时候,图林根遵循这个风俗如下:男孩子和女孩子用稻草一类的东西做一个偶像,偶像的样子年年不同。头一年是一个老汉,第二年是一个老妇,第三年是一个青年男子,第四年是一个老妇,人像的衣服也随着扮演它的人而不同。在什么地方做偶像,常有尖锐的争论。因为人们认为从屋里带出偶像的那一家当年不会有死人的事。偶像做好以后就拴在一根杆子上,如偶像为一老汉,则由一女孩背着,如为一老妇则由男孩子背着游行街道,青年人手里拿着一根棍子,嘴里唱道:他们正赶走死神!他们来到水边的时候,就把偶像扔进水里又赶快跑回,恐怕它会跳到他们肩上,拧他们的脖子。他们还留心不要碰着它,深恐它会使他们说不出话来。他们回来后,用他们的棍子鞭打牲口,认为这会使牲畜肥壮或繁殖。然后,他们又去拜访从屋里拿出死神像的那一家或那几家人,在人家里得到施舍的半熟的豌豆。在萨克森也流行“送死神”的习俗。在莱普西克,每年四旬斋中期,私生子和妓女都做死神的草人。他们带着它唱歌游行,把它拿给年轻结婚的妇女看,最后他们把它扔进帕思河里,他们声称这个仪式使年轻妻子多产,使城市清洁,当年能保护居民免遭瘟疫或其他灾难。在西里西亚,四旬斋中期也遵循同样的仪式。许多地方,大姑娘让小伙子们帮忙,给一个草人穿上妇女衣裳,在日落的时候带出村去。在村边上,他们剥去草人的衣裳,把它撕碎,把碎块撒在田里。这叫做“埋葬死神”。她们把偶像拿出去的时候,唱道,他们要在一棵橡树下埋葬死神,让它离开人们。有时候歌词说,他们翻山过谷背死神,让它再也不转回。在波兰边境的格罗斯—斯特里兹地方,这种偶像叫做戈伊克。人们把它驮在马背上,扔到最近水里。人们认为这个仪式能保佑他们来年百病息除。在伍洛和古罗地区,死神常被扔到邻村境内。但是邻村的人们也不敢接受这个不吉利的人像,他们警惕地看着不让它被扔来,因此,两边的人常常为此挥动老拳。在上西里亚的某些波兰地区,偶像是个老妇,叫做马扎娜,死亡女神。它是在最近死过人的屋里做,用杆子抬到村边,扔进池子里或烧掉。在波尔奎兹,“送走死神”的风俗原已消失,但是这个风俗停止后,爆发过一场致命的疾病,引得人们又把它恢复了。
在波希米亚,孩子拿着代表死神的草到村子人的尽头去把它烧掉,唱道:
我们现在把死神送出村庄
把新的夏天带进村庄
欢迎,亲爱的夏天,
绿色的小谷粒。
在波希米亚的塔博尔,人们把神像带出城,从高崖扔进水里,他们唱道:
死神在水上游,
夏天马上要来到,
我们为你送走死神,
我们带来夏天,
哦,神圣的马克塔,
让我们的小麦和黑麦
有一个好年成。
在波希米亚另外一些地方,他们把死神带到村头,唱道:
我们送死神出村,
让新年进村,
亲爱的春天,我们向你表示欢迎,
青青的草,我们向你表示欢迎。
他们在村后架起火葬堆,在堆上烧掉草人,同时辱骂它、嘲笑它。然后他们回去了,唱道:
我们送走了死神,
带回了生命,
他已经在村里住下来,
为此,让我们欢乐地歌唱。
在摩拉维亚的一些村子里,如在杰斯尼茨和塞坦多夫,年轻人在四旬斋的第三个星期天集合起来,做一个草人,戴一顶皮帽,穿一双旧皮袜子,如果能弄到这些东西的话。于是把偶像悬在一根竹竿上,由小孩子们带到开阔的田野里去。在路上,他们唱着歌,歌词说:“他们正送走死神,把亲爱的夏天带进屋里,和夏天一起带进五月和花卉。”到了预定的地方,他们围着偶像站成一圈跳舞,大叫大喊,然后突然向偶像冲去,用手把它撕碎。最后把碎片堆成一堆,把杆子也折断,全都用火点燃。它一面烧,队伍一面围着它高兴地跳,为春天赢得的胜利而高兴,当火快灭的时候,他们到各家去讨鸭蛋礼物,用以举行宴会,注意把请赏的理由说成是他们把死亡送走了。
前面的例证说明,人们常常害怕死神像,带着憎恨厌恶的心情对待它。如村中居民急于把偶像从自己这里转到邻村去,邻村的人又不愿接待这位不祥的客人,都足以证明它引起的恐惧。还有在卢萨西亚和西里西亚,有时是让偶像从人家窗子里伸进去看一眼,认为这家就会有人在一年内死去,除非他付款赎命,并且,扔掉偶像后,有时扛像的人飞跑回家,唯恐死亡会跟着他,如果他们有人在跑时摔倒,那就认为他在一年内会死去。在波希米亚的克鲁迪姆,死神像是用十字架做的,顶上插一个头并戴上面具,身上披一件衬衣。在四旬斋的第五个星期天,男孩子们把这个偶像拿到最近的河边或池边,然后站成一排后将它投入水中。然后都跳进去追赶它,一赶上它就不准再有人下水。未下水或最后进水的男孩子一年内会死去,他还得把那死神偶像拿回村里,然后把它烧掉。另一方面,人们认为带出死神的那一家一年内不会死人,有时认为赶走了死神的村子受到保佑,不得疾病或瘟疫。在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有些村子在死亡星期日的星期六用旧布、干草、稻草做一个偶像,目的是把死亡赶出村去。在星期天,人们带着棍棒和皮条,在存放偶像的房子前面集合。于是四个男孩在欢呼声中用绳子把偶像从村里拉过,其余的人就用棍棒和皮条抽打它。到了属于邻村的一块地里,他们放下偶像,毒打它一顿,把碎片散在田里。人们认为送走了死神的村子全年平安,没有任何传染病。
第四节 迎夏
在前面那些仪式里,继赶走死神之后,接着迎春天、夏天或生命回来,这仅是暗示,最多也只是宣布一下。在下面的例子却有明明白白的表演。如在波希米亚的某些地方,死神像在日落时扔到水里淹死:然后女孩子们到树林里去砍下一棵树顶带青的幼树,把一个妇女打扮的偶像挂在上面,再全部用绿色、红色、白色绸带点缀起来,然后拿着这个“列托”(夏天)到村里游行,收集礼物,并且唱道:
死亡在水里游,
春天来拜访我们,
带着红红的鸭蛋,
还有黄黄的烤饼。
我们送死神出村,
我们接夏天进村。
在许多西里西亚的村子里,对死神像恭敬一番之后,剥去它的衣服,骂着把它扔进水里,或在田里把它撕成碎片。然后青年人到树林里去,砍下一棵小杉树,剥去树干的皮,把它装上常青植物、纸做的蔷薇、染色蛋壳、各色碎布等花彩。这棵树装饰完毕,就叫做夏天或5月。男孩带着它挨家挨户走,唱着应景的歌,向人家请赏。他们的歌里有下面这么一段:(www.daowen.com)
我们送走了死神,
我们带回亲爱的夏天——
夏天和五月
所有的花儿鲜艳。
有时候他们还从树林里带回打扮得很漂亮的人像,名叫夏天、5月或新娘,而在波兰地区称作齐万娜,即春天的女神。
在爱森纳赫[11],在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日,青年人常捆一个代表死亡的草人在车轮上,他们把它滚到小山顶上。然后点燃草人,让它和轮子一起滚下山坡。第二天,他们砍倒一棵高大的杉树,用绸布条装饰起来,立在平地上。然后,人们爬上树去取下绸布条。在上卢萨希亚,用稻草和破布做的死神像,戴上新婚新娘供给的面纱,穿上最近死过人的人家供应的上衣。穿戴完毕就把人像栓在长杆的一端,由最高最壮的女孩扛着快走,其余的人用棍子和石头击打偶像。谁要打中了,肯定那一年不会死。这样,死亡被带出村子,扔到水里或扔到邻村界内。在回家的路上,每人折一根青枝,高高兴兴地拿着,等到村边时就将它扔掉。有时候,那邻村的青年人追赶过来,把偶像又扔回来,不愿意让死神留在他们那边。因此两边的人有时还对打起来。
在这些情况里,死神由偶像代表被扔掉,夏天或生命由树枝或树代表,被带回来。但是有时候,人们似乎又赋予死神偶像新的生命力代表,通过某一种复活的形式,它又成了普遍苏醒的工具。如在卢萨希亚的某些地方,只有妇女管送死神的事,不容男人插手。她们整天穿着衣服,做一个草人,给它穿上白衬衣,让它一手拿扫帚,一手拿镰刀。她们一面唱着歌,让顽童跟在后面扔石头,一面把偶像带到村边,在那里把它撕碎。然后她们砍下一棵好看的树,把衬衣挂在树上,唱着歌把它带回家来。特兰西瓦尼亚地方有个名叫布拉勒的村庄,离赫尔曼斯塔不远,村里的撒克逊人在升天节的时候,用下面的方式举行“送死神”的仪式:早祷完毕,所有的女学生都到她们一个同学的家里去,在那里为死神装扮。做法是拿一把脱过稻粒的稻草,大致扎成人头人身的样子,两只手是用扫帚柄水平地穿过身子做成的。人像穿着年轻农妇的节日衣服,戴上红头巾,银胸针,手臂和胸上悬挂着大量的绸布条。女孩子们加紧速度地完成它,因为晚祷的钟马上要响了,死神必须及时做好,摆在打开的窗户上,让所有前往教堂的人在路上能看见。晚祷完毕,长久盼望的时刻来到了,开始第一次带死神游行。这是女学生独有的权利。两个较大的女孩拿着偶像的两臂走在最前面,其余的人排成两行相随。男孩儿们不许参加游行,但他们排在队伍的后面,羡慕地唱着“美丽的死神”。于是队伍走过村里所有的街道,女孩子们唱一起首古老的歌曲,开头是:
Gott mei Vater, deine Liebe
Reieht so weit der Himmel ist, [12]
调子与这首歌的普通唱法不一样。当游行的队伍穿过了每一条街之后,女孩子们又到另外一个同学家去,她们对着在后面一群焦急多事的男孩子把门关上,立即把死神剥光,把光光的草杆从窗户扔给男孩子们,他们赶忙拿着它,不唱歌,跑出村去,把破烂的偶像扔进附近的河里。完事之后,这场小戏的第二幕就开始了。男孩子把死神送出村的时候,女孩们留在屋里,其中一个现在已穿好偶像穿过的一切漂亮服饰。这样穿戴之后,她由队伍领着穿过所有的街道,唱着原先唱的那首歌。游行完毕后,她们都回到扮演主角的女孩家中去。在这里有一场宴会等着她们,男孩子又不得参加。民间相信孩子们可以安全地先吃醋栗和其他水果。这一天死神已经被送走,因为死神过去专门藏在醋栗里,现在则被消灭了。现在他们还可以大胆地到户外洗澡。直到近年来,摩拉维亚的一些德国村子举行的仪式还与这相近。男孩子和女孩子在复活节后第一个星期日的下午聚会,一齐做一个草人代表死神。给偶像穿上色彩鲜艳的绸条和衣服,捆在一根长杆的顶上,然后又唱又喊地把偶像背到最近的一块高地上去,在这里剥掉偶像漂亮的衣服,把它扔下坡去,或让它滚下坡去。然后有一个女孩再穿上从死神像身上取下来的漂亮衣服,由她领头,列队走回村庄。有些村子的做法是把偶像埋在全乡声名最坏的地方。有一些村是把它扔进流水里。
在上述卢萨西亚的仪式里,毁掉死神像以后带回家的树显然等于以前所说的习俗中在死神被扔掉或毁掉之后作为夏天或生命的代表而带回的那些树或树枝。但是把死神穿的衬衣披到树上,显然是表明树是毁去的偶像在新形式中的一种重生。在特兰西维尼亚和摩拉维亚的习俗中也表现了这一点:女孩穿上死神穿过的衣服,被领着游村且唱送走死神所唱的歌,其用意都在于她是刚被毁去的神灵的复活。所以,这些仪式中虽然都表现了死神的毁灭,但这些例子证明,不能把死神看作如我们理解死神那样仅只是纯粹破坏的因素。如果带回的树是春天苏醒的草木的标志,却穿上刚被毁掉的死神穿过的衬衣,其目的绝不可能是阻滞或反对植物的苏醒,而只可能是培植它,促进它。所以,刚被毁掉的神灵——所谓死神——一定具有某种苏醒复活、促进生长的影响,它能把这种影响传给植物界,甚至动物界。某些地方遵守一种风俗,拿几块死神草像的碎片,把它们放在田里能促使在庄稼生长,或放在牲口槽里使牲口繁殖。那么说死神像具有促进生命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在奥地利的西里西亚有一个村子名叫斯巴琴多夫,人们高唱着歌,把稻草、小树和破布做的死神像带到村外,一个开阔的地方,在那里把它烧掉。正烧的时候,大家都争着抢碎片,用空手从火焰里把碎片取出来。每一个得到偶像碎片的人都把它栓在自己园子里最大一棵树的树枝上,或是把它埋在自己的地里,相信这会促使庄稼长得好一些。奥地利西里西亚的特罗波地区,男孩在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日做一个草人,由女孩子为它穿上妇女的服装,挂上绸条、项链、花环。把它拴在一根长杆上,然后带出村去,后面跟一队男女青年,又闹、又哭、又唱歌。到达目的地——村外的一块田地——之后,就去掉偶像的衣服和装饰品,然后人们涌向前,把它撕成小块,大家争夺碎片。人人都想得到一把做偶像的草,因为人们相信这样一把草放在牲口槽里可以使牲口繁殖,或者是把草放在鸡窝里,认为这能防止母鸡把蛋带走,并使它们孵更多的蛋。如果背死神像的人扔掉死神后用背死神的棍子打牲口,也能使牲口肥胖或多产,这种信念也是认为死神像有增殖的能力。也许棍子原先是打过死神的,因而得到死神所具有的繁殖力。我们还讲到过,在莱普西克,把死神的草像给年轻的妻子们看,可使她们多生育。
似乎很难把五朔树和毀掉死神后带进村里的树或树枝区分开来,扛它们的人说是带回夏天,所以这些树显然是代表夏天的。在西里西亚,它们通常确是被称为夏天和五月。有时在“夏天”树上系一个娃娃,它不过是再一次代表夏天,正如“五月”有时候同时由一棵五朔树或五朔娘娘来表示。还有,“夏天树”跟“五朔树”一样是用绸条等等装扮的。跟五朔树一样,如果很大,就把它们栽在地上,让人爬上去;如果小,就由男孩女孩拿着挨家走,唱着歌收钱。好像是为了证明两套风俗原是一套似的,背夏天树的人有时宣布他们迎来了夏天和五月。所以,“迎五月”的风俗和“迎夏天”的风俗,基本上是一样的。“夏天树”不过是“五朔树”的另一种形式,唯一的区别(除了名称而外)是它们各自被迎来的时间不同,五朔树通常是5月1日迎进来,夏天树则是在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日迎回来。所以,五朔树如果是体现树精或草木精的,夏天树也必然是体现树精或草木精的。但是,我们已经谈到过,夏天树在某些例子里是体现死神的复活。那么,在这些例子里,称为死神的偶像也必然体现树精或草木精。这种推论可以得到证实:第一,人们认为死神偶像的碎片对植物和动物的生长都具有使之成活和增殖的影响。我们在本书前面已谈到过,人们认为这种影响是树精特有的属性。第二,死神偶像上有时点缀着树叶,或是用大小树枝、大麻,或脱粒后的稻草扎成的,有时是悬在一棵小树上,由女孩子拿着收钱,正如五朔树或五朔娘娘的做法一样,也正如夏至树和悬在树上的娃娃一样。总之,我们只得认为,至少在某些例子里,驱走死神和迎进夏天不过是死亡和草木精在春天复生的另一形式,我们在野人被杀又复活的扮演中已经见到了。狂欢节的埋葬和复活也许是表达同样想法的另一方式。如果认为狂欢节和死神偶像一样具有促进生命和增殖的影响,把狂欢节的扮演者和埋葬在粪堆下面,那是很自然的。的确,爱沙尼亚人在忏悔节星期二那天照一般做法把草人带出村庄,他们不叫它狂欢节,而称它为树精(木奇客),他们把它拴在林中的一棵树顶上,用以明显表示偶像和树精是同一个,在那里挂上一年,几乎每天都有人向它祈祷和献祭,求它保护牲畜:因为跟真正的树精一样,木奇客是保护牲口的。有时候木奇客是用玉米穗做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大致推论出,狂欢节、死神和夏天,都是我们探讨的许多风俗中某种神灵人格化较晚近的、不适当的表现形式。这些名字的抽象性本身就说明它们起源于现代。因为像狂欢节和夏天这种时间和季节的拟人化,或像死亡这种抽象观念的拟人化,都不是原始人所具有的。但这些仪式本身都带有远古时期的印记,所以,我们几乎不已不认为它们所体现的那些观念原本是属于更简单更具体的一类。这些仪式中所提到的任何一棵树或者是某种树,甚或某棵个别的树(因为在某些野蛮人的语言中,并没有一个代表“树”这个总称的字眼),所代表的观念即足以构成一个具体的基础。从这个具体的基础上出发,然后再加上逐渐概括性的、抽象性的类比过程,我们就可以得一到个更广泛的草木精灵的观念。但是这种关于草木的总概念很容易与草木在各季节中的表现混淆。所以用春天、夏天或五月代替树精或草木精灵就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事了。还有,将死亡的树或草木这个具体的概念在类似的概括过程中变成一般死亡的概念,因而在春天送走将死亡或已死草木作为它复活的第一步,这种做法经过一时段后便发展成从村里或地方上驱除死亡。在这些春天的仪式中,死亡是指冬天将死或已死的草木,这种观点得到曼哈德的大力论证。他以死亡这个应用于成熟的玉蜀黍的精灵这个名词,加以类比,从而肯定了这种观点,一般是把成熟的玉蜀黍的精灵看成衰老,不是看成死亡,所以通常称它为老人或老妇。但是在有些地方,一般认为玉蜀黍的精灵住在收割时最后的一把谷穗里,这把谷穗在这些地方称为“死家伙”。人们警告孩子们不要到田里去,因为死亡就住在玉蜀黍里。特兰西尔维尼亚的撒克逊人小孩子在收割玉米的季节玩一种游戏,由一个满身铺着玉米叶的孩子扮作死亡。
第五节 夏冬之战
有时候,农民中流行的风俗把植物在冬季潜伏的力量和在春天苏醒的活力两者间的对比,分别用扮演冬天和夏天的演员之间的戏剧性争斗来表现。如在瑞典的城镇里,每逢五朔节总有两队骑马的年轻人互相对峙,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两队中,一队由穿皮衣的冬天代表领道,他扔下雪球和冰块,以延长寒冷的天气;另一队由披新鲜树叶和花卉的夏天代表者指挥。在假斗中,夏天队战胜了,于是仪式以宴会结束。又如在莱茵河中部地带,穿长藤的夏天代表和穿谷草或水草的冬天代表战斗,最后战胜了冬天的代表。敌人被摔倒在地上,剥去他的草衣,撕成碎片撒开,同时两位斗士的年轻伙伴们一齐唱着歌,祝贺夏天战胜冬天。然后,他们带着夏天的花环或树枝,挨家收集鸡蛋咸肉等礼物。有时候,扮演夏天角色的斗士穿着树叶花卉,头上戴着花环。在帕拉丁特[13],这种模拟的格斗竞赛在四旬斋的第四个星期日举行。在巴伐利亚全境,与此同样地戏也在同一天表演,有些地方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中叶或更晚的时候。夏天出来,穿一身绿,点缀着飞飘的绸带,怀里是一根开花的树叶或小树,上面挂着苹果和梨。冬天则裹在皮帽和皮大衣里,手里拿一把雪铲和连枷。他们各有后卫跟着,穿相应的衣服,他们走遍全村的街道,在各家门口停下来,唱几段古老的歌,因此到得面包、鸡蛋、水果等礼物。最后格斗一阵之后,冬天为夏天所败,被浸到村中的井里,或随着喊声笑声从村里把他赶到树林去。
在下奥地利的戈弗里茨,忏悔星期二那天有两个扮演夏天和冬天的人挨家挨户地拜访人们,处处都有孩子们极高兴地欢迎他们。夏天的代表穿白衣服,拿一把镰刀。他的伙伴扮演冬天,头上戴一顶皮帽,胳臂和腿都包着稻草,手拿一柄连枷。在每家门前,他们轮流唱歌。在不伦瑞克[14]的德罗姆林,直到现在每年降灵节期间,都有一队男孩和一队女孩扮演夏冬之间的斗争。男孩挨家跑着、叫着、唱歌、摇铃,以赶走冬天。他们后面跟着低声唱歌的女孩子,由一个五月新娘领着,全身穿得漂漂亮亮,佩上花朵和花冠,代表温和的春天降临。在从前,冬这天一角色由一个草人来表示,由男孩子们拿着,现在则由一个化装的真人扮演。
在北美中部爱斯基摩人当中,在欧洲已蜕化为单纯戏剧表演的冬夏代表之间的斗争,却仍然是一种巫术形式,众所周知的目的是要影响天气。在秋天,当暴风雪宣告北极阴沉的冬天将要来到的时候,爱斯基摩人分成两组,分别称为松鸡和鸭子,松鸡组包括所有冬天出生的人,鸭子组包括所有夏天出生的人。然后拉开一根长长的海豹编的绳子,两组各执一端,尽力把对方拉到自己这边来。如果松鸡组失败,夏天组赢得胜利,那么整个冬天都可以指望有好天气。
第六节 春神的死亡与复苏
在俄罗斯,“埋葬狂欢节”和“送死神”之类的葬仪不是用死亡或狂欢节的名目举行的,而是用某些神话人物的名字,如科斯特鲁邦柯、柯斯特罗马、库帕洛、拉达和雅丽洛。这些俄罗斯仪式在春天和仲夏都举行。如“在小俄罗斯[15],在复活节期间常有一个风俗纪念春天之神柯斯特鲁邦柯的葬仪。歌手们站一圆圈,围着一个躺在地上像已死去的女孩慢慢走,他们一边走,一边唱:
死了,死了,我们的科斯特鲁邦柯!
死了,死了,我们的亲爱的!
等到女孩突然跳起来,于是歌队快乐的喊道:
苏醒了,苏醒了,我们的科斯特鲁邦柯!
苏醒了,苏醒了,我们的亲爱的!”
在圣约翰节的头一天(仲夏节的头一天),用稻草做一个叫库巴罗(Kupalo)的人物,“穿上妇女服装,戴着项链和花冠。然后砍一棵树,缀上绸带后,立在某个预先选好的地方。他们给树取个名字,叫玛莉娜(Marena)(冬天或死亡),草人放在这棵树附近,还放了一张桌子,桌上是酒和食物。然后点一堆火,青年男女成双地围火跳舞,并带着人像。第二天就把树和人像上的装饰品取下来,把两者都扔到河里去。”在6月29日圣彼得节的时候,或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俄罗斯举行“柯斯特罗马(Kostroma)的葬仪”或拉达(Lada)或雅丽洛(Yarilo)的葬仪。在潘查和西姆伯斯克两个行政管理地区,葬仪的方式如下。在6月28日点一堆火,第二天少女们选一人扮演柯斯特罗马。她们的同伴深怀敬意地向她行礼,把她放在木板上,抬到河边。在那里,她们让她下水洗澡,最大的一个女孩提一个菩提树皮的篮子,拿它当鼓敲。然后她们回到村里去,开始游行、游戏、跳舞,尽欢一天。在莫罗姆地区,柯斯特罗马由一个草人表示,穿妇女的衣服,戴着花。人们把它放在一个木槽里,唱着歌抬到湖边或河边。这时人群分为两派,一派攻打草人,一派保护草人。最后攻打这派的人得胜,剥去草人的衣服和装饰,把草人撕成碎片,把做草人的草踩在脚底下,然后把它扔到水里。同时,保护草人的人用手捂着脸,假装悲悼柯斯特罗马的死亡。在柯斯特罗马地区,于6月29日或30日举行雅丽洛的葬仪。人们选一个老人,给他一口小棺材,里面放一个普里阿普斯神[16]的小像代表雅丽洛。他把这口棺材带出镇外,后面跟着妇女唱挽歌,做出表示悲哀失望的姿态。在开阔的田地上挖一个坟,在号哭声里把人形放下去,然后开始游戏跳舞,“使人想起古代异族斯拉夫人的葬仪游戏”。在小俄罗斯,雅丽洛这个人像被放在棺材里,日落时带着游街,周围是酒醉的妇女,她们不断悲哭道:“他死了!他死了!”男人把人像拿出来摇晃,好像他们要把死人唤活。然后他们对妇女说:“女人们,别哭。我知道什么比蜜还甜。”但妇女们继续啼哭,像在葬仪上一样。“他到底犯了什么罪啊?他人真好哇。他再也不起来了。我们怎么跟你分得开呵?没有你还有什么日子呵?哪怕是一会儿工夫,你也起来一下呀!他到底是起不来了!他起不来了!”最后人们把雅丽洛葬入坟墓。
第七节 植物的死亡与复活
这些俄国习俗与奥地利和德国的所谓“送死神”的那些习俗属于同样的性质。所以,如果本书对后者所作的说明是对的,那么,俄罗斯的柯斯特鲁邦柯、雅丽洛等等原来也必定是草木精灵的体现,他们的死亡也必定是看作他们复活所必需的开端。死亡以后必然复活,这在我们所描写的仪式(第一个柯斯特鲁邦柯的死亡与复活)中是表演出来了的。这些俄罗斯的仪式中,有一些是在仲夏纪念草木精的死亡,其理由可能是夏天的衰退是从仲夏节开始,这个节日以后,白昼开始缩短,太阳开始了自己不愉快的行程:
黑乎乎的凹地里
那里躺着冬天的寒冷。
在一年的这样一个转折点里,人们可能认为植物也具有夏天的那种刚刚出现的,虽然还几乎无法察觉出来的衰退,原始人很可能选这样的转折点作为从事巫术仪式的适当时刻,希望用这种仪式阻止植物生命的衰退,至少也要保证植物生命的复活。
但是,植物死亡虽是表现在这些春天和仲夏的仪式中,有一些仪式还表现了它的复活,而某些仪式里的一些特点却很难只用这个假设来说明。这些仪式常常特有的庄严的葬仪、嚎哭和丧服,的确对造福于人的植物精的死亡很适合。但是,常常送走偶像时很高兴,拿棍子和石头攻打它,又对它辱骂、诅咒,这些我们又怎么说明呢?扛偶像的人一扔下它就赶快跑回家,这种匆忙中所表露的对偶像的恐惧,偶像看过的任何人家不久就有人要死去的这种信念,我们又怎样说明呢?这种恐惧也许可以用一种信念来解释,认为死去的植物精具有某种传染性,接近它是危险的。不过这种解释有些勉强,此外,也不能说明送走死亡时的笑闹。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些仪式中有两种彼此不同的、似乎对立的特点:一方面为死亡哀愁,对死者深爱和尊敬;另一方面,对死者害怕怀恨,高兴他的死亡。这两种特点中,前一个如何说明我已经试着表明过,后者与前者为什么结合得那么紧,则是我在后面要试图答复的问题。
第八节 印度的类似习俗
在印度卡纳格拉地区,少女在春天遵循一种习俗,与前面描写的某些欧洲的春天习俗极为近似。这种习俗叫做拉里·卡·米拉,即拉里的庙会,拉里是湿婆[17]或帕婆提[18]的一个小小的涂色的泥塑偶像。这个习俗在整个卡纳格拉地区都流行,对它的纪念完全限于年轻妇女,时间是“且特”(3月-4月)的绝大部分直到巴撒赫(4月)的桑克兰。在3月的某个早上,村里所有的少女提着装有达伯草和花的小篮子去到指定的地方,在那里她们把花扔成一堆。她们围着花堆站成一圈,唱着歌。一连十天,每天如此,直到花草堆到相当高的时候。然后,她们在林子里砍两棵树枝,每根树枝头上带三个尖,然后把它们尖朝下地放在花堆上,形成两个三脚架或两个锥形物。她们请会做偶像的人做两个泥偶像,放在两根树枝朝上的尖端上,一个代表湿婆,一个代表帕婆提。然后女孩子们分为两起,一起代表湿婆,一起代表帕婆提,按常人为这两个偶像举行婚礼,婚仪做得很周全。结婚后,她们举行宴会,宴会费用是她们请父母捐献的。然后在第二年的桑克兰(巴撒赫),她们都一起到河边去,把两具偶像扔在一深池子里,在那里哭起来,好像她们在举行葬仪。附近的男孩子常常逗她们,游泳追偶像,把它们拿上来,在女孩子哭偶像时,他们摇晃偶像。据说庙会的目的是为了得一个好丈夫。
在这个印度仪式中,湿婆和帕婆提这两尊神被看成草木精似乎由偶像之被放在花草堆上的两根树枝上得到证明。在这里,跟欧洲民间习俗中常见的一样,草木神有双重代表,植物和偶像。这两尊神在春天结婚是欧洲仪式相符的,欧洲春天草木精的结婚是由五月王和五月娘娘、五月新娘、五月新郎等等表示的。把偶像扔进水里,为它们悲悼,等于欧洲习俗中把死亡、雅丽洛、柯斯特罗马等等名义的死去的草木精扔进水中并为之哀悼一样。另外,这种习俗在印度,同欧洲常见的习俗一样,都是妇女们做的。人们对这种习俗的观念,即认为能使姑娘们配上好丈夫的想法,可以从人们相信的植物精灵能够促使男人同草木一样加快生育繁殖的观念得到解释。
第九节 用巫术招引春天
关于上述的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仪式,我们经过探索得出一般的解释,就是:它们原来都是巫术的仪式。目的是促使自然界在春天复苏。人们以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模仿和感应。由于对事物的真正起因没有认识,原始人以为要造出他的生命所依存的伟大自然现象,只有仿造这些现象。他在林间隙地、山岭峡谷、荒漠平原,或迎风在海岸演出的小小戏剧,通过秘密的交感或神秘的影响,能够立即引起更强有力的演员予以接受并在更大规模上再现出来。他想象通过用花草枝叶化装的办法,可以帮助荒芜的大地长出青翠的草木来覆盖自己,通过扮演冬天的死亡和埋葬,可以赶走阴郁的季节,为春天的回来铺平道路。如果我们觉得这一切对于我们是很难想象的,我们自己很难具有这样的思想境界,我们却可以比较容易地勾画出原始人的真切心情。当原始人最初开始提高了自己的思想,不仅只求满足自己肉体上的需要,而且还思考事物的起因的时候,可能已感觉到了我们今天称为自然法则的那种连续的自然变化。我们十分熟悉宇宙现象交相更替的一致性和规律性,不会相信产生这些效果的动因有朝一日会停顿下来,至少在最近的将来不会如此。可是,对于自然稳定性的这种认识,只有通过广泛观察和长期积累的经验才能培养出来。原始人由于观察的范围狭小和传统短暂,还缺乏这种经验的重要因素。可是却必须有这样的经验才能使他在永恒变化,并时常造成危害的自然现象面前心情平静。所以,毫不奇怪,日蚀月蚀会使他惊慌失措。他以为如果不大声喊叫并对空射出他那微不足道的箭矢来保卫日月的话,那么天上的怪物就一定要吞噬了它们,这两个天体就一定要毁灭。同样,漆黑的夜里忽然一片闪电照亮了大块天空,或者北极朦胧的光亮映照着一片苍穹,都会使他惊恐不已。这也不足为奇。甚至在一定间隔时期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在他没有人认识到它们的规律之前,也会对之忧心忡忡。对于自然界这些定期或周期性变化的认识的快慢,大多取决于某一特殊循环周期的长度。例如,昼夜循环的现象,除南北两极地区外,到处都是。昼夜循环为期既短,又极频繁,所以古人很快就不再担心它的反复出现。当然,我们也知道古代埃及人曾经每天施行巫术,使西天一片晚霞中沉没的、火红的天体在早晨回到东方来。可是一年四季节序的循环更替则远非如此。鉴于人生在世,岁月几何,一年光阴,在我们是非常宝贵的。但是在原始人看来由于记忆的短暂和计时方法的不足,一年的时间似乎如此漫长,根本认识不到它的周期规律。他怀着永恒的惊异,守望着天地景象变化,随着光热的更易,动植物生命的代谢,或有益于其逸乐,或威胁其安全,因之亦喜亦忧。秋天,刺骨的风卷起寒林中落叶,他看着光秃的树枝,疑虑它们还会再绿吗?随着冬季太阳一天天低下去:他疑惑它是否还能回复原先的天路旅程?甚至下弦的月亮在东方地平线上显得一天比一天缩小的时候,也会在他脑子里引起疑惧:一旦月儿全部消失了,恐怕就不再有明月了!
以上这些以及千千万万其他疑虑麇集在原始人的脑际,搅扰着他的心灵,他第一次开始思考他所生活的世界的神秘,筹划着比明天更远的未来。因此,很自然地,带着这些思想和恐惧,他要尽其所能试图使凋谢的繁花再绽枝头,使冬季低下的太阳旋回到夏天天空原来的高度,令下弦的月亮恢复银盘似的满盈。假如我们高兴的话,对于原始人这些徒然的努力可以报之一笑。然而,正是这些长期的努力实验(其中许多注定必然要失败),原始人们才从经验中认识到自己的某些努力无济于事,有些则获得了成果。无论怎样,巫术仪式毕竟只是一些试验,有的失败了,却仍继续在做,那只是因为,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些从事巫术的人们还认识不到自己的失败。随着知识进步,这些仪式或者已完全停止,或者当初兴此仪式的动机目的早已忘记,不过由于习惯力量尚在延续而已。它们已从原来的高位跌落,不再是某一地区人们福利与生命之所依和必须确切遵行的庄严礼仪。它们逐步降为单纯的壮观表演、化装游乐和消遣,并最终为年老人们完全舍弃。一度曾经是圣哲最严肃的职业,到后来却成了儿童的游戏。我们欧洲祖先的巫术仪式正是古代巫术衰朽没落最后阶段的东西,绝大部分迄今依稀残存,但正在受推动人类向新的未知目标前进的道德的、才智的,和社会的各种力量的荡涤。对于那些离奇习俗和别致仪式的消亡,我们可能很自然觉得有些遗憾,因为它们为我们这个似乎平庸沉闷的时代保存了上古时期某些清新别有风韵的东西,是这个世界的青春的气息。然而想到那些美好的仪式表演、那些现在看来是天真无知的娱乐,都有其愚昧迷信的根源。假如说它们是人类努力进步的记录,它们也是人类无成果的首创精神、白费劳力、历经挫折的希望丰碑。尽管它们有着鲜艳的服饰、鲜花、彩带和音乐,它们却更多地具有悲剧的性质而不是笑剧。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遗憾的心情就会大大减轻了。
我对这些仪式所有的解释,是紧追曼哈德的后尘的。自本书最初写成以后,一项新的发现有力地证实了我的解释。这项发现是:澳大利亚中部的土人还经常进行巫术仪式,目的在于催醒即将来临的可谓澳大利亚之春的自然界的处于蛰伏之中的能力。在澳大利亚中部荒芜地区,季节的转换特别突然、特别鲜明!那大片沙石荒野的地方,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凄凉。经过长期干旱之后,一连几天倾盆大雨,就一下子变成一片青翠的平原,出现大量的昆虫、蜥蜴、青蛙和鸟类。在这样时刻,大自然面貌的这一奇妙转变,连欧洲的目击者也比之为魔术般的景观,就无怪乎未开化的人们要实际这样看待它了。现在美好季节的到来已经在望,澳大利亚中部土人习惯特别爱在这时期进行巫术仪式,其公开的意图就是要大量繁殖他们的粮食作物和家畜。因此,这些仪式同我们欧洲农民春天的习俗极其相似——不仅时间上相近,目的也相近。因为我们很难相信我们的原始祖先在实行这些旨在促进作物春天复苏的仪式时,只是想闻到早开的紫罗兰的芳香,采撷最早的报春花,或观赏微风中摇曳的水仙,而不是从真正的实际考虑,即从人的生命同植物生命紧紧相连,如果植物生命毁灭,人也不能生存这一实际来考虑的,澳大利亚未开化的土人相信巫术仪式有效。通过观察,每当仪式以后,或迟或早,植物动物都有增产,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也证实了巫术仪式的效验。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古代欧洲未开化的人也是这样。看到丛林中的新绿,满布藓苔的河岸上绽开了春天的花朵,燕子从南方飞来了,太阳在天空越爬越高。他们欢迎这许多可见的标志,证明他们的巫术确有成效,鼓舞着他们更具愉悅的信心:他们按照自己愿望塑造的世界,一切都很好。只有秋天里,随着夏天的逐渐消逝,自然界衰败的征兆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忧虑,冲击着他们的信心:永远不教冬天和死亡来临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1] 德国的两个地区。
[2] 同上。
[3] 现为捷克与德国边境地区。
[4] 英文carnival,按音义合译为“嘉年华会”,亦译“狂欢节”或“谢肉节”,至今欧洲民间仍盛行。
[5] 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一译大斋首日,或圣灰礼日,或灰星期三,在复活节前第十四天,即四旬节的第一个星期三,这一天罗马天主教向忏悔者头上撒灰(棕榈主日使用的棕榈树叶烧成的灰),以示谢罪和忏悔。
[6] 在这里“狂欢节”(嘉年华会)被看成是一个男性神灵人物。
[7] 属西班牙。
[8] 法国旧时的一个省份。
[9] 法国的一个省。位于法国东北部,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之间多森林的高地。
[10] 现属德国。
[11] 德国境内。
[12] 德文,大意是:“上帝,我的父亲,你的爱竟像天空一样辽阔。”
[13] 德国莱茵河西地区,古巴伐利亚的一个地区。
[14] 属德国下萨克森州。
[15] 旧称,指乌克兰。
[16] 普里阿普斯(Priapus),希腊罗马神话中阿芙罗狄特与狄俄尼索斯的儿子,掌管园圃作物与繁殖之神。
[17] 湿婆(Siva),印度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即毁灭之神,善行之神,舞蹈之神。
[18] 帕婆提(Parvati),即雪山神女,湿婆的妻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