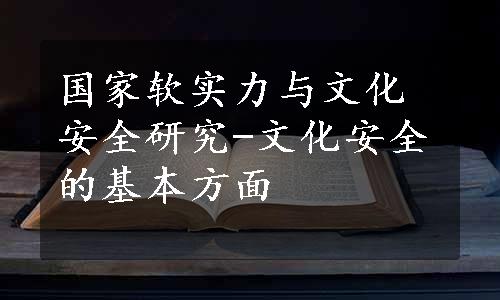
(二)文化安全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指的是国家利益、特别是重大国家利益免受威胁或危害的状态。传统的国家安全指的是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冷战结束后,经济安全日益重要。现在看来,全面的国家安全概念应该包括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安全和文化安全。因为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其他各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一国的综合国力,因此,文化安全是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
由于文化的内涵非常复杂和宽泛,在不同的语境下有不同的解释,所以,我们在理解文化安全时也必须考虑到特定的含义。
在一般情况下,文化是作为与经济、政治相对应的概念使用的,同时作为人类的精神成果与物质生产、社会秩序和制度相区别。文化是不同民族、国家、社会制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作为精神成果的科学技术等共性文化并不具有民族、国家和制度的身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无国界,其利益关系也就不具有此消彼长的“零和”特征,因此也就不存在文化层面的安全问题。当然,一个国家保护本国的科技秘密不被泄露,那是属于科技安全的问题,而不是文化安全问题,对此我们需要区分清楚。而文化心理、民族精神、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层面的个性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国家和制度的特点,这种带有个性的文化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根本前提,也与民族国家利益有着直接对应的关系。因此,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中的文化是指与不同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对应的个性文化,它们可以分为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化两个层次。国家的文化利益与主权就表现在对这种个性文化的发展和维护上。国家文化安全所关切的就是国家文化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国家文化主权是否受到侵犯,即这种个性文化是否得到独立自主地健康发展,是否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获得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与本民族、国家和制度相对应的个性文化由于不平等的国际文化交流而存在丧失其独立个性的危险,则国家文化安全受到威胁,反之,则处于安全状态。国际文化环境中的不平等交流主要体现为文化扩张与文化霸权,因此,文化安全是一个与文化扩张、文化霸权相对应的概念。
国家文化安全有两个基本方面,即意识形态安全和民族文化安全。 (1)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直接相联,靠国家政权来维护和传播,同时也为国家政权提供“合法性”的文化基础。国民的意识形态认同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巩固和稳定,缺少意识形态认同就意味着政权丧失其“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危机必然导致政权危机,因此,意识形态的扩张最终指向国家政权以及该政权保护下的特定利益。而民族文化及其认同则是国家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和国民凝聚力之所在。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一个民族正向的身份感,能产生强大的心理力量,给个体带来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因此,如果民族文化受到挑战或者质疑则民族认同就会出现危机,随之而来民族凝聚力的涣散不仅是一个民族衰落的征兆,而且孕育着国家危机。所以,民族文化的霸权解构的是一个民族独立自主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在这种冲突中丧失的是民族利益。
我们尤其需要注意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关系。当今世界,虽然处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但是全球化并不能消融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个民族历经千百年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文化大都已经深深融入了民族的血液中,很难被放弃和改变,尤其像中华民族的文化历经五千年而未曾中断,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化,人们很难想象会有什么文化能够改变它,会影响它的发展。像中华文化这样的文化发展只能是自我选择的发展。因此,文化霸权主义对待各种民族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中的精粹部分是难有什么作为的。当今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各种民族文化并不是一味地采取敌视的态度。实际上西方的文化霸权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这是特殊的历史背景决定的。
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来看,由于文化安全包括着对文化主体进行文化创造、文化管理、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等的独立自主权,又包括着文化主体对文化价值、文化传统、文化制度和文化行为等的继承权和选择权,所以文化安全必然内涵着意识形态的斗争。虽然文化不等同于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决定文化的主导价值倾向。(www.daowen.com)
冷战结束后,西方有两种观点风靡一时,这两种观点都反映了西方意识形态对东方意识形态的霸权。一是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二是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前者为资本主义的胜利欢呼,后者则为资本主义的未来筹划。两者都宣称意识形态不再重复,人类可以告别意识形态的斗争了。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世界及其价值体系可以一劳永逸地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亨廷顿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代替意识形态的斗争。其实,他们都是否定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普世化。
事实正是如此。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在这本书中,他提出美国要做世界的领导者,当然,这也不是什么新观点,因为美国一直以世界警察自居。布热津斯基认为当今世界比冷战时期复杂得多,美国面临的挑战甚至比“9·11”以前严峻得多。他说:“当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挑战美国的霸权,美国的力量对于全球安全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同时,美国的民主——和美国成功的范例——传播着经济、文化和技术的发展变化,从而促进了超越国界的全球性相互联系。然而,这些变化可能削弱美国力量力图确保的全球稳定,甚至会引起反美的敌对情绪。” (2)于是他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强大的国家,但同时其本土也是独一无二的最不安全的地方。他认为美国是具有全球性文化魅力的国家,“这种文化魅力逐渐深入、充斥、同化并重新塑造着人类越来越大的一部分人的外部行为,最终改变着他们的内心世界。毫不夸张地说,这种生活方式到处传播,潜移默化地起着重新定义的作用,它的穿透力势不可挡。没有任何一个大陆,也许甚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抵御它的影响”。 (3)
亨廷顿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方面“美国信念”从例外成为了普遍,民主制已被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至少在理论上承认它是治理国家的唯一的合理形式。另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永恒的……即使是最成功的社会,也会在某个时候遇到内部分解和衰落的危险,或是受到更加激烈和无情的外部‘野蛮’势力的威胁。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也会遭受斯巴达、罗马等国家的命运”。 (4)而保罗·彼得森则认为,冷战结束导致的后果会是“国家利益感日益模糊”,“为国家做出牺牲的意愿降低”,“对政府的信任下降”,“道义感趋弱”,“需要有经验的政治领导人的想法会减少”,没有外敌,个人利益会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因此,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亨廷顿等,作为美国利益的维护者,面对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他们仍然在思考美国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这显然是一种文化安全战略,是一种从“美国信念”和美国价值观出发的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安全战略,尽管他们在有意回避意识形态的提法,但实质就是意识形态战略。而他们为美国政府所设计和描述的对中国的战略思想更是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战略。
就让我们看看他们是怎样看待中国的。在他们眼里,“新世纪的最初几年,美国和其他西方利益的威胁来源多样化而且难以预测,威胁主要来自‘无赖’国家、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中国或俄罗斯”。 (5)所以,中国始终被看作是这样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它有着从一个地区性强国发展成为超级大国的实质性潜力,尽管需要经过几十年之后,它还仅仅开始赶上冷战时期的超级大国。纵然如此,中国在第三世界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潜力,展示了其有可能集中力量挑战美国的政治经济优势”。 (6)所以,美国一直认为,在技术上保持对中国的优势,仍将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主要关注的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中国眼下最需要的是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假如美中关系处于对立状态,这两样东西中国就得不到。所以,“中国人比任何人更清楚,他们缺乏——而且在一定时间内将继续缺乏——挑起重大军事事端的能力。任何导致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的局面对中国都将是一场灾难。美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封锁中国”。 (7)尽管如此,美国还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和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其终极目的都是保护美国自身的文化和价值的生存与发展。无论怎样看,这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进攻。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