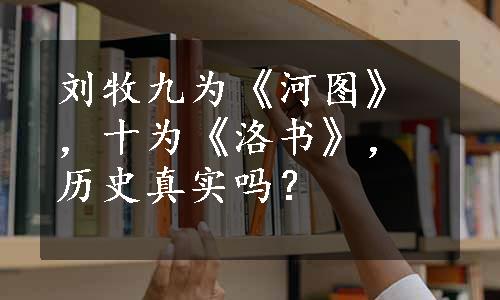
答:笔者曾在《周易研究》上发表《易数钩隐图作者等问题辨》一文,指出在三衢刘牧(1011—1064,字先之,尚书屯田郎中)之前,还有一位彭城刘牧(字长民,太常博士)。
《中兴书目》所记《易数钩隐图》一卷,是为前刘牧所撰。彭城刘牧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按《东都事略》所记,陈抟于端拱二年(989)秋七月二十二日化形于莲花峰下张超谷中。彭城刘牧于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致仕,其时陈抟已仙逝17年。陈抟所传的象学,也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既然范氏之学传于南方,而范氏晚出,那么就不会传给其前之彭城刘牧。由此可知,范谔昌不可能为彭城刘牧之师,彭城刘牧并没有得到什么“河洛”图书之传承。
本《中兴书目》所记,考定彭城刘牧原著《易数钩隐图》为一卷本,按其自序(见于《道藏·易数钩隐图》卷首,胡渭《易图明辨》、朱彝尊《经义考》亦引用之),有“原其本,则形由象生,象由数设,舍其数则无以见四象所由之宗”“两仪变易而生四象,四象变易而生八卦”“今采摭天地奇偶之数,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于逐图下各释其义”等说,依此可知,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以自序对照今见《易数钩隐图》前二卷,其所“钩隐”之图则是从“太极第一”至“七日来复第四十六”,其中并没有涉及黑白点“河图”与“洛书”。一卷本《易数钩隐图》的作者是本《系辞》“易有太极”一节之义而阐明其“象由数设”意图的。特别指出“河出图,洛出书”为“圣人《易》外别有其功,非专《易》内之物”,彭城刘牧一语道破并八卦之画与“河出图,洛出书”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如果彭城刘牧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出图,洛出书”而画,那就是说“河出图,洛出书”应该为《易》内之物,他便不会有如此相反之说。
彭城刘牧既然说“河出图,洛出书”非《易》内之物,并不主张八卦是圣人则“河图”(或“洛书”)而画,而是主张八卦是由太极步步生出来的。
《中兴书目》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吴秘表进,田况序。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所谓“言数者皆宗之”,并非谓“言河出图者皆宗之”。从今见《易数钩隐图》卷上的内容看,彭城刘牧主张“象由数设”,自太极生两仪至四象生八卦,皆以天地生成之数“凡五十五位”点之成图,的确在当时自成一家之言,庆历初(1041)呉秘献其书于朝,优诏奬之之后,言数者皆宗之也是情理中事。以倪天隐述其师胡瑗《周易口义》为例,仁宗时之胡瑗释《易传·系辞》“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时,则曰:“义曰,按此河图,是天之大瑞也。”于此可见胡氏并没有宗《易数钩隐图》下卷之说,以黑白点数之图释“河出图,洛出书”。至释“两仪生四象”时则曰:“义曰,言天地之道阴阳之气,自然而然生成四象,四象者,即木金水火是也。故上文谓天一下配地六生水,地二上配天七生火,如此之类,是天地阴阳自然相配,生成金木水火之象。然此止言四象而不言土者,盖天地既判生为五行,然二气既分,则自然生而为木金氷火,则地之道本于土而成,但言四象则土从可知矣。”及释“易有四象所以示也”则曰:“义曰,按此四象有二说,一说以谓天地自然相配,水火金木以为之象,所以示也;又一说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是言大易之道有此四象,所以示人之吉凶。疏庄氏谓,六十四卦之中有实象,有假象,有义象,有用象,则非也。又何氏以为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亦非也。”于此我们却从中见到胡氏“宗之”《易数钩隐图》卷上之说的痕迹。
康定元年(1040),宋咸作《王刘易辨》,自序中有“近世刘牧既为《钩隐图》以画象数,尽刋王文,直以己意代之”语。此“近世刘牧”当指彭城刘牧而言,而三衢刘牧时当30岁,仍健在,宋咸不会针对三衢刘牧而有是语。又宋咸所辨是针对“《钩隐图》以画象数”,并没有辨什么“河洛”图书。以此推之,宋咸所见《易数钩隐图》,似当为彭城刘牧著之一卷本,书中并没有“河洛图书”的内容。一年之后,庆历初(1041)黄黎献弟子呉秘献《易数钩隐图》等书于朝,此时已经是彭城刘牧赴边任武官15年之后。(www.daowen.com)
庆历七年丁亥(1047),李觏作《删定刘牧易图序》,存其易图者三:河图(“九宫数”戴九履一图)、洛书(合生数、成数二图为一)、八卦图(《说卦》所言方位)。由此可见,吴秘所进《易数钩隐图》不再是一卷本,其中已有今见三卷本卷下之“河洛”诸图。这就是说,此时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已经“颇增多诞谩”。如此,我们可以推断,彭城刘牧原本《易数钩隐图》只是有“自太极生两仪而下至于复卦”的易图四十六幅的一卷本,其中并无“河图”“洛书”等图,而今见三卷本之卷下之“河图第四十九”“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等图,诚如李觏所言,的确是“观之则甚复重”:“河图天地数第五十”既是卷上之“天地数十有五第四”;“河图四象第五十一”既是卷上之“两仪生四象第九”;“河图八卦第五十二”既是卷上“四象生八卦第十”;“十日生五行并相生第五十五”既是卷上“二仪得十成变化第十一”。至谓“颇增多诞谩”,则“河图第四十九”“洛书五行生数第五十三”“洛书五行成数第五十四”三图乃是不合于一卷本作者自序本意之图。从文字上看,卷下有“河图、洛书出于牺皇之世”“龙图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韫。且其图纵横皆合天地自然之数,则非后人能假伪而设之也。夫龙图呈卦,非圣人不能画之”“河图相传于前代,其数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义,而兼五行之数,洛书则惟五行生成数也,然牺皇但画卦以垂教,则五行之数未显,故禹更陈五行而显九类也”等说,显然有悖于卷上原作者自序之初衷。
是何人增多彭城刘牧原一卷本之《易数钩隐图》,并加入所谓“河图”与“洛书”之图与图说?以彭城刘牧弟子黄黎献著有《续钩隐图》一卷的情况来看,似乎吴秘所进之书为合彭城刘牧原著与黄黎献之续著为一书。倘若如此,则“河图”与“洛书”(有“洛书五行生数”与“洛书五行成数”两幅图)的始作俑者,就是黄黎献无疑了。无论如何,“河图”与“洛书”诸图不出自彭城刘牧之书,这是毫无疑问的。
三衢刘牧(1011—1064)于景佑元年(1034)登进士榜,累官至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王安石所作墓志铭谓其“学《春秋》于孙复,与石介为友”,叶适谓其“当时号能古文”。今见其遗文有《待月亭记》《送张损之赴任定府幕职序》(以上见《宋文鉴》)、五言排律《仙李洞》(见《廣西通志》)。三衢刘牧没有专门易学著作存留于世。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録解题》针对三衢刘牧后裔刘敏士刻于浙右庾司,前有欧阳公序之《易数钩隐图》提出了疑问,曰:“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案,敏士序称伯祖屯田郎中,临川先生志其墓。今观志文所述,但言学《春秋》于孙复而已,当庆历时,其易学盛行,不应畧无一语及之。”如果三衢刘牧果真著有“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颇有影响之《易数钩隐图》,那么深明易学之王安石怎么会作墓志时“无一语及之”呢?事实上,恰是从王安石所作《荆湖北路转运判官尚书屯田郎中刘君墓志铭并序》中看出,《易数钩隐图》一书本不出自三衢刘牧之手。南渡后三衢刘敏士重刻三卷本《易数钩隐图》,并明注为其伯祖三衢刘牧撰,又伪造欧阳修之“序”,遂使见此书者误将三衢刘牧当做彭城刘牧,此则刘敏士之徒,实是引起后世之疑的肇事者。前此《中兴书目》早已明言“本朝太常博士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牧字长民,彭城人,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至南宋陈振孙始见刘敏士之刻本,因而《直斋书录解题》方有如此之疑问。此误之传,愈传愈真,愈传愈广。至明道士白云霁撰《道藏目録详注》,除谓《易数钩隐图》三卷,《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一卷,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外,又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亦“三衢刘牧撰”。实则此三书皆非“三衢刘牧撰”。《易数钩隐图》一卷本为彭城刘牧撰,《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原名《先儒遗事》,南宋郑樵《通志》记或谓陈纯臣撰,是书中有《易数钩隐图》中数幅图,刘牧岂能自称“先儒”?“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六经图》中之《易经》图总名(其他五经亦各有总名,分别是:尚书轨范撮要图,毛诗正变指南图,周礼文物大全图,礼记制度示掌图,春秋笔削发微图),是书即不是三衢刘牧撰,也不是元张理撰,本为南宋杨甲撰,毛邦翰增补,叶仲堪重编之《易经》图版本。至清初,黄宗羲著《宋元学案》,于《泰山学案》中谓泰山孙复弟子三衢刘牧著有《易数钩隐图》及《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乾隆间四库馆臣亦深然白云霁之“详注”,《四库全书》提要中照样谓《易数钩隐图》与《易数钩隐图遗论九事》二书,皆为“三衢刘牧撰”,而又误考白云霁之注,谓《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元张理撰。
三衢刘牧与一卷本及三卷本《易数钩隐图》毫无关系;朱震等所言“河洛图书”的传承代次,多是瞎说(胡适语),不可再引以为据;华山陈抟及范谔昌所传“象学”,并非“河洛图书”之内容;黑白点“河图”与“洛书”出现于彭城刘牧著一卷本《易数钩隐图》之后,是其弟子黄黎献所为,而且有三幅图。到了仁宗年间,李覯合为二幅,九数黑白点为《河图》,十数黑白点为《洛书》。历史事实证明,恰恰是朱熹易置了李覯的“图书”。所以《易学启蒙》谓“惟刘牧臆见,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言出于希夷”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朱熹和蔡元定根本不了解北宋有二位刘牧的历史事实,也不顾李覯书中列有九数《河图》和十数《洛书》的历史事实,甚至污蔑刘牧“易置图书”。此种作学问的态度,实不足取。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