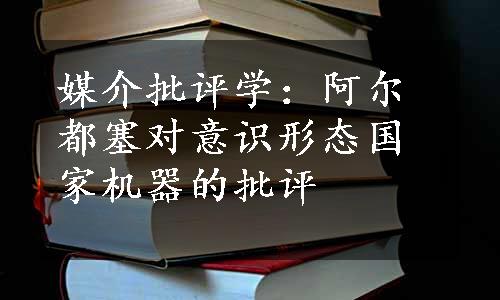
路易·皮埃尔·阿尔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1918—1990),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37年进入里昂一所知名中学读书,课业表现优异,后被最高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录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阿尔都塞成为德国战俘。在战俘营中,他接触了共产主义。1945年重返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在哲学家巴歇拉尔指导下研究哲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并于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62年升为教授,1975年通过答辩,又被庇卡底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1980年患精神病,退休疗养。
阿尔都塞长期在大学执教,但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积极参与现实斗争。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围绕马克思主义同人道主义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他同“新左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发表了《孟德斯鸠、卢梭、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自我批评》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在批判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黑格尔化的思潮中,他以“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威胁的正统捍卫者”姿态出现,在党内外赢得了颇高声誉。在他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吸取的不是辩证法和异化概念,而是“无主体过程”的哲学范畴。马克思主义是从费尔巴哈抽象的“人”、“人道主义”的决裂中产生,严格地说,它是“理论反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的历史理论是社会科学中发现的“新大陆”,而作为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却以“实践状态”仍包含在《资本论》等著作中,还有待于从理论上系统阐述。阿尔都塞按照“对应阅读法”,把《资本论》作为认识物件,进行了深入研究,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中抽取出来。所以,他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定义为“理论实践的理论”。实际上,他是运用“多元决定”、“结构因果性”等结构主义原则概念,对社会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作了新的解释,认为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按一定结构方式构成的复杂统一体,历史的发展不是按“人的本质的异化”和“扬弃异化”的人道主义方式进行,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无主体过程”。
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中,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的部分就是其意识形态理论,尤其是他首先创用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观点对媒介批评具有一种方法论的意义。这一理论集中体现在他1965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和1970年在法共机关刊物《思想》杂志上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篇文章中。尽管由于写作的背景和关注的方向有很大区别,文章各有偏重,但毕竟只相隔数年,其基本观点仍然一致。由于阿尔都塞首先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到社会物质生产结构当中进行讨论,在很大程度上绕开了将意识形态当成精神现象或理论(知识)体系的普遍思路。
在探讨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时,阿尔都塞继承了葛兰西对于国家和意识形态的有关论述,运用结构主义重新解释了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他沿用了葛兰西的模式,把上层建筑分为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两个部分。前者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等强力系统,后者包括学校、教会、工会、传媒等组织,后者虽然不受国家控制,但仍然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最大特色是:貌似中立,自诩公正不阿。例如传媒一贯宣称客观性是处理新闻和评论的准则,媒介会“公平”地对待各种社会群体,但其用以衡量公平的标准,可能已经不自觉地采用了白人男性中产阶级的看法。(www.daowen.com)
阿尔都塞把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改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着特别的用意。两种提法的外延虽然重叠,但寓意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将传媒等文化机构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而不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更能凸显出这些文化机构与现行国家霸权体制的关系。其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提法指向一个更为广阔的意识形态分析领域。在葛兰西那里,意识形态还只是一个内在的观念系统,意识形态分析也还只限于一般的文本分析或内容分析。但在阿尔都塞那里,意识形态已经从一堆隐蔽的、无形的观念中走了出来,而具有了一定的物质性。根据阿尔都塞的定义,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实际生产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再现”。[4]既然是“再现”,当然要是可见的、有形的东西,才可以再现——这就是为什么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具有物质性”的原因。文字符号是这样一套再现系统,我们日常的行为、社会例行的行为、各类组织的活动,又何尝不是一套再现的系统?于是,意识形态由此进入了能指的层面,不再只是被动的所指。也就是说,它不再只是人们极力去“再现”的东西,“再现”的行为和过程本身就已经是意识形态,或具有意识形态性了。所以,从这一角度上来看,传媒的意识形态批评不应只是聚焦在传媒的文本上,传媒例行的仪式、传媒生产的过程、传媒的组织架构等等,都是重要的“再现”方式或者是“再现”的内容,都值得作意识形态分析。
阿尔都塞认为,召唤(interpellate)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建构主体的主要机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并没有强制性的推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只是告诉人们,什么方式的行动和思维是最自然不过的行动和思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是靠强制性的手段来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统一、稳定,而是通过不知不觉的传输、渗透让个体自觉地接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提倡和认同的行动和思维方式。人们一旦接受这种“自然法则”,就会自觉地复制这种行动和思维方式,并通过这种复制来再现特定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要把个体建构成某种角色,即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主体——即儿子、父亲、丈夫、学生、工人等等,而这一建构是在一片亲切自然的召唤、询唤及叫喊中完成,从而成为召唤主体。召唤主体认为自己是由自我决定,觉得自己在直接地把握现实,处于一种自由自主的独立状态。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有将个体“召唤”或建构成主体的功能,如同在街上听到别人叫唤自己的名字,在一瞬间会意识到“我”的存在一样,意识形态也向我们发出深沉的“召唤”,但并非要将我们“还原”成张三、李四等个体,而是将我们“再造”成统治权力架构可以接纳的角色或意识形态主体。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早在我们呱呱坠地之前,意识形态已经预设了我们的主体,我们已经接受了某些“预先的任命”。例如,我们必须跟随父姓,必须接受一个较高尚的地位(如果出身高贵的话)或一个较低下的地位(如果出身低微的话)。
可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政治无意识”所依附的真正物质基础,是对个体进行体制化规训和合法化“生产”的领地,是一套看似温和却弥漫着神秘暴力的社会调控工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资产阶级法学或伦理学体系对公共/私人领域的区分,深刻揭示了公共领域对私人领域的渗透和作用,尤其强调了公共法则对私人领域的控制。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去揭开日常生活和文化的秘密,恢复社会领域本应该拥有的批判活力。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当中,传播媒介是具有“召唤”功能的一种重要形式。一些传播学者曾应用这一“召唤”理论,研究媒介的“主体化”功能及其作用机制,如分析广告如何制造幻觉,把读者建构在“主动的接受者” 的地位;分析电影摄影机“如何为观赏者制造特定的认同方式”。特别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张昆教授对媒介“政治社会化功能” 的分析,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尤具旁证意义。张昆教授通过大量的实例和细密的论证指出:“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利用大众媒介广泛而持续的传播活动,在政治社会化对象的心理世界建构现代的政治价值体系,即爱国主义理念、国家民族统一的目标,政治系统的稳定和法治、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价值,对于丰富公民的政治认知,形成正确的政治态度,塑造健全的政治人物,进而推进政治发展,保持政治系统的有序运行,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5]这一论断,既与媒介的涵化理论有相通之处,又可以认为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中的具体应用。这也证明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对媒介批评具有一定的方法论意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