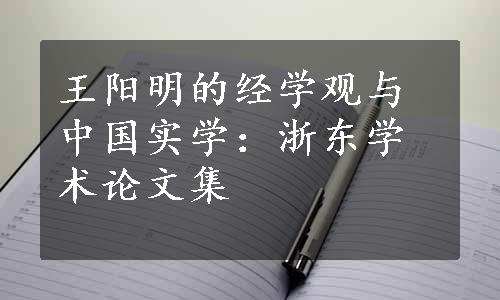
李明友
王阳明的经学观还有一种表述,即是“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这一提法,与其所谓的“敦本尚实,返朴还淳”的提法基本一致。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的提法,出自王阳明《五经臆说序》一文。《五经臆说》原有四十六卷(其中《易》、《书》、《诗》、《春秋》各十卷,《礼》仅六卷),后散失殆尽,仅存十三条及序文一篇。
《五经臆说》是王阳明在贵州龙场谪居时所写。当时的情景,《年谱》有如下描述:
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瘅疠,与居夷人鴃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士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士架木以居。时或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墎自誓日:“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因念:“圣人此处,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居久,夷人亦日来亲狎。[2]
这就是后人津津乐道的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情况。而《五经臆说》则是“龙场梧道”的文字结晶。从梧道的具体情况看来,王阳明不是为注经解经而作《五经臆说》的。首先,他反对繁琐的注疏而不屑为,自然不会像历代经学家那样去做注疏工作。另夕卜,当时恶劣的环境也不允许王阳明做注疏工作,因为他手头没有做注疏所需的大量书籍、资料。再者,他是在“中夜大梧格物致知之旨”,“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之后,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而写下《五经臆说》的。可见,王阳明所悟之道来自于《五经》,他依据《五经》梧出与朱熹不同的格物致知之旨,即“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而《五经臆说》,正是他悟道所得之记录,并非注经解经之作。王阳明在《五经腌说》中也说:
龙场居南夷万山中,书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记旧所读书而录之,意有所得,皆为之训释,期七月而五经之旨略遍,名之日“臆说”。盖不必尽合于先贤,聊写其胸臆之见,而因以娱情养性焉耳。[3]
“娱情养性”,便是其录写《五经臆说》的初衷。它不是注琉,而是“聊写其胸臆之见”的自我抒发。“臆说”之名也由此而来。
王阳明抒发胸臆之见,强调读经务求把握经书的精神实质,不可被文字语言名物训诂所束缚。他在《五经臆说》中说:
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签与糟粕也,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窃尝怪夫世之儒者求鱼于茎,而谓糟粕之为醪也。夫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鱼于茎,则筌与鱼远矣。[4]
《系辞传》曾引孔子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说法,而庄子则进一步以“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说明“得意而忘言”。玄学家王弼则以此说明“得象在忘言”、“得意在忘象”的方法论。(www.daowen.com)
实际上,中国古人关于言、象、意之辩,即是今人所谓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关系的讨论。语言、符号是为了表达思想的,但语言、符号能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呢?而主张“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观点则已包含着“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观点。就是说,即使是圣人的经典,其语言文字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而作为学习经典的方法,“得意忘言”强调把握经典的精神实质,反对拘泥于语言、文字。王阳明在此序文中并没有就言象意之辩展开讨论,只是借此说明他“聊写其胸臆之见”的《五经臆说》重在把握《五经》的意义即精神实质,而不着重于经典的文字语言名物训诂。不过,王阳明这篇序文所表达的,并不完全仿照、沿袭古人的“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说法,还是有点新意的。王阳明除了用“得鱼而忘筌”的比喻以外,还用了“醪尽而糟粕弃之”的比喻。他认为,后世儒者求鱼于筌,是一种十分错误的方法,因为:“筌与鱼远矣”,筌是捕鱼的工具,捕鱼时需要它,除此之外,筌与鱼毫不相干,倘若老想从筌中得到鱼,那不会有任何结果。而醪与槽粕的关系则不同,“糟粕之中而醪存”,所以“谓糟粕之为醪,犹近也,”不过,人们的目的是从糟粕中提引出醪,所以一旦醪尽,可将槽粕弃之。将经书中的思想意义与语言文字的关系,比作醪与糟粕的关系,要比鱼与筌的比喻更加贴切些。思想意义寄寓于语言文字之中,或说语言文字之中寓存思想内容。人们可以从语言文字中把握思想内容,但如果一味执着于语言文字,把握不了思想内容,那就像老拿着槽粕而不从中提引出醪一样。因此,王阳明这一比喻,说明他看到了思想意义与语言文字的内在关系,求取思,想意义,当然离不开语言文字,只不过不可偏执语言文字而放弃思想意义的把握。应该说,这一比喻要比鱼与筌的比喻更合理些。
王阳明重提“得鱼而筌,”又提出“醪尽而槽粕弃之”,进一步讨论言、象、意之间的关系,当然是有所指的。治经学史的人,往往区别汉唐时期和宋明时期儒家治学的学术方法与学术风气。前者注重名物训诂,后者注重义理理解和发挥,而后者是为了纠正前者的。然而,宋元明时期,尤其在朱熹的思想学说被官方定于一尊,《四书章句集注》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本之后,学术风气又开始窒息,学术方法又误入蹈旧,唯朱子为是,不敢更张,“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正是当时僵化局面的极好写照。
朱熹在经学上的成就是极其辉煌的,几乎所有的经典,他都作过注解发挥,其代表作有《周易本义》、《易学名蒙》、《诗集传》、《诗序辨说》、《家礼》、《仪礼经传通解》、《四书章句集注》等。朱熹的经学方法,确是注重义理理解和发挥的典范。在学术的方法上,王阳明是继承朱熹的。不过,在基本一致的方向下,有没有区别呢?一些研究者指出,王阳明与朱熹同样注重对经书的义理发挥,从方法上讲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具体的理解和发挥上有区别,比如对“格物致知”,朱熹理解成"即物穷理”,日久积累,达到豁然贯通,王阳明则认为天理良知在吾心中,致吾良知于事事物物即是格物致知等等。可以说,王阳明在经学方法上与朱熹在根本上没有多大分歧,其区别在于贯彻发挥义理方法的程度。王阳明以为,朱熹对经书的义理发挥留下的文字语言,同样存在着文字语言与经书本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当朱熹后学拘泥于朱熹注经解经的文字语言而不断重复,不思发展的时候,又阻碍了人们对经书本意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可以说,王阳明并不是反对朱熹治经的方法,而是反对朱子后学治经的方法。所以,他重提“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弃之”的方法,除了批评汉唐时期的注重文字训诂的学术方法之外,主要是批评朱子后学的拘泥于朱子文字蹈旧的风气。如果我们采用学术界所谓“汉学”与“宋学”的区分的话,这里的问题,可说成是有关“宋学”内部的分歧问题。而“宋学”内部的分歧问题也关涉“言”与“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重提“得意而忘言”“醪尽而槽粕弃之”的方法论,其意义就在于打破新的经学垄断和经学教条。也就是说,正在发挥义理的“宋学”,依然存在着如何正确处理“言“与“意”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前人发挥义理而形成的文字语言,倘若成为后人的障蔽,那就得破除,所以要重提“得鱼而忘筌”、“得意而忘言”的方法,同样因为它适用于这些“后学”。也正因为如此,王阳明后来“自觉学益精,工夫益简易”之后,再不将其早年所写的《五经臆说》示人,当其弟子问起时,王阳明笑日:“付秦火久矣。”弟子问其缘由,王阳明说:“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典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5]王阳明不希望自己以前所留下的文字成为后人的障蔽和束缚,将其付之秦火,也可谓“得鱼而忘筌,醪尽而糟粕之”也。
(作者系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1]参看拙文:《致本尚实,返朴还淳——王阳明的经学观》,载《中国哲学史,2005年第二期。
[2]《王阳明全集》第1228页。
[3]《王阳明全柒》第876页。
[4]《王阳明全集》第876页。
[5]《王阳明全集》第976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