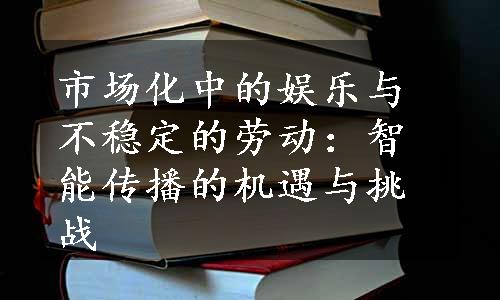
在向波兹曼式“娱乐至死”前行的路上,中国的步调机警而审慎。这如同玛丽·加拉格尔(Mary Gallagher)对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顺序的精辟见解,市场改革小心翼翼地从经济领域的边缘地区与非核心部门开始,以避免社会主义遭受正面冲击[15]。而与历经40多年转型的市场领域相比,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是社会主义的心脏,其市场化在近些年才逐渐放开。实际上,对大众娱乐的警惕根植于革命年代的传统中。在糖衣炮弹的警示下,五花八门的综艺娱乐与颓废柔弱的靡靡之音被认为会瓦解群众的革命斗志,可以说意识形态与文化战线的重要性不可小觑。但在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不能被忽视,而让人们离开美剧和日韩综艺的最好方式显然是打造中国自己的文化产品。所以,即便在为民众提供娱乐产品上,国家仍然处于纠结中,但文化产业的市场化还是一步步地推进着。2009年,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开始效仿国外的“制播分离”模式,进行本土综艺节目制作。此后,各方资本迅速涌入综艺娱乐节目制作领域,这使得我国电视节目制作机构从2007年的2874家攀升至2014年底的8 563家[16-17]。
C公司面对的市场环境并不友好。从全球范围看,文化创意产业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场域,市场风向不断变化、资本之间兼并重组不断。在这里,几家寡头周边聚集了大量小而灵活的企业,后者相互抢夺生意,随时面临破产[18]。中国的情况则更令人担忧。国家虽然大举推动文创产业的发展,但诸如版权保护等制度规范尚待优化。行业大举发展之时,资本间的竞争却无序而残酷,虽然项目与商机俯拾即是,但风险也随处可见。此时,市场各方小心翼翼、各逐其利,位于上游的播出平台毫不手软地将风险转嫁给了下游制作公司。从2012年开始,C公司针对某档知名综艺节目与Z电视台签订了对赌协议:节目虽能在Z台播出,但由C公司承担节目制作的所有成本与投资风险,只有在收视率超过特定比例时,制作方才能参与利润分成。C公司步入了一场豪赌,这背后的资本逻辑昭然若揭:要么赢得盘满钵盈,要么输得片甲不留。
为了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大多文创企业使用了“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玩工”(playbour)等免费劳动者进行生产[19,11]。当然,这里还是实习劳动的重灾区,这里的劳动者被称为“学生数字劳工”“看不见的劳动者”和“希望劳工”[2021]。C公司的情形也与此类似。其正式员工限制在300人左右,为了完成节目制作任务,公司招募了大量项目实习生。项目实习生不同于校招实习生,后者以应届生为主,实习期结束后就能够转正,而前者以大二、大三的在校生为主,劳动时长以项目时间为限。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内,实习仅仅作为社会实践,他们与实习单位不存在隶属关系,其劳动亦不受《劳动法》与《劳动合同法》的保护[22-23],所以企业不为其发放正式工资、福利,不为其缴纳社保,也不制定与之相关的正式制度。“物美价廉”的优良特性使实习生成为节目制造业中的劳动生力军,各制作公司不间断地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实习招募启事。在寒暑假等热门档期,多个大型项目同时运作的情况下,C公司实习生数量往往在300名以上,甚至超过了正式职工的数量。
实习生由导演团队招收管理,其眼光审慎而苛刻。我经历了两轮面试才进入W导演团队——这支团队负责某档知名综艺节目的宣传工作,并与腾讯视频合作推出其线上衍生节目。与我一同进入该团队的还有另外19名来自全国不同高校新闻学、广播电视学或影视制作专业的在读学生,所有人都熟练掌握摄影、摄像、剪辑等媒体制作技能。令人惊讶的是,W团队一共只有5名正式员工——其中2名是总导演和执行导演,其他3名员工带领与指导实习生进行具体工作。后来,我从其中一名正式员工的口中得知,自己之所以能够进入该团队,是因为既会做剪辑又参与制作过一档养生节目。
在项目制的运作方式下,对赌协议的压力转嫁到核心导演团队中,可想而知,这压力最终落到了实习生头上。W团队参与制作的这档综艺节目共有十二期,每一期的制作都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台本制作、中期现场录制和后期画面剪辑。从项目整体运作上看,每阶段约占一个月时间。进入项目中期后,为将就艺人时间,需要两期联制,这意味着我们每天工作12小时,每周工作60小时左右,而且周四、周五这两天会连续工作30个小时。然而,尽管每一阶段都充斥着高强度的劳动,但实习生快乐的状态持续在线:在头脑风暴中绘声绘色地表演自己的提案、在幻彩缤纷的录制现场兴奋地跑来跑去、在通宵剪片时哈哈大笑。最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档综艺节目播出效果惊人、收视率屡创新高。
2015年,这档综艺节目大热,其广告收入超过了20亿元人民币,其中插播的60秒广告价格被卖到了3000万元的高价,W团队制作的线上衍生节目的广告收入也高达2000万元。该年,C公司的营业收入超过13亿元,利润超过11亿元,利润率高达85%[5]。但实习劳动几乎是无薪的。在W团队项目经费存在盈余的情况下,实习生能够每月支取1000元到2000元的津贴——这低于上海市2015年每月202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实习生们必须依靠父母补贴的生活费才能留下来继续工作。若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公式进行计算[24],这项劳动的剩余价值率高达216%,为传统产业望尘不及[6]。
C公司的高额利润后隐藏了一个控制难题,即怎样使实习生人尽其用。这一难题源于三方面因素:第一,行业与生产本身的独特性对实习劳动提出了更高要求。我们发现,传统企业往往要求实习生承担打印资料、做PPT、给老板冲咖啡等辅助性工作,而IT技术公司会直接支付写代码的大学生以计件工资作为激励。而C公司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需要利用无薪劳动来填补资金与劳动力的双重缺口,在收视率和点击率的要求下,管理方需要实习生同正式员工一样全面地投入体力、创意和情感。这显然为劳动控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www.daowen.com)
第二,在工具理性的追求下,大部分实习生的目的是获得实习经验以及了解职业行情,他们并不打算将自己全身心地奉献给企业。问到为何来C公司实习时,莹莹的回答很典型:
“我之所以会来C公司,是因为舍友说在这里能见到明星,能去美国和中国台湾出差,伙食好。我想,她能来,我为什么不能来?而且,我想要一段实习经历和到领先的电视制作公司体验一下。我要把传媒圈全部实习一遍,了解整个行业生态、自己的兴趣、本身可能擅长的,要了解自己在职业方面有没有发展空间。”(实习生莹莹访谈,2017年10月28日)
实际上,W团队所有实习生都有在传媒机构的实习经验,甚至有人创过业。他们来C公司的目的是想了解制作公司的状况,以寻找自己的兴趣方向和就业可能。从大家的毕业去向来看,留在节目制作业的实习生仅有5名,还有7名实习生毕业后的去向与传媒完全不相关。实习的暂时状态与过客心理会增加劳动控制的不确定性。
第三,实习生的工作动力往往由“志愿者热忱”所推动,他们虽踌躇满志,但缺乏耐久力。罗斯·佩林(Rose Perlin)在《实习国度》(Intern Nation)中明确指出,尽管实习生在劳动初期往往充满热情、全心投入,但随着志愿情结与好奇心的消失,他们就会开始因为没有薪水而懈怠,这往往使管理者对激励实习生感到无能为力[20]。如何使劳动者保持热情和投入的状态是实习劳动的一大难题。
C公司高额利润的背后隐藏了一个控制难题,即如何使实习生自觉自愿地抛开学校课业和个人生活,在三个月的项目运作期中,全时段、全身心甚至疯魔地投入到娱乐性劳动中。进一步来看,当企业并不提供经济激励和内部劳动力市场升迁激励时,管理控制何以有效?当劳动强度令人精疲力竭时,情感整饰何以可得?当劳动合同无从可觅、口头协议无处可鉴时,雇用控制如何可达?我们发现,单纯的工具理性或短暂的志愿者热忱都不足以解释上述问题,只有进入C公司W团队的实际劳动中,才能洞察新产业中劳动控制与意识形态支配的隐秘核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