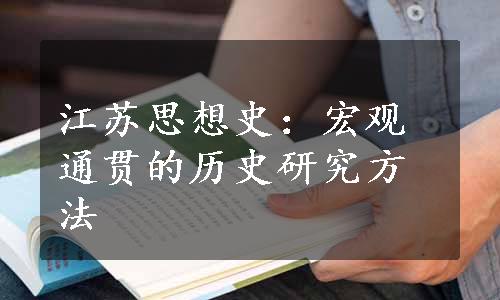
钱穆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著名的史学大家之一,不仅留下了大量的史学著作,而且也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这些方法有的是继承前人,有的是他自己摸索、实践得来的。
首先,钱穆继承了中国传统读书人治学的精华,他认为要做好学问,必须将考据、义理和辞章三者结合起来。传统中国学人在治学过程中各有侧重,如宋明理学重义理阐发,清人则多侧重考据之学,而桐城派则较重辞章之学。钱穆综合诸家治学之长,认为考据是为“求实”服务,义理可以挖掘历史的意义和功用,而辞章则是写出好的史学著作必备的基本功底。钱穆在当时提出这种治学方法也是为了校正当时学界治史之风气,如傅斯年从德国留学回来,学习了德国大史学家兰克的治学方法,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单纯追求史学求真的面向,而放弃了史学的其他功用。当然,除了傅斯年的史料学派之外,史学界还有一“革新派”,该派的特点恰恰在于为理想之目的而罔顾事实,信口开河,正如晚明心学末流那样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因此,钱穆强调考据、义理与辞章三结合的治学方法不仅是继承前人治学之精华,也是矫正学风之努力。同时,钱穆治史注重主客观的统一,即在重视史实的基础上,也重视治史者的“史识”,他认为纯粹客观地还原历史是不可能的,史家只能在他所掌握的史料基础上进行加工。因此,历史学家的作品必然会带有他的主观性,因为不同的史家在知识结构、思维看法、伦理价值取向方面都不完全相同,即使面对同样的史料也可能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虽然人的主观性可能带来历史事实的失实,但是钱穆鼓励史家发挥主观能动性,写出适合自己时代的史学作品,如对侠客的描写,要根据时代对“侠义”需求与否来进行加工,在诸国纷争的乱世之中,荆轲、聂政、专诸这些人在史家的笔下既可以是侠义的代表,在“大一统”的王朝体制下,也可以是“以武乱禁”的豪强恶霸。这或许也就是当代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其中之意,人们往往是根据时代来评判历史。
其次,钱穆强调学贵主“通”,这也是继承了传统史学中“贵通不贵专”的治学特点,自司马迁《史记》之后,中国史家治史就有了一个标杆。司马迁理想中的史学著作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内容宏富,从时间上看,上至三皇武帝,下至汉武帝;从内容范围上看,政治、经济、人物、天文、地理等无所不包,充分体现了“通”的特点。到了近代,西方学术的观念和方法传入中国,学问逐渐向专门之学发展,但是钱穆仍然秉持大毅力,要做通人之学,他的史著也是立意高远,时间横跨古今,于政治、学术思想、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无不涉猎。他强调:“中国学问主通不主专,故中国学术界贵通人,不贵专家。苟其专在一门上,则其地位即若次一等。”为什么钱穆要与学术专业化的趋向相背离,非要强调通学呢?他的解释是由于史学并不能独立成为史学,其他学问也是一样,都不能独立自成一套,学问与学问之间交叉互补才是常态。而西方发展出来了分科之学,由于划分的过于专业化,从而导致了三个弊端:“一则各自分道扬镳,把实际人生勉强地划开了。如研究经济的可不问政治,研究文学的可不问历史等。第二、各别的研寻,尽量推衍引申,在各自的系统上好像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但到底则每一项学问,其本身之系统愈完密,其脱离人生现实亦将愈显著。”钱穆还从中国文化的特点出发来强调“通史”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和合”,西方则是重“分别”,因此这也决定了中国学术的特点是重视“会通”,大儒的气象就是博通古今、贯穿经史。梁启超在世纪之初曾经撰文提倡建立“新史学”,引发了学者对“新史学”理论的探讨。钱穆在悼念好友张荫麟时,曾经系统总结了他认为和主张的“新史学”者所要具备的几个特质:首先要对国家和社会存有使命感和关怀;其次要能鉴往知来,不拘泥于“世事现实”;再次,必须对“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项”及各学科的知识有相当之了解;最后,必须具备哲学的头脑,能够将孤立存在的“时空诸事”融会贯通,归纳总结出结论和规律。钱穆的以上观点,实际上是在要求作为史学家,应该要具备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并兼具博闻强识、好学深思的能力,实际上,钱穆也正是这样的史学家。
钱穆在做学问的过程中也是按照“贵通不贵专”的标准要求自己的,在写作《先秦诸子系年》时,他曾在自序里指出此前考证诸子年世的毛病之一就在于不能“通贯”。他说:“各治一家,未能通贯……未能通贯,故治墨者不能通于孟,治孟者不能通于荀。自为起迄,差若可据,比而观之,乖戾自见。”因此,为了达到“通人”之境,钱穆博览全书,对于经史子集都有深入的研究,他的侄子钱伟长后来回忆和钱穆相处时候的情景,称钱穆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并且传授给钱伟长大量的文史知识,令其受益匪浅。作为著名的教育家,钱穆先生的“通”也体现在他的教学当中,有学生回忆钱穆曾开过的课程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诗经》,道家的《庄子》,在历史课程上,他曾主讲过中国通史、秦汉历史、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经济史等,他的这种通博是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难以企及的。在著作方面,他的《国史大纲》是通史作品中的佼佼者,此书两大特色最为人们所称道,其一是对民族国家存亡及文化命脉存续的忧惧与关怀,极大提振了抗战时期军民的民族意识和抗争精神。其二就是该书极为通博,包含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内容,而且该书是在颠沛流离中写成,随身并无大量史料可资查证,更多凭借其多年的读书积累,更显出钱穆先生掌握知识和材料之渊博、扎实。(www.daowen.com)
再次,钱穆对中国的历史观察全面深入、高屋建瓴。中国历史渊远流长,历代留下了大量庞杂的史料,他是如何从众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记载中求得历史的“精髓”呢?这和钱穆通“变”的历史眼光有着密切关系。钱穆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中“变”量进行考察,所谓“变”就是指某一因素或现象,在前一历史阶段并没有,或者是前一阶段有此因素、现象,但是到另一历史阶段发生了较大变异,前后迥异。“凡某一时代之状态,有与其先后时代突然不同,此即所由划分一时代之特性。从两状态之相异,即两个特性之衔接,而划分为两时代。从两时代之划分,而看出历史之变。从变之倾向,而看出其整个文化之动态。从其动态之畅遂与夭淤,而衡论其文化之为进退。”因此,治史贵能知“变”,在某一历史时段,政治制度上发生了重要变革,就应着眼于政治制度方面,而另一时期,学术思想发生巨变,如佛教的传入等,就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学术方面。又如晚明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就应该将视野投放到经济上去。这样,在治史的过程中就把握事物变化发展的主要矛盾,也更有助于发现历史规律。在注意“变”的同时,钱穆也提醒人们不能忽视“常”,历史虽然不能再现,但是具有某些共同本质的事情会不断地在历史中上演,即我们常惊叹的“历史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钱穆认为常与变的辩证关系是:“变完成这个常,常亦是来完成这个变。没有变,就不得常。没有常,也不得变。任何一个文化传统里都该有常有变。变只是在常的中间变。常呢?拿这许多变合起来,就出一个常。”这也就是说,历史的殊性构成了历史的共性,而历史的共性也体现在历史的殊性当中,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互相依存的。这其实也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最后,钱穆强调要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上进行历史研究。如前所述,“古今中西”的问题是近代学人萦绕在心的时代问题,钱穆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中西”问题化约为“古今”问题。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明显落后于西方,仁人志士希望向西方学习,但是中国又是一个尊重历史和传统的国家,有着牢固捍卫传统的观念,因此,西方文化在中国受到了顽强的抵制。为了让中国人可以安心接受西方文化,而且在心理上摆脱“以夷变夏”的不适心理,一些学者就主张淡化“中西”差异问题,将之归结为“古今”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冯友兰先生的观点,他曾经说:“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冯友兰的这个思路是将世界看成一个整体的历史,有古代、近代和现代分别,而无地方性的差别。按照冯友兰先生的思路,人类由于受地域和生产生活空间的限制,产生了不同形态的文明,但总体上来看,不同形态的文明中很多基本内容是相通的,也都是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而且随着社会交往的扩大化,人类文明的趋同化也在初现端倪。
钱穆不接受将“中西”问题化约为“古今”问题的看法,他认为按照冯友兰等人的看法,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就被泯灭了,中西之间的差异绝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前现代和现代的差别。钱穆治史有一以贯之的理念,那就是探求中国历史传统及其特殊性,这是中华民族和其他民族之根本区别所在,所以他在不同的作品中都多次强调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在《国史大纲》中就曾指出西方文明是在多国并存、互相争斗中发展出来,而中华文明则是各个地方紧紧团结在中央周围,以道德、伦理等文化方式互相团结协作。正是两种不同环境孕育出来的文明,就导致了西方文明图强进取的特点,中国文明则是谋求和平稳定的特点。因此,钱穆主张研究中国要从本国的历史文化出发,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要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这种温情在他的著作中随处可以感知,比如他反对用西方民主—专制二元对立的话语来定义中国的政治制度,他强调中国的科举等制度能够保证平民的参政权,帝王、贵族、军人和富人都不能垄断国家权力,他将之称之为“东方式民主”。对于钱穆的此种观点,当然是见仁见智,但钱穆并非顽固的文化本位主义者,对于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他是有所涉猎的,对其中有益的部分他也是能够借鉴包容的。钱穆的民族本位文化论调,近年来有不少人予以响应,特别是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以及对传统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精神的延续性,希望传统文化成为滋养国人精神和建构话语体系的重要源泉。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