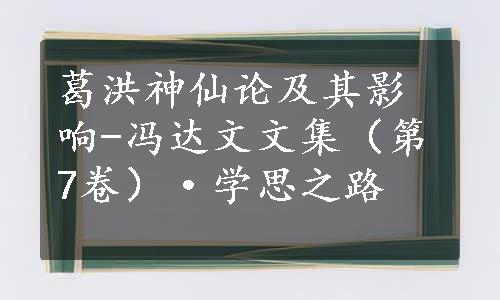
葛洪以前的道教,主要讲求以符箓、咒语为人们祛祸祈福,带有巫术的色彩。葛洪著《抱朴子·内篇》的意义在于:吸纳了两汉流行的元气本源论论证修炼成仙的可行性,从而为道教神仙论提供了一种自然哲学的基础,并使之获得某种经验科学的意味。
葛洪称:“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抱朴子·内篇·至理》)。葛洪的这一观念即是两汉元气本源论的基本观念:天地万物以至人类,都由一气化生,气是宇宙的最终本源。
两汉元气本源论不仅认为天地万物都由一气化生,而且,天地万物的性质、功能也由禀受的气的多少、种类所决定。葛洪说,“(人与物)受气各有多少,多者其尽迟,少者其竭速”。(《抱朴子·内篇·极言》)又说:“彼虽年老而受气本多,受气本多则伤损薄,伤损薄则易养……此虽年少而受气本少,受气本少则伤深,伤深则难救”(《抱朴子·内篇·极言》)。这也是认为,人、物的生死寿夭取决于禀受元气的状况。
在东汉,杰出的思想家王充用元气本源论说明万物的成因所强调的是:万物一旦禀受气的多少、种类成性定形之后,便再也不可能有任何变更。这是自然命定论。这种观念一方面否弃人的任何主观努力,另一方面也避免走向神学。葛洪接受元气本源论,则把这种理论引向了与王充相反的方向。
在葛洪看来,既然天地万物都由同一元气化生,其性质、功能也由所禀受的元气的状况所决定,禀受状况相同的事物便应该具有同类性,而且就万物最终都由一气所化的意义上说万物都是相通的。万物同类而相通的特性确认万物是可以互相转易的。葛洪说:“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钧末乖,未可一也。”(《抱朴子·内篇·论仙》)比如:“泥壤,易消者也,而陶之为瓦,则与二仪齐其久焉;柞楢,速朽者也,而燔之为炭,则可亿载而不败焉。”(《抱朴子·内篇·至理》)葛洪以上观点都是确认万物的可变性。既然万物的性状是可变的,那么人用自己创造性的努力使万物依照有利于人的方向变易便完全是可能的。“越人救虢太子于既殒,胡医活绝气之苏武,淳于能解颅以理脑,元化能刳腹以瀚胃,文挚愆期以瘳危困,仲景穿胸以纳赤饼……”(《抱朴子·内篇·至理》)这即是人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改变事物性状的有力证据。我们看到,在肯定万物的可变性与肯定人的主观努力的这点上,葛洪思想极具可取性。葛洪说:“天地之间,无外之大,其中殊奇,岂遽有限?”(《抱朴子·内篇·论仙》)又自称:“俗人多讥余好攻异端,谓予为趣欲强通天下之不可通者。”(《抱朴子·内篇·黄白》)葛洪这种求奇好异的致思倾向甚至颇具科学家的气质。
葛洪以这种思路思考人生问题。在他看来,人既由元气化生,人的生死寿夭一决于禀气的状况,那么,人如果发挥自己的主动精神,把自己已经禀得的气保养好而不耗散,不是就可以改变必然要走向老死的历程而获得永生吗?葛洪说:“故仙经曰:养生以不伤为本,此要言也。”(《抱朴子·内篇·极言》)这便是强调保气养生的至要性。
但事实上人是不能不损耗元气的。因此,养生问题就变成为:人有没有可能把每天损耗的元气补回来,并且使之稳固下来?葛洪依经验确认,有这种可能性。他说:“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抱朴子·内篇·金丹》)在日常经验的范围内,我们已知食用粗浊之气化生的五谷可以补充人体损耗的元气,何况是上品的药材?有没有这种药材呢?葛洪认为有,这种药材就是金丹。“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抱朴子·内篇·金丹》)。在葛洪看来,“金丹”永不变质,证明它是气中的精粹,因此,服用金丹,必定可以固精保气,令人不老不死。人在服用金丹之后,不再需要食用粗沉的五谷,人不仅可以不老不死,而且可以回复到本源气那种绝对纯和的状态,获得气那种千变万化的功能。人由此便成为神仙。(www.daowen.com)
这就是葛洪由元气本源论引申出的神仙论。在葛洪确认有神仙的存在与人有修炼成仙的可能性时,我们看到,葛洪走向了神学。
葛洪确认神仙的存在与人修炼成仙的可能性而走向神学,很难说是葛洪个人的思想局限。事实上,在两汉期间,元气论把气看作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赋予气无所不生、无所不支配的无限功能时,气即已被神化。葛洪只不过是把气的这种神奇性作了进一步的引申与发挥而已。葛洪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善行气者,内以养身,外以却恶,然百姓日用而不知焉。吴越有禁咒之法,甚有明验,多炁耳。知之者可以入大疫之中,与病人同床而己不染。又以群从行数十人,皆使无所畏,此是炁可以禳天灾也。或有邪魅山精,侵犯人家,以瓦石掷人,以火烧人屋舍。或形见往来,或但闻其声音、言语,而善禁者以炁禁之,皆即绝,此是炁可以禁鬼神也。”(《抱朴子·内篇·至理》)这里,葛洪已把气直接认定为神气。气为神气,由气化生的天地万物无疑也要被神化。故葛洪又说:“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及人身中,亦有魂魄;况天地为物之至大者,于理当有精神,有精神则宜赏善而罚恶,但其体大而网疏,不必机发而响应耳。”(《抱朴子·内篇·微旨》)天地万物均有精神,整个世界便成为神的世界。
在葛洪那里,“道”原本是使人如何修炼成仙的方法。但从道教徒的立场上说,如何修炼成仙的方法实具有更根本的意义。所以,葛洪又称,“凡言道者,上自二仪,下逮万物,莫不由之”(《抱朴子·内篇·明本》),“其唯玄道,可与为永。不知玄道者,虽顾眄为生杀之神器,唇吻为兴亡之关键……彼假借而非真,故物往若有遗也”(《抱朴子·内篇·畅玄》)。道由此也被神化了。道不再是一种“学”而是一种“教”。
葛洪就是这样借两汉元气本源论为道教神仙论奠定理论基础并走向宗教神学的。葛洪在岭南从事道教的理论研究与炼丹术、医术的实践探索先后达18年,对岭南道教的发展自有巨大影响。罗浮山从此成为道教的一个重要基地。
葛洪借外物(金丹)求存精固体的神仙术,在道教中称外丹术。罗浮山不仅因葛洪而成为外丹术的重要发源地,而且还因苏元朗而成为内丹术——通过提炼人身固有的精、气、神以成仙——的初发地。苏元朗曾学道于茅山,隋朝开皇年间来居罗浮山青霞谷,号青霞子。弟子从游者闻朱真人(传说中的罗浮山早期隐者)服灵芝得仙,都叹灵芝难寻。苏元朗笑道“灵芝在汝八景中,盍向黄房求诸。谚云:天地之先,无根灵草,一意制度,产成至宝。此之谓也。”于是著《旨道篇》论说之,自此道徒始知有内丹一术。[3]依苏元朗的观点,炼丹关键不在向外寻求丹砂,而在提炼个人内在的精气神。故谓“内丹”。内丹术于宋元以后大盛。道教内外丹的理论与炼治的实践都与罗浮山密切相关。可见岭南在中国道教文化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