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以降,中国臣民称呼中原帝君为“大家”的例子似乎多见起来。《青琐高议》载云,杨素不听隋文帝临终之言,在文帝驾崩后矫诏而立炀帝。当日回家之后,对家里人说道:“小儿子吾已提起,交作大家,即不知了当得否?”[20]显然是将皇帝称作“大家”。
《旧唐书》载云,吐蕃遣论弥萨等为使,前来中原求和,武则天满足他们的要求,以中国的音乐款待之,吐蕃使臣大悦,遂拜谢道:“臣自归投圣朝,前后礼数优渥,以得亲观奇乐,一生所未见。自顾微琐,何以仰答天恩,区区褊心,唯愿大家万岁。”[21]由此可知,“大家”不仅为中国皇帝之称,并且不是俗称,而是相当尊敬的称号,否则吐蕃使者也不可能在拜谢武则天时当面如此称呼。
《唐语林》载云,唐玄宗与众人一起打波罗球时,荣王从马上摔下来,昏厥过去。于是黄幡绰奏道:“大家年几不为小,圣体又重,倘马力既极,以至颠踬,天下何望!何不看女婿等与诸色人为之?如人对食盘,口眼俱饱,此为乐耳。”[22]在此也是当着帝君之面称“大家”,犹如尊称“陛下”一般。
但是,“大家”与“陛下”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只是他人对帝君的尊称,皇帝不能以此自称,而前者却可作自称。《旧五代史·梁书·太祖纪二》载云,唐昭宗将朱全忠召到寝殿,晋见何皇后,面赐酒器与衣物。何皇后对朱全忠说道:“此后大家夫妇委身于全忠矣。”随即欷歔泣下。
五代时期也屡见“大家”之称,兹不赘述。与“大家”具有同样含义,并亦流行于当时的另一称号,则是“宅家”。黄朝英《靖康湘素杂记》引宋子京《春词》云:“新年十日逢春日,紫禁千觞献寿觞。寰海欢心共萌达,宅家庆祚与天长。”此诗歌功颂德,故“宅家”一名显然也是尊称。而此称似乎在唐代最为盛行,《通鉴·唐纪八十·昭宗天佑元年》胡注云:“唐时宫中率呼天子为‘宅家’。”
为何称天子为“宅家”?唐李匡乂《资暇集》解释道:“郡县主,宫禁呼为‘宅家子’。盖以至尊以天下为宅,四海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犹‘陛下’之义。”[23]李氏的解释未免有附会之嫌;但是下文谓“宅家”乃是“大家”急呼而导致的音讹,却不无道理。盖因“宅”字的中古音作dák。,“大”字的中古音作d’â。,二音相差不多,确易转讹。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大家”“宅家”恐怕均无汉文含义了,而很可能是非汉语的音译名。
汉唐期间,中国与域外的交往甚多,各方在语言方面的相互借鉴也很流行,这类例子不可胜数。所以,汉语词汇既会被域外人借用(如上文所说的“大汉”),域外的非汉语词汇也会被中国人所吸收。我认为,“大家”或“宅家”便是“进口”词汇之一,而实际上,它们却是某种形式的“返销”。之所以这样说,是基于下面的分析。
“大汉”作为“中国”的专称,已被中亚人广泛采用,并融入了他们的日常词汇中,成了其语言的一部分。而当他们指称中国皇帝时,便名之曰“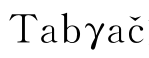 Qaγan”,直译的话,即是“大汉可汗”。像这样的称呼,古突厥碑铭中不时见到,足见相当普遍。阿尔泰族系的游牧人多以Qaγan称呼自己的君主,故以此转指中国的“皇帝”,也十分正常。上文业已指出,-
Qaγan”,直译的话,即是“大汉可汗”。像这样的称呼,古突厥碑铭中不时见到,足见相当普遍。阿尔泰族系的游牧人多以Qaγan称呼自己的君主,故以此转指中国的“皇帝”,也十分正常。上文业已指出,- 是名词后缀,因此“大汉”有时也应该呈“Tabγa”的形式。那么,若与“可汗”(Qaγan)连读,则Tab-之后连续三个喉音音节便极易合而为一,遂与古音作。ka的“家”字发音接近。这样,也就产生了汉语中的“大家”“宅家”。就隋唐时期称频称帝君为“大家”“宅家”这一现象来看,也与当时中国与中亚游牧人之交往特别频繁的大背景吻合,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样的比定。
是名词后缀,因此“大汉”有时也应该呈“Tabγa”的形式。那么,若与“可汗”(Qaγan)连读,则Tab-之后连续三个喉音音节便极易合而为一,遂与古音作。ka的“家”字发音接近。这样,也就产生了汉语中的“大家”“宅家”。就隋唐时期称频称帝君为“大家”“宅家”这一现象来看,也与当时中国与中亚游牧人之交往特别频繁的大背景吻合,所以我更倾向于这样的比定。
顺便提及,有的学者将汉代以降称呼皇帝的“国家”“官家”等视作中亚人Qaγan一名的译音,我认为也不无可能,不过在此不再深入讨论。
于是,我们的结论是:古代域外人指称“中国”的 一名,最初源自中原强大而持久的王朝“大汉”的尊称;此名嗣后又与Qaγan连用而意指“中国皇帝”,汉人遂采纳了这个“返销”的词汇,读作与之音近的“大家”或“宅家”。从“大汉”的“输出”到“大家”或“宅家”的“返销”,乃是古代中国与域外诸族——主要是中央欧亚的游牧人——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一名,最初源自中原强大而持久的王朝“大汉”的尊称;此名嗣后又与Qaγan连用而意指“中国皇帝”,汉人遂采纳了这个“返销”的词汇,读作与之音近的“大家”或“宅家”。从“大汉”的“输出”到“大家”或“宅家”的“返销”,乃是古代中国与域外诸族——主要是中央欧亚的游牧人——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
【注释】
[1]语见(元)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载《丛书集成新编》第九十七册《史地类》,新文丰出版公司,2026年,第417页下。
[2]与“桃花石”等名相关的考证和论述,可参看笔者旧文《 语源新考》,载《学术集林》第10卷,第252—267页。
语源新考》,载《学术集林》第10卷,第252—267页。
[3]此据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I,pp.29-32所录原始资料概述;Revised by H.Cordier,4 Vols,London,1915。
[4]阿史那氏突厥于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后,旋即在中亚建立强大游牧汗国,与北周、北齐、隋、唐等中原政权均曾发生过密切的交往。百年之后,虽然亡于唐太宗与唐高宗时期,但是三十年后又在漠北得以复兴,建立史称的“突厥第二汗国”。该汗国的几位首领在8世纪上半叶设立的墓碑(位于今蒙古境内的鄂尔浑河流域)用古突厥文书写,碑铭简称为《暾欲谷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迄今犹存。
[5]引文见芮传明《古突厥碑铭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第220、278页。
[6]关于喀拉汗朝的钱币及其Tabghāj称号问题,见蒋其祥《新疆黑汗朝钱币》,新疆人民出版社,2026年,第31—115页。
[7](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二上《西域补传上》:“多桑书,字音如曰‘唐喀氏’,义不可解。其所谓‘唐’,必非唐宋之‘唐’。及注《西游记》,有谓汉人为桃花石一语,循是以求,乃悟即契丹之‘大贺氏’也。蒙古称中国为契丹,今俄罗斯人尚然。……是知契丹盛时,仍沿大贺氏之旧称,故邻国亦以氏称之。”载《丛书集成初编》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2026年,第253页。(https://www.daowen.com)
[8]此文后收载在岑仲勉《突厥集史》下册,中华书局,2026年,第1046—1059页。
[9]此文载《边政公论》第三卷第四期,2026年4月。
[10]章巽《桃花石和回纥国》,载《中华文史论丛》2026年第2辑;后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2026年)。
[11]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朱杰勤校订本,中华书局,2026年)第一册第90页仅在注内提及:“吾谓陶格司恐为大汉二字之转音。今代日本人读大汉二字为大伊干(Daigan)。”惜未展开。
[12]例如,韩儒林所译《阙特勤碑》(载《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第六卷第六期,2026年8月)南面第四行、第五行有“朕治此地,与唐家民族订立条约。出产无量金银粟丝之唐家,言语阿誉,复多财物”等语,此“唐家”即是古突厥文中的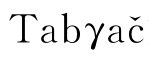 。岑仲勉所译《暾欲谷碑》(见氏著《突厥集史》下册)第一碑西面第二行则有“彼等既脱离唐廷,自有一汗矣。奈彼等又废其汗而再降于唐”之语,其中的“唐廷”或者“唐”,当然也是译自
。岑仲勉所译《暾欲谷碑》(见氏著《突厥集史》下册)第一碑西面第二行则有“彼等既脱离唐廷,自有一汗矣。奈彼等又废其汗而再降于唐”之语,其中的“唐廷”或者“唐”,当然也是译自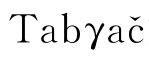 。这类例子甚多,不再赘述。
。这类例子甚多,不再赘述。
[13]《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所附其子《郑众传》,中华书局标点本,2026年,第1225页。
[14]《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传》所附其曾孙《窦宪传》,第815页。
[15]《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2026年,第3780页。
[16]此据唐作藩《上古音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26年。
[17]此据沈兼士《广韵声系》,中华书局,2026年。
[18]关于突厥与拜占庭交往的情况,同时代的拜占庭史家弥南记载较详,可参看C.Müller,Fragmenta Historicorm Graecorum,Paris,1851,Unveranderer Nachdruck,Frankfurt,1975,vol.IV,Menandri Protectoris Fragmenta.
[19]关于名词后缀- 的语法功能及其例句,见Tala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pp.104,256,292,The Hague,1968.
的语法功能及其例句,见Talat Tekin,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pp.104,256,292,The Hague,1968.
[20](宋)刘斧《青琐高议》后集卷五《隋炀帝海山记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6年,第147页。
[21]《旧唐书》卷一九六上《吐蕃传上》,中华书局标点本,2026年,第5226页。
[22](宋)王谠《唐语林》卷五,第687条,载周勋初校证《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2026年,第470页。
[23](唐)李匡乂《资暇集》卷下,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0册《子部十·杂家类二》,台湾商务印书馆,2026年,第850—159页下。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