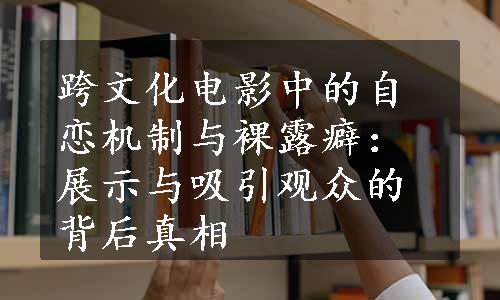
自恋是一种精神症候,它表面上是人类个体过分自信、自满乃至陶醉迷恋的心理表现。其内在的原因,按照经典精神分析理论的解释,则是一种类似“自恋性人格障碍”的病状:患者无法把自己本能的心理力量投注到外界的某一客体上,该力量滞留在内部,便形成了自恋。
就是说它看似辉煌,内在却充满困惑。中国成语“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可以形象地描绘其真实的“表里”矛盾。这种自恋,还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我们在全球化时代几乎每个人面临的资本文化的影响(甚至洗礼)之后果有关。换句话说,像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著作中所说:在文化和社会断裂日益加深的语境里,我们离言行一致、表里合一的生活愈行愈远,从而使得自己的人格和伦理在矛盾中危机重重。
《鸟人》讲述了这样一个“表里危机”的故事:早已年过半百的里根·汤姆森曾经是一名风光一时的好莱坞电影明星,他所塑造的超级英雄飞鸟侠家喻户晓。而今荣耀早已成昨日黄花,不甘寂寞的里根转战百老汇,试图通过改编雷蒙德·卡佛的《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重新赢得关注与尊重。无奈现实总和理想有太大的差距,剧组经费吃紧,糟糕的男主角被灯砸破头,刚从戒毒所出来的女儿萨米行为放荡不羁,对之不利的戏剧评论员蓄势待发,此外请来救场的好莱坞当红小生麦克·珊农乖戾张扬,屡屡染指篡改里根殚精竭虑打造的戏剧。在混乱的鼓点中,命运多舛的戏剧迎来了公演的重要时刻。
将《鸟人》归入自恋的精神范畴,是因为作为由当今的好莱坞电影人制作团队生产出来的一个产品,《鸟人》其主要人物里根·汤姆森和剧中的剧组人员、评论家都是戏剧人、电影人,也就是说电影所反映的很大程度上就是自己行业内部的故事。因此其题材具有十足的自我指涉和自我映射性,其背后的驱动机制就是古希腊的自恋(narcissism)机制。
这种自恋机制还反映在近期频频出现的跨文化电影之主题范式上。里根·汤姆森的烦恼与《迷失东京》中作为曾经辉煌一时的电影影星的鲍勃·哈里斯的烦恼、困惑一样,多来自一种资本主义式“自我成功”(所谓美国梦)导致的自寻烦恼式的谵妄上。前者讲述了鲍勃·哈里斯在他者的文化中无所事事、失落异常,以及和同病相怜的夏洛特、女演员凯利的故事。两个人以心有灵犀开始,到止于礼节结尾,散发淡淡的忧伤。不过,对于电影的主题,在随后导演科波拉遭到批评界的批判中也有所“互文”。诸如布拉内特撰文《索菲亚·科波拉过于狡猾的‹迷失东京›》(见《斩首好莱坞——索菲亚·科波拉作为女性作者》)等谈到的种族主义、偏颇的女性视角等。其为人诟病的根本原因是人物的自恋和电影生产本身的过于自恋(在另外一种氛围里,完全可以把这种自恋和自寻烦恼的疾病称为“精神病”,无怪乎在电影中里根的女友对他最后“你屁眼一个”进行嘲讽,女儿也对他进行了一通长篇批判——主要是针对他头脑中的英雄主义之“不合时宜”展开的嘲讽。这种观念差异也是代沟)。
在《鸟人》中,电影人自我指涉电影界再次应验。这种不经意的媚俗在中国导演顾长卫作品《微爱》中也有展现,而且《微爱》更加赤裸裸地展现了电影人的尴尬和卑微。通过喜剧式、浅程度式地揭示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等于也传递了一种揭秘性质、自我暴露、自我裸露的图像(行业外面的人看不见的图像)。这与裸露癖在心理机制上相通。(www.daowen.com)
在《鸟人》中,细心的观众只要仔细辨认,还可以通过剧中这个位于百老汇时代广场一侧(大约位于曼哈顿42—43街之间)的剧场,感受到这个被巨大的音乐剧和戏剧海报点缀出的戏剧王国的灵韵。比如,随着剧情展开,与这家剧院毗邻的,位于曼哈顿时代广场边的百老汇剧院2013—2014年度上演的音乐剧《妖姬长靴》《摩城唱片》甚至《狮子王》等的巨型招贴广告,都一一呈现。这可以说是客观展现场景,但背地里则是一贯的以噱头吸引观众和裸露癖的机制使然。
按照笔者的推测,《鸟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制胜法宝,并不在于这些自恋机制的运作本身对同样属于电影工业圈子的评委会们施加了“同情药丸”,而是在于,当这种自恋和裸露癖好与忧伤主题——资本主义的老话题结合起来的时候,电影产生的迷影(cinephilia)效果,即苏珊·桑格塔所言的“电影所激发的那种独树一帜的爱恋情痴”就发挥出来,而这就是当代电影的魅力所在。同样的“梦想、乌托邦不可能实现”之表现,在《革命之路》(人对于远方和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具有天然的热情和越得不到越珍贵的情绪,是普遍性的,受到人类基因的支撑)中就成了独特的“迷影”。换了其他导演制作,也许类似《鸟人》《迷失东京》的事业受挫,或者中年困惑的题材(好莱坞这类题材的电影汗牛充栋的数量),根本不会有类似的迷影效果呈现。
《鸟人》中,有两个超现实的表现,类似安托南·阿尔托理论中再现和表现之间深刻的混乱,即故事中他扮演的鸟人的一个叠影(一个复制版)和鸟人自己在影片叙述时空中的飞翔。这些飞翔,被处理成充满诗意和想象空间的视觉奇观,魅力无穷。穿行——这种逻辑导致最后他梦想鸟人飞翔的画面展示上(之所以这样描述是因为这个影像本身呈现的意义是多样和歧义、含混的),是自杀或者是终于回归到飞翔的内在本性,不得而知(德勒兹就在《千高原》中揭示人的种类划分的复杂性,一个女人和男人的差别可能大于一个人和一只鸟的差异等)。这种逻辑也导致了德波所言的资本主义“景观”——媒体(暗指纽约时报的戏剧批评版面)之权威性——具有生杀予夺大权,这也是景观异化的一种佐证。在无实物表演(假设)和现实(由曼哈顿的建筑物质感提供)之间穿行。
毋庸置疑,《鸟人》围绕这个不成立的大叙事冲突背景,营造节奏的本领还是非常过硬的,细节栩栩如生。自恋导致的疾病及其后果是电影无关观众痛痒和实际生活的复杂及大千世界的广阔性。它以封闭式的、类似一个三一律戏剧(所有的剧情都发生在试演的一个时间当口,所有的地点都在这家旧兮兮的百老汇剧院里,所有的人物和故事都是高度统一的)的制作模式,为电影的审美制造了又一个好莱坞景观和幻觉。它是在电影界几乎没有打破第四堵墙的一次戏剧操练,也是跨界,更是电影作为一种资本主义(性质)景观本身的性质所赋予的。在这种景观中,看和被看都成了欲望。
这种自恋,与希区柯克式的自恋不同,除了题材的自我指涉,顾长卫在《微爱》中还扮演了一个失聪的厨师,让自己在银幕上呈现。作为韩寒的朋友(以及可能的拍摄电影的顾问)在韩寒导演的《后会无期》中,中国新生代导演贾樟柯也作为敲诈团伙成员出现。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