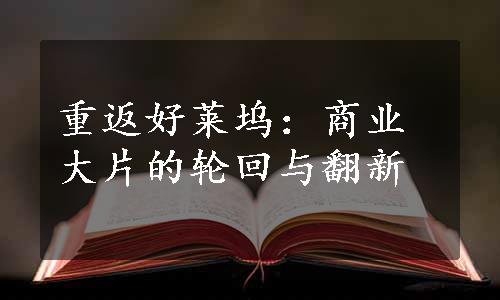
好莱坞最近的商业大片,似乎已经如学者杰弗里·A.布朗所盖棺论定的那样,充满了“霸权性男性气质”。[40]如果不做深入分析,我们真的会以为好莱坞的电影作坊只是生产陈旧事物的地方。在2016年的《电影与录像季刊》杂志上,杰弗里·A.布朗发表的这篇重要的论文《超级英雄电影的戏仿及霸权性男性气质》,将我们的视点转向了一个比较真实的好莱坞。那就是,如果有一个词汇可以概括好莱坞今天电影制作的景观,那将不是“英雄”“高概念”“大投资”,而将是——依我之见——“戏仿”一词。原因正如作者所罗列的当今好莱坞之主流,除了传统的以英雄人物为主线的商业大片外,英雄主义的主题依然拥有不少观众,而在这种自古希腊就开始流行,继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沉浮,有时候沉入水底,不再被推崇,有时候又出现柳暗花明的状态,正说明电影和文学叙事一样,处在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轮回的命相中。除此之外,杰弗里·A.布朗非常敏锐地分析了美国当今电影的制作趋势:戏仿。他罗列的(那些寄生于前期超级英雄主角电影基础的)戏仿电影有如下的种类:
1.家庭友善类(如《超人高校》);
2.动画修正类(如《超人总动员》);
3.浪漫喜剧类(如《我的超级前女友》);
4.现实主义修正电影(如《全民超人汉考克》);
5.由超级英雄电影改编而来的真人秀节目(《如超人前传》)……
总之,杰弗里·A.布朗归纳这种戏仿现象的成因乃是认知意义上的,他的观点十分明确:“一旦观众对某个电影类型的形式以及固有风格熟悉之后,对这个类型电影的戏仿或恶搞就是时间的问题了。”[41]
可见,好莱坞电影在树立其英雄主义色彩电影的同时,一种颠覆固有类型、戏仿电影程式的做法也比较常见。这种原型和戏仿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正—反”或者“正—正”那么单调,而是类似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所秉承的“杂糅”概念,意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www.daowen.com)
这样,当我们评价好莱坞电影的制作趋势时,轮回(守旧思维)或者戏仿和衍生的(杂糅模仿和创新思维)的悖谬将持续良久。我们需要时间等待尘埃落定。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的网生代电影。自从2014年被专家定义为“网生代电影元年”之后,至今“年多的实践,对它的研讨层出不穷。得益于中国当代电影理论视野的拓展和对西方学术成就的译介之贡献,以及事实上的中外学者跨文化交流的日渐频繁,目前所涌现的网生代电影之研究中,借鉴西方学术成果(之论点)的论述不计其数。比如雷蒙·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论点采用、挪用和借鉴不计其数。而针对麦茨关于电影史三个机器的运作之综合,以及其“这三个机器(机制)之间如何运作?电影各个机器与社会的互动性如何之研究”等问题也开始涌现。这些探讨“网生代”电影的概念和生产方式的学术研究,笔者认为以《当代电影》杂志发表的网生代论文专辑(2014)[42]最有代表性。因为该期刊物发表了尹鸿、朱辉龙、王旭东、朱晓敏、陈旭光等网生代电影学者的一些定义性论点和阐述,也为“网生代电影导演”和“网生代电影”这两个概念提供了迄今比较权威的解释,并且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认同:“网生代电影”是新生之物,它使电影在内容、市场、传播、观影模式、评论等方面发生变革;它也是生产方式的分水岭,它在集资、营销、消费等生产流程上都发生了改变。[43]对于“网生代导演”的特征,王旭东就总结为:“(网生代电影)具有鲜明的标签,他们反映虚拟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拥有碎片化表达和渐进式的文化消费”,以及“他们往往具有依赖互联网生存的特点,可能从互联网起家(或小说或微电影)转而执导大银幕电影;借助互联网聚合的大量粉丝提升票房;擅长利用互联网营销,制造话题。”[44]
在上述观点的引领下,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当今新出现的电影现象或者电影美学,不能将之理解为一种孤立的文化现象,而是应该解读为一种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互动现象。正如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和互动符号理论家欧文·戈夫曼早就揭示了一种基于互动的人类社会性戏剧(表演)天性和运作机制。语言学家约翰·朗肖·奥斯丁更是发明了语言行为理论,提出了“以言行事”的新颖观念。意为语言具有自身的表演性。我们也可以借助戈夫曼的理论、克里斯蒂安·麦茨的“信念结构”理论(分为初次信念和次级信念)或者实验电影导演安迪·沃霍尔的装置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电影作为一种以物性呈现的特殊产品,也具有表演性”的综合性观点,在这种表演性的机制里,与电影相关的各个环节都具有生产意义。比如,在互动层面,政策、法律层面的因素也加入电影意义生产的核心,这对如何理解电影颇有裨益。我们可以从政策(策略)法规、生产、消费和传播的四个层面来剖析电影的内容(社会)意义。
因此,电影作为一种社会实践的议题与电影本体和现实之间的亲缘关系有关,也与电影历史上有关电影社会学、电影认知学等学科的发展和演绎有关。如今电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审美对象,而逐渐变成一种观众了解社会、参与社会的一种社会性实践。迄今为止的电影也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电影不仅仅是银幕依附物,也不单纯是一个叙事媒介。
归纳上述展开的分析,网生代电影的社会互动包含了互相杂糅甚至对立的三方面内容:第一,网生代电影生产中普遍有削弱叙事逻辑、降低文化视野的弱点,其对于社会真实内容的传递带有浮躁、肤浅的特征;第二,在消费的层面,越来越多的网生代电影吸引了城镇青年群体(集体)观影的热潮,让这些电影创造了一个讨论当下社会事件的公共空间,扮演了公共意识的认同推手,激发了社会和电影的互动;第三,屏媒时代影像的互动趋势,导致了沉浸、体验、超文本、非线性等诸多美学体验的流行,也导致了对意义生产系统的解构和对社会意识的逃逸。可见,网生代电影之于社会意识的建构,既是促进之物又是游牧和逃逸的媒介(某种程度上,逃逸正是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对它的培育和批评须同时进行。网生代电影其实代表了社会转型期的一些有趣现象,比如沉浸、体验、超文本、碎片、非线性、图像崇拜、恋物癖等诸多美学体验的流行,也导致了对意义生产系统的解构和对社会意识的逃逸。
如果我们超越“好莱坞/华莱坞”的二元模式,再引入宝莱坞和非洲电影,则又可以多一个探索问题的面相。我们暂且把差异放在一边,探索三者之间的叙事和人物、结构模式上的相似之处。我们惊奇地发现,近来这种相似性在增加,比如美国和南非合拍的“非洲电影”《卡推女王》、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和美国电影《百万美元宝贝》在其国别和反映故事背景的现代化程度上各不相同(分别是非洲、亚洲、美洲,呈现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差异),但这三部电影在人物设置、主题和题材上具有一种似曾相识的雷同感,而其叙事结构(情节编码)也基本走向了“体育类”的类型模式。其他关于这些电影的励志效果、治愈效果、亲情效果则是以次类型、次信码的方式——艾柯所言的附加编码(overcoding)方式被编码的。除了主要的信码,这些次要的信码也是可以轻易解码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