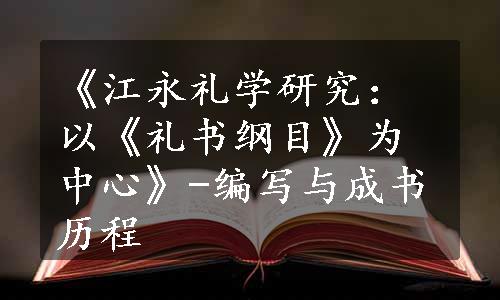
朱熹既是理學大家,也是禮學名家,他少時就傅,由楊由義親授司馬光《雜儀》,年輕時萌發考訂諸家祭禮的興味,成爲他禮學研究的起點。他曾自撰《家禮》,對删削有限而難以普及的司馬氏《書儀》進行增訂,在明清時風靡宇内。他晚年又主持編撰《儀禮經傳通解》,此書同樣在明清風靡。此外,留存於朱門弟子所輯纂的《語類》和《文集》中亦存很多有關考禮、編禮的内容。清代李光地曾以類纂集,分爲“總論”“冠昏”“喪”“祭”“雜儀”五目,成《朱子禮纂》五卷,於學禮者頗爲有功。朱子鍾情於編撰禮書,有着鮮明的時代背景。
朱子的禮書編撰是唐宋間禮下庶民運動的産物。衆所周知,禮以時爲大。由於今本《儀禮》主要是關於士禮,隨着社會文化的變遷,損益工作不得不進行。漢代叔孫通通過增删秦律制定漢禮,讓流氓出身的劉邦感受到作爲天子的威嚴。後漢曹褒也據叔孫通所制之禮損益,雜五經讖記之文,成天子及士庶人禮百五十篇,可惜不僅没能實行,還受到彈奏,漢禮遂不行[4]。魏晋南朝有關喪服的書籍特出,《隋書·經籍志》記載的136部1622卷禮學著述中,《儀禮》注釋的書籍幾乎闕如,全爲“喪服”替代。從隋唐開始,隨着國家的統一和對禮制的需求,大型禮書的編撰成爲可能,現存《大唐開元禮》即編於此時。同時,隋、唐以來科舉制度的實行,士人向上的流動性增加,門閥制度瓦解,士庶通禮等普及型禮書需求增加,“宋徽宗時頒定的《政和五禮新儀》,開始出現了《唐開元禮》中没有的士庶禮儀,即‘庶人冠儀’‘庶人婚儀’‘庶人喪儀’,成爲‘禮下庶人’的一大轉折。”[5]但士庶通禮受到佛道禮儀的浸染,禮書編撰回歸儒家傳統成爲一種普遍趨勢[6]。歐陽修、王安石偏向於以《周禮》爲中心重建禮制,司馬光、二程主張以《儀禮》爲主進行禮書編撰,後者的路徑被朱子用於禮書的編撰中,著成《家禮》《儀禮經傳通解》兩部劃時代作品。
同時,《儀禮》研究的衰落,竟至出現附會、杜撰風氣的盛行,促使朱熹决宗法《儀禮》,編撰禮書。《儀禮》在《三禮》中原本具有正經地位,但到了唐代修纂諸經正義,原本爲《儀禮》附庸的《禮記》成爲《五經正義》之一。此外,唐代科舉取士,以經書字數多少分大、中、小經,字數的多少與難易程度决定本經習讀的盛衰,九經中《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殆絶[7]。北宋神宗熙寧四年(1071)依王安石意見罷廢《儀禮》,致使《儀禮》研究遂歇,盛行附會和杜撰。朱熹曾批評陆佃解説禮時不以節文度數爲據而“先求其義”,失去了“古人所以講明其義者,蓋緣其儀皆在,其具并存”的基本要求,所求之義流於空疏[8]。當時禮學家林粟和朱熹進行過對《西銘》禮制問題的争論,林粟專研禮學,但不解宗子和嫡長子的關係,將其中“君者,吾父母宗子”理解錯位,造成君子“既爲父母,又降而爲子”,鬧出笑話[9]。劉敞在長安偶得周敦,其中刻云“弡中”,遂以爲周張仲之器。後又得一枚,刻云“弡伯”,遂以爲張伯。曰:“《詩》言‘張仲孝友’,則仲必有兄矣”,遂作銘述其事。後來趙明誠《金石録》辨之,云“弡”非“張”,乃某字也[10]。可見當時説禮無所據而杜撰者衆,主要原因在於王安石罷廢《儀禮》所致。朱子主張“孫爲人君,爲祖承重”,但缺少文獻證據,結果遍查《儀禮》疏未得,遂生感歎,“舊來有明經科,便有人去讀這般書,《注》《疏》都讀過。自王介甫新經出,廢明經學究科,人更不讀書。卒有禮文之變,更無人曉得,爲害不細。如今秀才,和那本經也有不看底。”[11]《儀禮》作爲正經,其研究的荒廢和附會、杜撰風氣的盛行,使朱熹感到憤恨。他在上書修禮書的札子中批評王安石,以爲:“熙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弃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虚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12]
朱子的禮書編撰有着現實需求。宋代的濮議事件,以及朱子在政治生活中論及禮制時所遭受的困境,使得他决心研究《儀禮》。濮议发生於北宋英宗時,是一場當朝文人士大夫深度捲入,包括學術争論和政治鬥争的議禮事件[13]。仁宗無嗣,生前指定後來的英宗繼嗣,但英宗繼承大統後,對於祭祀生父濮安懿王應該如何稱呼的問題,朝中以司马光爲代表主張尊稱“皇伯父”,欧陽修爲代表主張尊親稱“皇考”。這場争論凸顯了當時《儀禮》研究的缺失,這種缺失在朱熹自己的禮學實踐上體現得更加明顯。紹熙五年(1194)秋,光宗内禪,寧宗即位,冬十月,朱熹奏乞討論嫡孫承重之服[14],其主張儘管“法意甚明,而《禮經》無文”。他反思自己“講學不熟之咎”,未熟讀《儀禮》所致[15]。這一年朱熹上《祧廟議狀》,提出自己的祧廟方案設計。北宋王室在廟制問題的安排上混亂不堪,特别是孝宗死後,誰爲始祖,如何祧遷祖先牌位,如何安排廟室昭穆實行禘祫之禮,成爲一個涉及禮制和政治的敏感話題。孝宗祔廟重新引發了關於太廟之制的討論,在朝臣中間掀起了紛争。有宋以來争執不熄的禮制困境,讓後來朱熹在編撰禮書的過程中特别留意有關廟制、禘祫、郊社等問題[16]。現實中禮書編纂的需要,《儀禮》研究附會風氣的盛行,朱子自身禮制實踐遭受的困境,促使他决心宗法《儀禮》編撰禮書,最終編成《儀禮經傳通解》一書。
據白壽彝的考證,朱熹先後進行了五次較大的體系調整,才形成了今本《儀禮經傳通解》的體系和内容[17]。白氏稱朱熹的五次調整爲“五次設計”[18]。朱子對於本書的設計和編撰有過長時間縝密的思考,它凝聚着朱熹學術的結晶。(www.daowen.com)
本書編撰包括正文、注解以及參校,由弟子和朋友進行最初的編纂,朱子進行統籌。參編人員包括應仁仲、趙恭父、黄直卿、趙致道、吕子約、劉用之、劉履之、廖子晦、潘恭叔等,其中黄直卿就是黄榦,是朱熹的女婿和高弟。另外還有余正甫,他是當時的禮學名家,但編撰理念上和朱熹有分歧。余氏將《國語》放入禮書編撰中,引起朱熹的不滿。朱子最爲重視三禮的材料,三禮中又重《儀禮》,次《周禮》《禮記》,最後才是古書古籍[19]。一般認爲,《喪禮》和《祭禮》爲朱子囑托黄榦進行編撰,應被排除在《通解》體系之外,但白壽彝對朱熹去世前有關《通解》剩餘部分的編撰進行了推測,認爲《喪禮》《祭禮》在朱熹在世時已在進行編撰,死後成于黄榦之手,但當時編輯不限於黄榦一人。白氏考証朱子亦曾委托吕祖儉編撰《祭禮》,吕氏將《祭禮》放在《喪禮》前,但由於論事外貶身亡而止。此外,吴必大和李如圭也參與過《祭禮》的編撰。《喪禮》的編撰情况較《祭禮》更好,朱子在世時,《喪禮》的成熟度較《祭禮》高。《通解》在朱熹死後二十年具稿,最終《喪禮》沿襲者八篇,改定者兩篇,其變更較之《祭禮》還要小些[20]。朱熹指導了喪、祭二禮的編撰,設計了基本框架,準備了部分材料,給黄、楊的工作提供了指南。但如果没有黄榦、楊復的努力,朱子的設計永遠只是藍圖。黄榦在編定喪、祭禮中所設定的體例,被後來重訂朱熹此書的清代學者所推崇,楊復也在編纂祭禮時有着巨大的學術發現[21]。
朱熹慶元六年(1200)過世時,《通解》并未完成,在嘉定十年(1217)南康道院的刊刻本中,只有《家禮》《鄉禮》《學禮》《邦國禮》共三十七卷,《喪禮》和《祭禮》并未成型。在三十七卷中只有前二十三卷經過審訂,是爲《通解》,另十四卷未通過審訂者爲《集傳集注》。後來黄榦秉承朱熹的遺願繼續編《喪禮》和《祭禮》,在嘉定十三年(1220)《喪禮》完成後不久就過世了,剩下的《祭禮》由楊復繼續完成,這便是所謂《儀禮經傳通解續》,簡稱《續通解》。
《儀禮經傳通解》一書的編撰實際上由朱子發凡起例,由朱門弟子及友朋參加編撰,最後由朱熹筆削整理。從成書的最後情况來看,由朱熹所親定和認可的部分只有《通解》,剩下的《集傳集注》未來得及整理,黄榦、楊復所編《續通解》未能完全融入朱熹此書内聖外王的理學途徑。本質上,《儀禮經傳通解》是一部未成之作,這也導致了清代以來大批學者争相重訂此書,江永是其中之一。他認爲《通解》“前後體例亦頗不一,《王朝禮》編自衆手,節目闊疏且未入疏義,黄氏之書,《喪禮》固詳密,亦間於漏落,《祭禮》未及精專修改,較《喪禮》疏密不倫。信齋楊氏有《祭禮通解》,議論詳瞻,而編類亦有未精者”,最後他以“朱子爲宗,式法黄氏”,成《禮書綱目》一書,卒終朱子未竟之緒[22]。
《禮書綱目》作爲江永最大的禮學著述,是在朱子《通解》的基礎上增訂而成,意在回歸《周禮》吉、凶、軍、賓、嘉五禮體系,附益《通禮》《曲禮》及《樂》,總百單六篇,八十有五卷。《綱目》的編撰以朱子爲宗,確立以《儀禮》爲經,《禮記》爲傳的體系設計,在方法上又多有創新,主要以“統繁”和“補缺”爲原則,通過對《通解》的增删隱括,最終實現了禮書編撰者追求綱舉目張和禮樂合璧的夙願,在禮學編撰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但江永此書仍是一部未成之作,主要是對於“賈、孔諸家之疏,與後儒考正之説”的缺略[23],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主要在於個人精力的限制,也正是由於這一限制,使得本書的編撰在體系上更加完整,成爲朱子《通解》之後的又一禮學名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