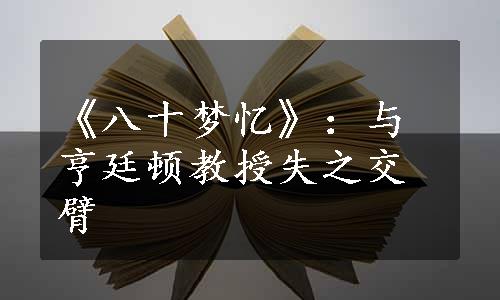
我当时拟订的访谈计划规模相当可观,想在哈佛访学期间与中国学这一块的主要教授都有所交流。连写《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亨廷顿教授,也约定了时间,并提前交给他一份详尽的访谈提纲。下面是《亨廷顿教授访谈提纲》的全文:
1.自从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发表以后,中国以及亚洲的知识界很少有不知道您的名字的。您的言论因此成为大家关注的目标。我在哈佛访学期间,听说您对该文的一些论点,已有所修正,不知是否真有其事?如果有,我想知道都是在哪些方面做了修正?
2.冷战结束之后,人们显然期待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但我以为,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秩序”,不仅发生了歧见,而且事实上遇到了困难。甚至,“世界新秩序”这个概念本身也变得模糊不清起来。请问,您是怎样看待“世界新秩序”这个概念的?或者您个人希望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新秩序”?可否就这个问题做一些分疏?
3.我在我创办的一本新刊物《世界汉学》的发刊寄语中,曾提出下面的观点:“如果冷战后文明的冲突愈益凸显之说无法得到广为认同的话,那么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变得更容易而是增加了新的难度,应是大多数学人都可以接受的事实。”这样讲,是因为当今世界普遍存在文化误读的现象。比如,在我看来,美国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您的看法呢?
4.您觉得现代文明建构的模式可以有多种形式吗?请谈谈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建构的关系。“亚洲价值”这个概念您怎样看?文化上的多元并立,在一个国家是如此,就世界而言,更是如此。那么文化上的这种“根性”,与现在颇为流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否隐含着某种意想不到的冲突?
5.我知道您的名字,是由于十年前北京三联书店翻译出版了您的《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据我所知,您的这本书在中国思想界也是很有影响的。至少书中阐述的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容易出现无序,因而强调权威秩序的作用,不少人都感到共鸣。特别是主张“新权威主义”的一些人,更有遇到异域知音之感。您对这本书以及中国读者,有什么话要讲吗?
6.现在已经是1999年2月底了,二十世纪只剩下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此世纪转换之际,您对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和马上就要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有何检讨和展望吗?当然我是指比较有形上意义的检讨和展望。还有,您预期中美关系在最近以及将来会有怎样的发展?(www.daowen.com)
7.可否透露一下您最近正在关注、正在研究的课题?您的研究是采取个人写作的方式,还是与同道者合作,共襄其事?
1999年2月25日
经周勤女士和梁治平先生的推荐,特请哈佛法学院的於兴中先生担任翻译,“访谈提纲”的英译即出自於先生的手笔。我个人并不赞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所表达的一些观点,我的学界朋友们也大都持批评态度。而亨廷顿教授显然了解都是哪些国家的学人对他的文章持有异议,所以他一般不会见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来访者。他之所以同意与我见面并接受访谈,我相信是杜维明先生的有效斡旋,他一定对我作了令亨廷顿发生兴趣的介绍,因此我也格外重视这次难得的机缘,我准备好要跟他畅论一番的。
不料访谈时间出了差错。亨廷顿得知的约定时间,是1999年2月25日下午2时。我得知的时间,是2月26日下午2时。待到我和内子26日陪同於兴中先生用完午餐,回到燕京学社会议室,请杜先生的秘书打电话给亨廷顿教授,确认他办公室的楼层位置。他说:“不是昨天吗?我昨天下午等了好长时间。”我们几个人一起面面相觑地定格在那里。亨廷顿先生是哈佛有名的忙人,无论是时间还是礼仪,都不可能再来补做已经过去的昨天的事。“天下事有出奇不意者”,斯为一例。
就这样,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最终和亨廷顿教授失之交臂。
摘自《刘梦溪学术访谈录》序言,中华书局,2007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