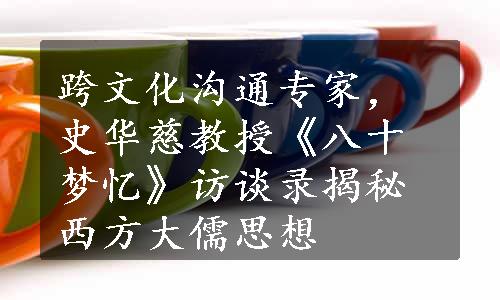
大体上还算没有延误过多时间的访谈文章,是《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史华慈教授访谈录》。所谈内容极为丰厚充盈,是我在哈佛收获最大的一次访谈。2003年首次在《世界汉学》披载时,获致学界朋友的好评。当然这不是由于我,而是史华慈学术思想的冲击力所发生的作用。他毫无疑问是西方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林毓生先生访谈前对我讲:“你见到了史华慈,可以知道西方非常高的大儒是什么样子。”他有无穷无尽的思想,他提问题的视角是面对整个人类讲话。他最关注的是人文精神的建构,他感到最难解释的是人到底是什么的问题。无法想象,这样一颗伟大的灵魂竟会在1999年11月4日悄然仙逝。我在《现代性与跨文化沟通——史华慈教授访谈录》整理完稿之后补写的《题记》中写道:
我很遗憾我与史华慈教授的访谈对话,他没有来得及看到就离开了人世。都怪我不恰当地生病,耽搁了及时整理访谈记录稿的时间。1999年对我是不幸的一年,4月份从哈佛回来不久,就病倒了。直至第二年春夏,方日渐恢复。但更加不幸的是,我所见到的西方最单纯的思想家、最富学养的中国学学者史华慈教授,已经永远不能向人类发表他的睿智卓见了。我和他的访谈对话,第一次在1999年2月9日下午2点到4点,第二次是2月22日上午10时至12时。地点在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对着门,大衣挂在门后的衣钩上。我和林同奇先生坐在他的对面,内子陈祖芬坐在左侧书架前。因为有事先送给他的访谈提纲,整个谈话非常顺利。他谈得愉快而兴奋,几次高举起双手,强调他的跨文化沟通的观点。讲到美国文化的现状,他略感悲观,他说自己也许是老了。这样说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眉宇间有一丝黯然。没法形容这次访谈我个人所受的启悟以及带来的学术喜悦有多大。第二次谈话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张纸条给他,上面写:“启我十年悟,应结一世缘。”当时说好访谈稿整理成文之后会寄请他过目。没想到因病未克及时竣事。而当现在终于成文准备发表,却欲送无人了。成为一次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好在此访谈稿先经林同奇先生根据录音整理并作汉译,然后我参酌现场所做笔记和内子的笔记,最后写定成文。其可靠性,史华慈先生自必认可。如果我揣想不误的话,1999年2月9日和22日我对他的这两次访谈,应该是他生平最后的两次学术对话。因为林同奇先生告诉我,我回国不久,史华慈先生就住进了医院。也许我纸条上的后一句不那样写就好了。林同奇教授为访谈所做的帮助,对访谈初稿的整理、汉译,我深深感谢并心怀感激。
上面这段文字,写于2001年1月24日,如今已经过去六年的时间,而距离我与史华慈先生那次访谈对话,至今已有八个春秋。需要说明的是,史华慈教授的谈话,不是对我所提问题的简单回答,而是参照我的问题,放开来阐述他的思想。我甚至觉得,这是他的一次借题发挥,他显然乐于并且需要发表他积蓄已久的思想。而且,我需要再次向林同奇先生表达我的谢意。上海的史华慈研讨会,他因身体原因没能来参加,但因缘凑泊的是,林毓生先生代他宣读论文,我恰好担任这场论文发布会的评议人。宣读超过了规定时间,主席叫停,林毓生先生郑重陈词:“那就是说林同奇先生没有掌握好时间。”全场莞尔而笑。(www.daowen.com)
会后我打电话给同奇先生,告知他研讨会的情况,并提及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的题目是《史华慈最后发表的思想》。
原载《刘梦溪学术访谈录》序言,中华书局,2007年,第10—12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