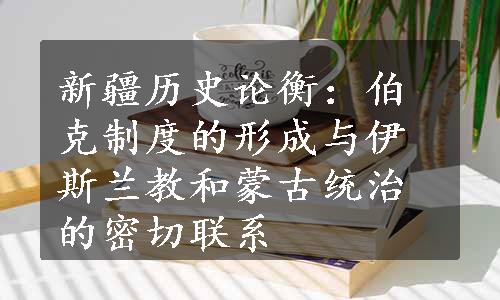
上面我们对37种伯克称名的语源、语意及伯克职掌进行了考察。其中,除密斯伯克、哈什伯克、阿尔屯伯克可认为是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后为开发当地矿产资源而设置,群奇由布伯克可视为同墨克塔布伯克一样,且仅在伊犁地区设置外,其他的33种伯克应是清代以前就存在。如果将原有的33种伯克称名按其语源分类,则阿拉伯语、波斯语的有18种,蒙古语的有7种,维吾尔语的有7种,汉语的有1种。这就表明,维吾尔族地区伯克制度的形成,主要受来自阿拉伯、波斯和蒙古草原方面的影响。如果对伯克职掌再进行粗略分析,则发现阿拉伯语、波斯语称名的伯克,多是伊斯兰教管理和教职人员,而蒙古语称名的伯克,又多是行政、税务及工程管理人员。这种情况又说明,维吾尔族地区伯克制度的形成与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蒙古贵族在西域的统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在10世纪就已传入新疆地区。喀喇汗王朝的“波格拉汗以传播伊斯兰教有功而著名,他使千千万万的佛教徒变成了穆斯林”[57]。但是,在西辽统治者屈从律在位期间(1212—1218),由于他强迫穆斯林或改信佛教,或改信景教,或至少放弃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势力遭到了沉重打击。所以,直到14世纪,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区域的东界并未超越阿克苏地区。
元末明初,是伊斯兰教在新疆大传播的时期。14世纪中叶,秃黑鲁·帖木儿汗(1343—1363年在位)作为新疆地区的第一位蒙古汗皈依了伊斯兰教。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幼子黑的儿火者也热心传播伊斯兰教,并率军对吐鲁番进行所谓的“圣战”,强迫当地居民成为穆斯林。所以,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伊斯兰教便风靡整个维吾尔族地区。
伊斯兰教势力的迅速发展,对维吾尔族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伊斯兰教势力已逐渐控制世俗政权,察合台后王“为人行事,一切都要取得教法允可”[58]。伊斯兰教职人员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这个阶层包括“司法部门的官吏,以及清真寺与礼拜场所的管理人”[59]。所谓司法部门的官吏及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人员,自然是指哈子伯克、斯帕哈子伯克、拉雅哈子伯克、茂特色布伯克、木特斡里伯克等。这些伯克称名也见于16—17世纪的维吾尔族史籍中,如贾拉斯的《编年史》(又名《〈拉什德史〉续编》)记载,在阿布杜·克里木汗时期(1570—1593),哈子伯克早已参与民事诉讼案件的处理,其下还设有军队中的哈子(即斯帕哈子)和城市的哈子,且“位在大伯克之列”[60]。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的《中亚蒙兀儿史》则记载说,哈实哈儿(今喀什)人大毛拉玉素甫就担任过茂特色布。[61]该书第42章还记载了木特斡里叙述“七贤”的故事。另外,沙敖在《和卓传》附录C中说:叶尔羌(今叶城)最早的经文学校创立于希吉历903年(1497)。那么,作为伊斯兰教经文学校的管理者、老师的匝布梯墨克塔布伯克、墨克塔布伯克,最晚也应在此时就设置了。所以说,在维吾尔族地区有关伊斯兰教司法、宗教管理及教职人员的伯克,在16世纪末就是存在的。
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及新疆地区与波斯、阿拉伯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大量的波斯语、阿拉伯语词汇为维吾尔语所借用、吸收,有的甚至保留至今。可以认为,那些与伊斯兰教无关的阿拉伯语、波斯语的伯克称名,如阿奇木、密喇布、巴匝尔、巴济吉尔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维吾尔族地区所采用的。根据贾拉斯的记载,羽奴斯汗时期(1457—1489),赛义德·艾里·密尔咱任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的阿奇木达24年之久。[62]《中亚蒙兀儿史》的作者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也曾担任过叶尔羌的阿奇木。[63]水利在维吾尔族地区农业生产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很早以前该地就设有专门管理水利的官吏。而在帖木儿时期,维吾尔族即称管理水利的官吏为“密喇布”[64],该伯克称名也屡见于贾拉斯的著作中。1603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经过新疆去内地,他描述叶尔羌的商业贸易状况时说,这里“商贾如鲫,百货交汇”[65],是东方的一座著名商业城市。其他如喀什噶尔、阿克苏、吐鲁番、哈密,也都是重要的商业市镇。市场的建立与商业的繁荣,自然需要市场的管理者。所以,巴匝尔伯克应是维吾尔族地区早就设立的官职。在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的著作中,称“税”为baji,而收税的官吏是任何政权也不会缺少的,这一时期维吾尔人可能已称征收赋税的官吏为巴济吉尔。另外,在14—16世纪,中亚地区同维吾尔族地区一样,都处在察合台后裔的统治之下,而阿尔巴布、都官、讷可布等伯克是16世纪乌孜别克、土库曼等地早就存在的官职,[66]因而,维吾尔族地区也应该设置了这些官吏。
至于蒙古语称名的伯克,有的是在蒙古贵族统一新疆后就设置的。都尔噶,就是达鲁花赤的不同音译,是元代在各地都设置的官职。《元史》卷一三四载:“昔班,畏吾人也……闻太祖北征,领兵来归。从征回回国,数立功,将重赏之。自请为本国坤闾城达鲁花赤。”据此可知,维吾尔族地区达鲁花赤的设置比内地还早。如果依尔哈齐像诺尔布先生所认定的那样是元代的断事官,那么该职1274年就在维吾尔族地区设立了。蒙古贵族统一新疆之后,为便于传递军事文报,于1274年在于阗和叶尔羌设水驿十三,1286年又在罗不、怯台、 (车尔臣)与和阗设立了驿站。驿站设立了,自然需要管理驿站的官吏。所以,都官、喀喇都官等伯克的设置可能即在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建立元朝以后,将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及其他条件(如民族)划分成若干种户计,统称为诸色户计,匠户便是诸色户计的一种。他们专门从事营造、纺织、军器、工艺品等各种手工业的生产。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是游牧民族地区的各级行政长官,蒙古贵族统一新疆后,这些官职也在维吾尔族地区设置了。B.B.巴托尔德指出:“14世纪前半叶,察合台诸汗直接统治马维阑纳尔的时候,似乎形成了新的地区划分,撒马尔罕、布哈拉、波斯的‘吐曼’,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的‘鄂尔沁’,都表示小的地区单位。”[67]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也说:“于阗和哈实哈尔(喀什噶尔)的居民可以分为四类。一类叫秃曼,意思是农民。他们臣属汗,每年向汗交租税。”[68]据此可知,在蒙古贵族统治新疆的时候,维吾尔族地区也建立了类似蒙古牧区那样的行政机构。作为这些行政机构首领的多博伯克、明伯克、玉资伯克、鄂尔沁伯克等,也就相应地设置了。还有其他几个蒙古语称名的伯克,我们虽然在史籍中找不出直接证据,但它们都明显地带有蒙古贵族及其后裔统治时期的烙印。如果这些蒙古语称名的伯克是和卓时期(1678—1759)或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才开始设置,就没有必要借用蒙古语称名了。
(车尔臣)与和阗设立了驿站。驿站设立了,自然需要管理驿站的官吏。所以,都官、喀喇都官等伯克的设置可能即在这一时期。蒙古统治者建立元朝以后,将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及其他条件(如民族)划分成若干种户计,统称为诸色户计,匠户便是诸色户计的一种。他们专门从事营造、纺织、军器、工艺品等各种手工业的生产。万户长、千户长、百户长是游牧民族地区的各级行政长官,蒙古贵族统一新疆后,这些官职也在维吾尔族地区设置了。B.B.巴托尔德指出:“14世纪前半叶,察合台诸汗直接统治马维阑纳尔的时候,似乎形成了新的地区划分,撒马尔罕、布哈拉、波斯的‘吐曼’,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的‘鄂尔沁’,都表示小的地区单位。”[67]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儿也说:“于阗和哈实哈尔(喀什噶尔)的居民可以分为四类。一类叫秃曼,意思是农民。他们臣属汗,每年向汗交租税。”[68]据此可知,在蒙古贵族统治新疆的时候,维吾尔族地区也建立了类似蒙古牧区那样的行政机构。作为这些行政机构首领的多博伯克、明伯克、玉资伯克、鄂尔沁伯克等,也就相应地设置了。还有其他几个蒙古语称名的伯克,我们虽然在史籍中找不出直接证据,但它们都明显地带有蒙古贵族及其后裔统治时期的烙印。如果这些蒙古语称名的伯克是和卓时期(1678—1759)或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后才开始设置,就没有必要借用蒙古语称名了。
一些维吾尔语称名的伯克,如伊沙噶、克勒克雅喇克等,也是早已存在的。据J.奥本介绍,帖木儿朝的阿布·赛依德的大臣罗呢敦阿布杜尔·哈密德的职务就是Kerekyarak。[69]而伊沙噶伯克在喀喇汗王朝时期就设置了。
总之,我们从16—17世纪有关新疆史籍的记载中,可以找出大部分伯克称名及其设置的依据。当然,伯克制度同其他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一样,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一些变化,原有的个别伯克称名可能消失。如15—16世纪作为阿奇木助手的歪则尔(Vaizir),已不见于17世纪的史籍,[70]而不见于15—16世纪史籍的商伯克,却在17—18世纪的维吾尔族地区设置了。伯克的职掌前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伊沙噶伯克,从贾拉斯的著作中我们发现,它虽属大伯克之列,却只担负宫廷侍卫或城防之责。但至清朝政府统一新疆前后,伊沙噶伯克却“协同阿奇木以办理庶务”,成了阿奇木伯克的副手。蒙古语称名的伯克职掌变化更大,如都尔噶、依尔哈齐等伯克,在蒙古贵族统治新疆时期,他们都是地位显赫、权力极大的官吏,但至18世纪却成了一般的伯克。这种变化可能反映了蒙古贵族及其后裔在新疆统治的逐步衰弱。当然,我们绝不能因个别的伯克称名或职掌的变化而否认伯克制度的存在。(www.daowen.com)
当然,作为一种官制,仅有称名是不足为证的。实际上,15—17世纪伯克制度已有一整套规章,如任免、伯克养廉、进献制度、会议制度等。
从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和贾拉斯的著作中我们得知,15—16世纪,各级伯克尤其是阿奇木等高级伯克,是由汗直接任命的,主要城镇的阿奇木伯克往往由汗的亲属担任,其辖地也是他们的世袭领地。如阿布杜·克里木汗(1570—1593年在位)就将阿克苏封给其弟穆罕默德汗,又封另一弟为和阗的阿奇木。阿布都拉汗(1627—1665年在位)即位后,也派自己的儿子尧勒瓦斯汗为喀什噶尔的阿奇木。[71]至于小伯克,有的由汗来任命,有的则是由汗授权高级伯克任命。阿布都·赛义德汗(1514—1533年在位)就赐给其相霍加·穆罕默德·沙阿九个官职、九条渠水。[72]所谓赐给九个官职,就是授权让其任命九个伯克。
对于阿奇木以下伯克的罢废,《西域图志》卷三九说:“阿奇木以下,犯小罪,夺其职,为苦役或派课耕,或派监畜牧,或责令入山取铜铅,三年、五年而复之。”这或许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阿奇木伯克的罢废自然是由汗决定的,处置小伯克的权力则有时掌握在高级伯克手中。
伯克的养廉额数是由汗所赏份地及所辖居民的多少来决定的。Б.Д.加富罗夫指出:早在喀喇汗王朝时期,维吾尔族地区就实行给官吏赏赐“份地”的办法,以支付官吏的俸禄,这种份地名为“伊克塔”。“在伊斯兰教法律中,伊克塔被说成是代替薪金的酬劳”。至12世纪,伊克塔中的大部分土地实际上已转化为世袭领地,享有伊克塔土地的官吏也成了封建领主,而耕耘伊克塔土地的农民则完全依附封建领主。[73]蒙古贵族统一新疆后,并没有改变这种制度,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伊克塔土地的数量,并将这种制度推广到游牧草原,[74]被称为“苏尤尔加尔”,即军事封建采邑制度。这种制度至15—17世纪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前举阿布都·赛义德汗赐给霍加·穆罕默德·沙阿九个官职、九条渠水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在阿布都·热西德汗时期(1533—1570),也被赐以六十箭之地的居民、土地和水,还赐给一条渠的土地、水及其他财物。[75]和卓时期(1678—1758),维吾尔族地区继续沿用了这种形式,以支付伯克的薪俸。所以《回疆志》卷四说:伯克“唯序坐次以相统属,无服色崇卑之别,亦无贡赋养廉额数,均视其所辖回民之多寡贫富,恣意索取。”
“份地”或者说封建采邑制度,是在伯克中实行进献制度的前提与条件。Д.И.吉洪诺夫指出:早在10—14世纪,维吾尔族社会中官吏的薪俸就是由农民的无偿劳动得到补偿的。这些农民及其所领土地在伯克供职期间,被指定由伯克管理,其大部分收入归于伯克。[76]作为报答,伯克再把其收入的一部分以贡赋的名义献给他的上司。蒙古贵族统一新疆后,这种形式也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按照封建采邑制度的惯例,小的封建主对大的封建主也负有进献义务。受此影响,伯克有自己的进献制度。《西域图志》卷三九说:“凡阿奇木、伊沙噶新除,必致礼于其汗”,“其物则远方珍异之属也”。“商伯克以下新除,见汗亦如之。有,则致珍异之物。无,则马牛鹰犬器甲之属”。“阿奇木以下,行军得胜,以数军实,必以上品先进于汗。自远方使回,有珍异之物,必以献于汗”。“每大小年,各村庄伯克炮羔炊黍为礼,以致于阿奇木及伊沙噶。”
汗与各级伯克及伯克与伯克之间有他们的会议制度和宴会制度。“每日,阿奇木以下见汗二次,伊沙噶以下至明伯克见阿奇木一次,有计议之事不在此限”。“每岁,汗设大宴会三次,牲牵果品之属,鄂克他克奇掌之。阿奇木设宴两次,各村庄明伯克供之,以大飨僚属”[77]。
伯克的任免、养廉及进献制度、会议制度等情况表明,作为一种官制,伯克制度基本是完善的。如果我们把这些内容与15—17世纪有关新疆的史籍记载的伯克称名联系起来并加以分析,就不难得出结论:伯克制度的形成主要是蒙古贵族及其后裔统治新疆和伊斯兰教在新疆传播的结果。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