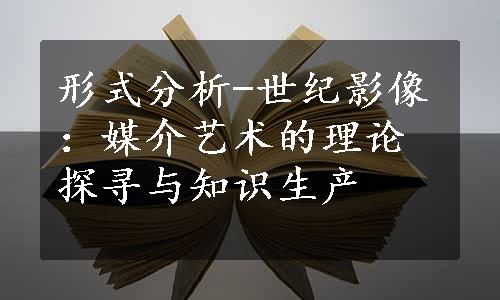
“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就是一个重要范畴,它建立了美学和艺术阐释之间的联系。马克思革命思想的提出,根源就在于他对于现存形式的关注,他将这种革命性的方法称为“唯物主义”。马克思将思想指向物质环境,使哲学的单一主体复杂化、多样化和多元化。同时,他还将哲学的精神领域语境化,将思想置于权力、关系、组织等物质语境中,这种语境化过程的结果是对哲学抽象的“确定形式”的关注。同时,马克思通过对现象的构成、安排、设计和组合方式的关注,使得他的哲学与唯心主义哲学区别开来。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以他对价值“形式”的强调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做出了巨大贡献。[25]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商品进行了透彻分析,在这里,他展开了关于商品形式的分析,即商品形式具有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二重性。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也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他们执着于隐藏在商品形式后面的内容而无法对“真正的秘密做出解释”。相反,马克思则抓住了商品形式本身,指出劳动产品采取商品形式所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是从商品形式这种形式本身而来的。由此发展而来的,是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以及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形式。“在这一经典论述之中,我们发现,正是通过商品形式、人类劳动的等同性、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生产者关系等这些人的特质、人与人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而这种转换正是商品拜物教、商品恋物癖得以成立的基础。”[26]在每一种情况下,马克思都能够进行概念创新,因为他关注形式、系统、整体和复合。形式是由关系性组成的。马克思是一位关系思想家,一位形式思想家,因此他的批判性前提、程序和词汇很容易用于分析文化生产的形式。他标志性的关键举措是问为什么事情会采取这种形式?为什么我们有这种形式的经济生产而不是另一种形式?为什么我们有这种形式的阶级关系而不是另一种形式?正如他描述自己的分析项目时所说,他的目标是“从实际的、给定的生命关系中发展出这些关系被神化的形式”。他想从观察经验主义开始,并从那里转移到一般性。[27]
马克思对于形式分析的重视,无疑也延续到了詹姆逊与齐泽克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体系的过程中,比如詹姆逊通过将电影形式与叙事内容的辩证统一的分析来观察和思考社会情境、社会条件和社会形式。这一方法主要呈现在其技术寓言主义思想内,主要表现为对电影媒介形式的关注。学者胡亚敏在研究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时提出:“后现代美学已经表现出与晚期资本主义时期高科技携手并进的趋势,高科技手段为作品带来了令人吃惊且富有刺激的综合效果。”[28]在詹姆逊的后现代理论和电影分析中,技术媒介形式分析都占据了异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资本主义晚期的技术是一种不可用于再现的技术,技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语言在‘颠覆主体性’的同时却又拥有‘重塑主体性’的力量”[29]。在高速发展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各种媒介形式,如报纸、电视和计算机等所组成的新机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而这个系统即是“社会关系的象征,也创造了人类关系的一种新模式”[30]。而在这个强大的系统面前,个体无法判断出自己的位置,也无法确认自己是以何种方式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始终无法掌握偌大网络的空间实体,未能失却中心的迷宫里寻找自身究竟是如何被困的蛛丝马迹。”[31]同时,詹姆逊也为主体性的重塑提供了方向,即主体可以在多元的数字交往时代充分利用自己的能动性与开放性,从而将自己扩展到无数的网络之中,最终朝向集体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与批评体系中,詹姆逊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检验电影媒介的波动提供了一个准则,尤其是电视与电影的并置尤为关键。分析《华尔街之狼》时,詹姆逊通过电影形式展现了多种媒介的作用,如电影以一则三十秒的商业广告开场——西装革履的金融从业者们在肆意侮辱侏儒。这个形式之下所蕴含的含义是:并不是那些看似体面的经纪人在帮我们赚钱,相反,他们聚集在淫秽的阴谋集体中,对残障人士进行毫无人道的羞辱。正如电影其他部分所展示的那样,他们还参与毒品和卖淫等多种犯罪活动。这部电影提供了两种不同形式的金融业表现形式:一通过电视广告表现行业自身,二通过色情办公室派对进行电影表现。詹姆森曾表达过有关视差的观点,即电影的“与另一种媒体的竞争”,通过这种竞争最终肯定了电影的“本体论首要地位”。正如《华尔街之狼》向我们所展示的那样,这种跨媒体对抗具有三个含义:第一,媒介在表现效能或真实性上的冲突(这将体现《华尔街之狼》如何定义“本体论首要”);第二,在可变交付模式的商业环境中,电影可以通过DVD、流式传输或下载等方式进行观看;第三,关于表征的媒介特殊性的论证。[32]詹姆逊通过对电影媒介形式的论证,将电影本身与经济基础、社会背景等联系起来。同时,他认为形式与叙事辩证统一的,而形式的“遏制策略”之下所掩盖的是意识形态。同时,詹姆逊定义中的叙事不是封闭自足的文本,而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即将叙事看成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想象性投射。在他那里,“叙事首先表现为一种美学的形式,当人们在自身条件下难以驾驭其现实的社会矛盾时,就会在美学领域内寻求某种纯形式的解决”[33]。詹姆逊的贡献在于,他指出了这种解决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的意义,“审美或叙事形式的生产将被看作是自身独立的意识形态行为,其功能就是为不可解决的社会矛盾发明想象的或形式的‘解决办法’”[34]。
与詹姆逊对媒介形式的侧重及其试图将叙事、形式和意识形态进行辩证交织不同,齐泽克的电影分析是从叙事内容转向形式模型。在通常的电影分析语境中,电影是一种“讲故事”(story telling)的方式。但齐泽克却在《斜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Looking Awry:An Introduction to Jacques Lacan through Popular Culture)撰写的序言中,提出了一种电影分析模式:“我们从一开始就要剔除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叙事内容,只留希区柯克电影的高强度的形式模型(formal pattern)。如果我们要对希区柯克的电影进行严肃的社会批评性解读,我们也理应仔细辨析出早已渗入纯粹形式层面的社会中介(social mediation)。”[35]这时,齐泽克举了一个希区柯克《迷魂记》(Vertigo)中主客观镜头切换的例子,并指出其中的主观镜头实际上是“伪主观镜头”,是男主人公斯考蒂的想象。齐泽克论述道:“这两个镜头虽然已经主体化,但无法把它归诸任何的主体。我们从这两个镜头中得到的,正是纯粹的前主体现象(pre-subjective phenomenon)。玛德琳的侧影是纯粹的假象,充满了丰富的力比多投入(libidinal investment)。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因为过于主体化和过于强烈,这样的力比多投入是任何主体都无法承受的。”[36]这里,齐泽克所展现的,是希区柯克电影中的“形式模型”。这也是齐泽克电影分析的秘密所在,“即通过摒弃一部电影的整体性转而分析其中的某个特定的代表性场景。这个场景中往往‘浓缩(encapsulate)’了整部影片的观影结构,从而建构了特定的欲望模式”[37]。(www.daowen.com)
无论是詹姆逊对形式与叙事的辩证统一,还是齐泽克对表层形式模式的重视,他们都试图通过电影的形式分析来抵达意识形态批判。只不过詹姆逊认为意识形态是在整体形式的更深处,齐泽克则把目光聚焦到了形式本身。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