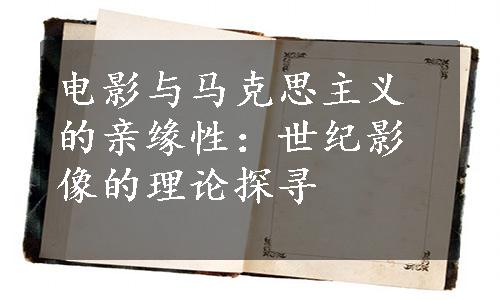
大众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生活体验在结构上与观影的体验相类似,这是因为电影观众从资本主义令人困惑的外观与本质的矛盾中提炼出了相同的经验。著名的情境主义理论家和电影制作者居伊·德波(Guy Debord)在他对20世纪的描述中改写了马克思的开场白:“在现代生产条件盛行的社会中,所有的生活都表现为巨大的景观积累。”电影可以通过将日常的幻觉转化为动态的画面为社会现象提供形式,并向观众揭示社会政治和知识经验。导演们也通过引人注目的剪辑、夸张的镜头和打破第四堵墙等手段来暴露电影充满矛盾的幻觉本质。这样,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在电影这一艺术的中介下联系到了一起。
首先是电影及资本主义的密切关系。“视觉本质上是色情的,也就是说,它以全神贯注、无意识的魅力而告终。”[6]从置身杂耍场开始,电影就是一种有“裸露癖”的艺术形式,通过诱发观众的“窥视癖”来进行艺术创作。视觉性是无处不在的,是看似自然中立实则有倾向性的。主体与视觉场,主体与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关系存在同源性,这种同源性使我们能够看到资本主义的非自然状态及其隐藏这种非自然状态的力量。尽管资本主义是一个塑造主体的系统而不是一个捕捉外观的领域,但它与视觉领域有着共同的关键要素。因为就参与的主体而言,资本主义和视觉领域似乎独立处于一种中立状态中,它们将自己表现为再简单不过的井然秩序。[7]
但主体的看与视觉场域的中立表象,始终会被凝视所扭曲,就像资本主义秩序不过是一种假象一样。齐泽克认为:“在拉康成熟的思考中,凝视已经不再属于主体,视线是大他者的视线,凝视则来自客体。”[8]此时,不再是主体观看,而是客体凝视,客体从我看不到它的地方凝视着我。而当电影作为一个屏幕对凝视——这一实在界之物,进行实体化呈现时,作为平面的电影屏幕却暗示着真实之物的深渊,最终成为一个“平面之深渊”[9]。当我们看到凝视时,我们看到视觉场是围绕着我们的视觉构成的、为我们的欲望所扭曲了的,这种扭曲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正如琼·科普耶克(Joan Copjec)在她对凝视的描述中所指出的那样,“在凝视被识别的那一刻,整个视觉领域,呈现出一种可怕的变化”。我们看到我们的欲望被一个看似中性的视觉场所捕获,在这个瞬间,视觉场域的中立性消失了,而扭曲这一场域的政治影响变得显而易见了。典型的好莱坞电影竭力复刻观众在生活中真实的视觉场域,试图模拟一个中立透明的资本主义世界。同样,明明是主体活动构成了经济场,但资本主义却将经济呈现为存在于主体活动之外的场域。同时,好莱坞电影不仅仅传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它还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以资本主义作用于主体的方式作用于观众。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无法轻易地认识到自己参与了这一体系的构建。在纪录片《变态者电影指南》的最后,齐泽克表示:“为了理解今天这个世界,我们真的需要电影。只有在电影中,我们才能得到我们在现实中不准备去面对的残酷的一面。如果你们想要在现实中找到比现实更加现实的东西,就去看故事片。”这是因为电影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我们还可以在电影中看到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固有矛盾,以及发现颠覆资本主义的力量。
其次,马克思主义与电影的相遇。电影诞生于世纪之交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中,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典范媒介,但这并不意味着电影首先或最终是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如果艺术形式不仅能够表征或诊断它们自身的生产条件,而且能够以其反事实的能量和作为创造力的本质指向超越那些仅仅存在的条件的乌托邦视野,那么结论是电影在携带资本主义基因的同时,也指向了资本主义未能实现的自由和集体主义承诺。[10]而这种承诺从一开始就是虚假的,因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不过是有限范围内的自由。实际上在电影发展的早期阶段,文化抵抗就始终存在。有意思的是,一位早期的电影艺术家指出,电影不仅对资本主义很重要,而且对那些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也很重要。[11](www.daowen.com)
电影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是不容忽视的。马克思主义电影要么被定义为“真相程序”,要么被定义为代表解放承诺的“乌托邦空间”。它不仅仅是政治、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在银幕上的应用,这种观点会将苏联电影等作品简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视觉表现,即电影被视为一种服从国家指令的审美方式。与这种观点相反,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电影实践被证明是十月革命的真正延续,它们作为艺术形式继续着革命。[12]苏联蒙太奇学派关注到了马克思主义强调矛盾表象与电影理论强调表象生产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并积极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电影实践。这里,我们借用齐泽克的一个概念——“视差之见”来解释革命政治和艺术之间的矛盾关系。在齐泽克看来,视差是审视同一个客体时两个互不兼容的视角,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不可化约的非对称性。以视差为起点,齐泽克透过黑格尔和拉康解读哲学、科学和政治理论,借助辩证思维和精神分析范畴分析当代文化,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视差法的采用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电影应该被理解为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政策和电影制作者的政治美学之间的相遇。因此,仅仅说革命艺术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对辩证模型进行微调,那么这就要涉及阿尔都塞所提出的一个概念:结构因果关系。这一概念发现如果我们把具体的历史节点置于辩证运动的中心,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将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与电影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新角度。这种因果观点避免将(苏联)电影定义为国家政策的传声筒,而是试图理解革命艺术在社会变革中的自主作用。电影作为革命艺术,积极参与了“新世界”的建设,实际上其间并没有受到明确的理念和政策的约束。毫无疑问的是,从很早开始社会主义政策中就存在着进步主义和生产主义倾向,包括维尔托夫、爱森斯坦、普多夫金等人在内的苏联蒙太奇学派积极探索各种电影技巧和电影理论,并将之运用于更广泛的社会转型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上的差异化和审美上的新颖性促使早期苏联电影超越了对政治政策的简单宣传,而是发展出了一种电影革命美学,这同时也意味着艺术不再只是单纯地为政治服务。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和电影的结合只能通过政治革命美学中所存在的生产性张力来理解,这种张力揭示了共产主义艺术与苏联早期新兴国家之间的新关系。[13]苏联蒙太奇学派的电影作品不仅承载和诠释了现代主义等理念,还通过创造和投射新思想、新视觉图标和新的视觉序列来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帮助苏联创造了新的民族和社会主义身份。由此,电影成了新政权巨大而分散的扩音器。苏联通过文化生产而不是警察等镇压性国家机器,实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控制模式。这一重要的革命启示后来被古巴、埃及、巴勒斯坦等不同国家借鉴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在詹姆逊和齐泽克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和批评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往往是一些好莱坞电影,如希区柯克执导的电影《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2013)、《秃鹰七十二小时》(Three Days of the Condor,1975)、《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1976)等。好莱坞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实际上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大众文化只能作为资本主义的奴仆,表达、转移和还原集体最深刻和最基本的幻想。”[14]美国是一个多语言移民国家,好莱坞电影承担着为美国创造新的国家形象和身份的作用,这与早期苏联电影的作用基本相同。对这些电影进行马克思主义批评,有助于我们发现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既能安抚大众又能阐明革命和解放的必要性。同时,马克思电影理论也会引发一些问题来引起观众的深入思考,如电影媒介如何处理甚至利用主导文化生产的矛盾角色?统治阶级制作的好莱坞电影是否曾经背叛过他们的阶级利益?电影能成为一门矛盾的艺术吗?……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是马克思主义电影理论的一部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