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姬汀
20世纪40年代,师陀是一位活跃于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作品等领域的多产作家。正如耿德华指出的那样,“无论就其作品数量、商业性成功、艺术成就或者文学实验来说,师陀都算是沦陷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2)尽管如此,研究者对师陀的关注并不多。这与同时期作家张爱玲和钱钟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3)在传统的文学史叙述中,他经常被归入京派作家或乡土文学作家。(4)因为,包括代表作《里门拾记》(1937)、《无望村的馆主》(1941)和《果园城记》(1946)等等,他的大部分作品主要讲述乡村和小市民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早期作品《谷》(1936)获得1937年5月在京派作家主导下举办的《大公报》文艺奖的奖金后,他对乡土社会的生动描写和批评引起了广泛关注,他还经常被人与乡土小说的代表作家沈从文相提并论。(5)但实际上,作家本人并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京派作家或乡土文学作家。他在《<马兰>成书后录》一文中说道:“在文学上我反对遵从任何流派(我所以要说出来,因为这大概是我说这种话的第一次也是最末一次),我认为一个人如果从事文学工作,他的任务不在能否增长完成一种流派或方法,一种极平常的我相信是任何人都明白的道理,而是利用各种方法完成自己,或者说达到写作的目的。”(6)他在创作上并没有固守特定的流派倾向或方法,而是尝试了多种方法。叙述视角的多元化运用、文体的变用、多种体裁的尝试等都可以说是他这种艺术探索的体现。在题材方面,不仅限于乡村和小市民,在1936年8月移居上海后变得更为广泛。定居上海后,他创作了散文集《上海手札》和长篇小说《马兰》《结婚》,戏剧作品《大马戏团》《夜店》等以都市生活为中心的一系列作品。可以说,这是师陀文学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的创作范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开始出现对新的都市生活的理解。(7)
1936年秋,我从北平到上海。抗日战争爆发,上海被日寇占领,心怀亡国之悲愤牢愁,长期蛰居上海。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后,曾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直到该台1947年秋冬之间结束文学节目),赖以维持最起码的生活。由于伪币通货膨胀,虽有稿费、剧本上演费的补贴,扔不免时常挨饿。偶成小文,每于稿末注明写成于“饿夫墓”。(8)
上述引文充分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上海这个摩登都市中所隐藏的半殖民语境和民族危机,使师陀把目光转向了这种内在的矛盾,而不是都市的未来。师陀在封闭、麻木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中找不到希望,同样地,上海这一都市空间从另一个方面让他陷入了绝望。可以说,他对都市的现代文明的尖锐批评源于他的这种空间体验。因此,上海时期师陀所写的都市小说是他的整体作家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遵循他对都市空间的批判性认识思路,阐明上海这座近代都市所具有的两面性,以及蕴含在都市日常中的人类的欲望。
20世纪40年代,师陀的两部代表性作品《马兰》和《结婚》虽然都是以都市为主题,但是表现形式截然不同。《马兰》以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批判了左翼知识分子;《结婚》则讲述了以所谓的文明之名享受物质生活的上海都市人的日常生活。本文将着重分析描绘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空间特征的《结婚》。抗战后期创作的《结婚》以1941年日本攻击珍珠港前后的都市上海为背景,讲述了厌倦教师生活的胡去恶投身投机事业,逐渐走向崩溃的过程。(9)小说分为两部分:上卷由胡去恶写给为躲避战乱逃往乡下的情人林佩芳的六封信组成的;下卷叙述者的视角转变为第三人称,共分六章叙述了围绕胡去恶的人物关系。这种视角的变化,一方面暗示了胡去恶的心理变化及对物质的欲望,另一方面也使得人物的各种冲突和投机过程更加戏剧化。
在此,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生活行为方式。与此相关,在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是以“金钱”为标志的都市文化结构和人的欲望。师陀对都市物质文化的批判意识在孤岛时期创作的散文《上海手札》中已经反复体现出来:“总而言之,上海是紊乱的。上海的商人和富翁们就像乡下地主一样,假如空气可以出卖,他们会把空气也存到货栈里去的。”(10)这种叙述是当时上海文化心理和经济现象的缩影,也与《结婚》中人物的整体行为方式相吻合。解志熙所称“生活样式”的这一行为方式,即是“社会化的人类生活模式,又体现为人的具体实存行为与复杂心性”,(11)它所指的并不是单纯的物质生活,还包含了社会文化结构和人类意识结构的变化。因此下面将通过小说中的具体人物来分析其特征。
小说中描绘的上海,是所谓的现代世界,既是价值错位的世界,也是被“金钱”推动欲望的世界。货币经济是现代社会的运作机制,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数学的规定、测量和价值的数量化为基础。这也强化了理性、算计的现代特性。(12)在这样的现代社会中,人际关系或人类本身也会被还原为数量化的价值,从而导致人类固有的本性扭曲变质。小说中的主人公胡去恶最鲜明地展现了小人物被以金钱为内核的上海物质文化毁灭的过程。从这个角度出发,《结婚》被概括为“一个小人物的‘上海梦’的破灭史及其人性的堕落史”。(13)
与崇尚上海物质文明的都市人不同,胡去恶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自己的归属。对他来说,上海这个大都市只是一个冷漠而无情的都市空间。在情人林佩芳一家因战争迁居到故乡后,他变得更加孤独。因为童年的遭遇,他将林佩芳和她的家人当成了一种精神家园。胡去恶的母亲是继室,母子俩在家里一直被欺负,他甚至产生了杀人冲动。(14)母亲死后,他既丧失了自然基础,又丧失了安全感,所以希望通过林佩芳和她的家人找回自我认同。(15)最初贷款做事业,并不是为了追求物质生活,而是想通过婚姻获得安定的生活。
胡去恶虽然因为资金问题去找田国宝借钱,但是其实内心十分看不起田国宝。这可以说是胡去恶对金钱这一物质和庸俗属性的一种内心排斥。同样地,胡去恶对于田国宝的妹妹田国秀的华丽外貌也表现出同样的排斥感,他只是觉得田国秀打扮得像个“四脚蛇”或“舞女”:“她自然也利用自己的聪明,像舞女一样努过力,在镜子前面照了再照,扭了又扭,而结果却给人一个印象:外表是个妖艳少妇,骨子里是呆板愚蠢。譬如照像师在照过的底片上重照进一个人,洗出来两个人重叠,看上去只觉三分像人七分像鬼。”(16)此后,胡去恶通过田国宝认识了投机分子钱亨、自称英国博士的黄美洲等等。在与他们的来往之中,他的态度也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他逐渐陷入物质生活,做起暴富的美梦。
亲爱的佩芳,我们不能老以貌取人!也许是我近来和外界稍有接触,我发现我们成见太深,我们太听信自己了!我没有想到钱亨——一个表面上十足的“小鬼”,而实际却有这么好,他们不但把我认为“老朋友”,还答应帮我的忙,给我去找伙伴。黄美洲也是个了不得的人,他想起组织投资公司,我竟连做梦也没梦见。总之,我们以后谈到种种事业,大家弄的很熟悉。(17)
胡去恶通过钱这一媒介作为交友手段,打开了社交圈。但是他们之间缺乏对彼此真正的理解,只停留在表面的关系。这体现了由“单子”的个人、碎片组成的现代的特征。(18)尽管如此,在金钱和欲望的驱使下,胡去恶无法摆脱这种关系。在钱亨的怂恿下,胡去恶开始投资股票,后来他听到自己投资的股票赚钱的消息,就陷入了自己不久也会赚大钱的幻想。个体与对自己期望的满足之间必然存在隔阂,金钱就很容易调整这个隔阂。(19)可以说胡去恶的幻想反映了这种金钱机制所具有的现代性的贪欲。实际上,钱亨所说的那笔钱并不是直接给胡去恶的,但他却觉得自己已经接近了幸福。
钱真是好东西,有了钱便有了快乐,你到处只看见笑……钱亨向我笑,黄美洲向我笑,老处女也向我笑,大家突然亲密起来,像多年的相好,别怪我浪费,我一出马就得胜,引句俗话:这是开市大吉。我只恨我钱少,赚的不够多;否则,至少是今天,我将把我所遇到的人全请来大醉。请为我快乐吧!为我们的将来快乐啊……!(20)
对金钱的欲望完全改变了胡去恶原有的价值观。不仅如此,他对林佩芳和田国秀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以前胡去恶从自己的情人林佩芳身上看到了温柔、善良、真诚和自尊自立,这种内心的美丽对他来说就是一个理想的标志,他以此安慰自己的缺失。然而,对于逐渐被金钱腐化的胡去恶来说,内心的美丽失去了本身的意义。胡去恶认为外在的一面也是人格的一面;曾像“四脚蛇”或“舞女”一样的田国秀摇身一变成为一只高贵妖艳的“天鹅”和上海的“名门闺秀”,林佩芳和坚守气节的父亲都被降格为“落伍的人”和“不识时务的顽固分子”。这反映了金钱彻底颠覆胡去恶原有的价值体系和心理结构的过程。
在这样的变化过程当中,金钱从获利手段变成了欲望本身。在金钱这种欲望的驱使下,越是追求金钱,就越会把人际的关系量化。他要和田国秀结婚的唯一目的也就是金钱。虽然他早就知道,无论在爱好还是生活方式上,自己和田国秀都完全不匹配,但是他已经沉醉在物质生活之中,真正的爱情意义不再重要,只求能得到的田氏一家的物质支持。另一方面,正如胡去恶为了钱接近田国秀一样,田国秀也有自己的目的——对林佩芳的嫉妒和对钱亨的报复。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体现了人性的异化。
这烦躁,无聊,空虚,他没想到别有原因。原来自从放弃佩芳,他的生命失去了向上的目标——至少是维持他稳定的部分,代之而起的是纯粹的肉欲和功利心。为了达到目的,他只得攻击别人的弱点,勉犟自己昏天暗地,以求满足对方。同时他也把自己闹昏了,离开热闹,不和国秀的身体贴近,便感到失了着落。(21)
从引文中可以看出,胡去恶越深入都市的物质生活,就越感到烦躁和空虚。这是异化的一个征兆,也是他走向灭亡的一种前兆。后来当他得知自己被钱亨欺骗,金钱根本没有自己的份儿,他开始发疯,最终杀人。
去恶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眼睛,玻璃球似的,又大又亮,磙动着绝望和恐怖。然而这种绝望恐怖,这种冷的像冰的亮光,不但引不起同情,反而更刺激他的敌意。(中略)并不觉得是在杀人,刀子下去,好像切瓜,给人一种快感。又好像他半生所受的痛苦,终于找到出气的机会,他也不管是头,是脖子,是胳膊,只朝下乱扎。有时刀子滑开了,他换个软的地方,更把上身全力压到刀把上去。(22)
杀人情节展现了人性异化的最极端的选择。胡去恶认为自己的杀人是“吃人的世界”中唯一能做的报复:“这个世界是吃人的世界,别人吃我,我也应该吃人,大家都不需要良心,对不对?”(23)这里出现的刀子——“正义之剑”具有很强的象征性:“那把为母亲报仇,十几年来又鼓励他向上的刀子,于是做了所谓正义的剑。”(24)终于他用那把刀子向世人报仇。但是在吃人的世界里,胡去恶也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这时他说的“正义”的复仇使正义本身的意义处于模糊的状态。杀了钱亨之后,胡去恶也被巡捕开枪打死了。对此,夏志清曾指出:“只有在他杀死钱亨后精神极端清明的一刹那,他才彻底看透自己的本相,但他的激情未几就会被死亡所净化。”(25)胡去恶虽然通过杀人完成了对世界、对人、对欲望的报复,但是他自己也将死去。这种结局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和人类的认识。作者批评了导致人性异化的现代物质文化及社会结构,同时否定了失去本质、陷入盲目性欲望的人类。
如果说胡去恶是刚踏入都市的书呆子,那么其他人物都是熟悉这个都市空间和都市生活方式的都市人。每一个人都是以师陀在上海实际接触到的人物为原型创作,可以说他们是“当时上海的现实人物的复制品”,(26)也是体现物质生活的都市人的典型。首先,外貌就体现了都市人的特点。我们看下面的引文:
(a)田国宝:“单看外表,这位世兄不愧为堂堂丈夫。他个子相当高,营养很好,脸色红润;衣服笔挺,衬衫又白又亮;小学“修身”教他注意卫生,相信为人在世,必须每十天理一回发。他走起路来自然风度翩翩,唯一的遗憾是仿佛脚上生着鸡眼和满脸的面泡。鸡眼使他走路忸怩像女子;面泡使他感到不十全十美,常常要伸手去揪。两种毛病同时似乎又影响到他的性格,他平常很骄傲,因为他有钱;有时候很自卑,因为世上还有很多人比他有钱。”(27)
(b)钱亨:“进来的是个胖胖的青年人,中等身材,脸蛋红润,烫过的所谓‘飞机’头,穿一身咖啡色西装,里头是条子衬衫。从他的外表上我很难断定他是大学生或经常被舞女倒贴的舞客。其实在上海,这两种资格是很难分开的。(中略)他竖起三根丰满的指头,露出三只钻石戒指。”(28)
(c)黄美洲:“他大约三十五岁,长脸尖下颔,额颅很高,很饱满,证明他的大脑发达,为人精明。身上穿着铁青英国料子西装,(虽然有点旧,然而烫得笔挺)朱红领带,小手上一双白手套,鼻梁上架着黑眼镜,分梳的头发上涂饱了油,身上香水气味逼人,看上去像个十足的英国派绅士。奇特的是他既没有胡子,也没有眉毛,脸上东青一块,西青一块,到处都是伤疤。至于他戴黑眼镜,到后来才知道他眼睛瞎,原是用来遮丑的。”(29)
从这些人物的外形描写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现代都市的氛围。特别是干净利落的外貌和穿着整齐的衣着展现了他们都市生活的一面。随着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文化的繁荣,这种都市人的形象经常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但是,追赶潮流,与其说是表现自我的手段,不如说是维持自我感的手段。(30)现代人外表的摩登掩饰了他们内心深处隐藏着不安和焦躁。摩登并不是每个人的个性表现,而是一种都市文明的符号。因此,我们要关注他们身上所带有的身体缺陷。这些缺陷与他们所标榜的精彩、时髦的生活方式相左。作者故意设置这些缺陷来丑化人物,并对近代的价值观提出质疑。他们虽然比胡去恶享有更加丰富的物质生活,但他们的生活终究是在金钱的机制下把一切都物化了,在这一点上他们之间没有区别。
以田国宝为例,他的欲望对象是名利。他以父亲留下的巨额遗产为基础,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这种对财富的满足推动了另一种欲望,这就是对名利的欲望。他结交那些贫穷却有才能的人,并假装自己有高尚的品位,想以此证明自己的道德纯洁。爱好古玩鉴赏是一个标志。他强调这种高尚的品味是家族遗传,自得其乐,但实际上是他所有的古董、书画都只是赝品。而且,这最终只会变质为积累财富的另一种手段。在这里,古董和书画只是脱离传统和道德纯洁性的毫无意义的符号而已。田国宝把胡去恶拿给钱亨抵押的两本稿子伪装成自己的出版物。这种行为更加凸显了田国宝的庸俗和表里不一。从所有东西都是由货币价值来评价的一般价值形态来看,胡去恶的著作虽然无法得到交换性认可,(31)但是对于田国宝来说,因为它可以满足自己对名利的欲望,所以具有同等的交换价值。
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如田国宝一般虚伪、自私。这也是当时上海都市人复杂的、多层次的心理结构的缩影。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身上民族认同感非常淡薄,这反映出半殖民地上海小市民的分裂性。在这样的语境中,他们所指的“和平派”和“抗战派”,都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所做出的选择,与民族的一体感相去甚远。他们用批判的口气来谈论发国难财的人,但是他们自己的行为也大致如此。从这一点来看,他们的立场就是自我分裂的。特别是,他们对于本国战事十分冷静,甚至讨论起美、日、英哪个国家更加优秀。这种分裂的立场使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加模糊。但是在众声喧哗中表现一致的依然是钱的问题:“其实我们做生意的,管他日本人胜也罢,美国人胜也罢,只要有钱赚就好。日本美国,一个要和南京亲善,一个要和重庆亲善,为来为去,还不是为钱?”(32)对他们来说,战时上海这个空间只不过是赚钱的机会罢了。战争这种不稳定的状态诱发了他们的贪婪和欲望。对此,解志熙曾非常恰当地指出:“摩登的上海‘文明’其实是一种偏至的商业—消费文化,唯利是图的‘唯“物”主义’和唯四方时尚马首是瞻的‘摩登主义’,是这个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生态及摩登人士心态的两个基本方面。”(33)
关于都市人混乱的身份认同,我们还要关注钱亨这个人物作为“陌生人”的性格。这体现了被都市异化的现代人的另一个特点。(34)在这里所说的陌生人与本雅明式的漫游者——都市观察者不同,这反而更接近格奥尔格·齐美尔所说的“潜在的过客”:“不是今天来明天走的那种过客,而是那种今天来明天会留下来的人——也就是所谓潜在的过客。虽然不再离开,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克服来去自如的轻松。”(35)钱亨一方面是集体的成员,另一方面也与集体若即若离。他原来的计划是在天津办完母亲的丧事再回重庆,但途中在上海意外地停留了很长时间。再加上他到上海还不到三个星期,所有的钱都花光了。结果他以学习为借口使得父亲允许他停留在此,之后开始陷入上海的都市生活。他崇尚的都市生活就是物质生活。他辗转于酒馆、跳舞场、回力球场等等,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偶然间被介绍到了股票公司。他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奢侈华丽,其实徒有虚名。通过与上海的各类人交往,他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上海这个都市的属性。但实际上,他所交往的所有人对他来说都无异于陌生人,只是根据彼此的需要而维持关系。特别是他跟国秀的关系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之间的亲密度也取决于需要的程度。(36)可以说,他最终未能摆脱以物质生活为基础的金钱的束缚,在无法离开上海、也无法完全定居的界限上,注定要不断地漂泊。
另外,在小说的结尾部分,所有人都在走向没落的道路,黄美洲反而似乎通过“结婚”达到了目的。但是,庆祝美洲结婚的酒席再次对他们的“成功”提出质疑。反讽的是,黄美洲的婚礼是靠他离婚诉讼所得的钱才得以成行的。黄美洲表面上看起来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对所有事情都表现出旁观者的态度,但实际上,就像他的假名“美洲”和“博士”头衔都只是虚名一样,他不过是把自己包装成留学派博士的庸俗小人物而已。黄美洲与张小姐的婚姻,只有一方是瞎子,另一方是相貌丑陋的老处女,才有可能实现。这样的细节安排给小说增添了喜剧性,使整部小说成为了围绕都市的一个悲喜剧。小说中的人物互相表现出的友情、礼节、亲切只不过是提高自身价值的“个性(personality)包装”。这种肤浅的关系如果相互丧失交换价值,必然会瓦解。(37)小说描述了人物之间的链式关系——每个人物因自己的利益而互相欺骗。作者通过这个作品,集中表现了被异化的都市的人类群像,批判了连人类也被物化的现代文明。
《结婚》的每个章节在特定的空间中展开,特定的空间则与文化相联系。根据通过空间来剖析文化的新文化理论,“文化以空间为媒介构筑,反之也会构筑空间本身。”(38)因此,观察空间的暗喻,就能了解构成文化的内在体系。小说的主要叙事空间包括居住空间,还有咖啡馆、股票公司、跳舞场、电影院、饭馆等等。这些空间既是日常生活的空间,又是反映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空间。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消费文化主体的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和他们的意识。尤其是小说中人物对空间的体验与他的行为或意识的变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空间作为一种象征和符号,有必要着重分析考察。
外滩我当然来过,只是来这么早还是第一次。你瞧那些人罢,各种各样的车子,四面八方,打每条马路不断涌出来,滚滚像无数条奔流。真是洋洋大观,惊心动魄的场面!人和车搅在一道,把路填塞,只听见人的吆喝声,三轮车的铃声,汽车的喇叭声哄哄然闹成一片,你就别打算分出谁是谁的声音。所有的脸都是呆板的,虽称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其实像被骗迫的野兽,除了匆忙与冷淡,压根儿就没有表情。他们是上千百种写字间去的,大家有个共同目的,为实现各自的野心去上战场。连走路都想战场。在这里你看不见中国人提倡了数千年的品德,只觉得所谓仁义礼让,根本不曾在我们国土上存在过。(39)
外滩通常被看作是上海现代性的一种能指。黄浦江边的摩天楼和异国建筑,既是进步的象征,也体现了殖民统治的欲望。这一点看,外滩是具有双重意义的标志性空间:“外滩象征着权力意志,暗示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于租界空间的掌控,是西方殖民者征服和开发十里洋场的集体意志的投影。”(40)主人公胡去恶在外滩首次感受到了上海作为现代都市的残酷法则——“优胜劣败”。“佩芳,我在上海好多年,直到今日,才感到过去的生活不算生活。一个千古不变的原则:为人在世,无须慈悲,优胜劣败,谁力量大,谁就有生存的权利。”(41)从这一角度来看,胡去恶所感到的外滩的鱼龙混杂、快节奏、人们的冷淡无情,可以说是半殖民地上海的一种象征。
股票公司集中再现了被物质文明扭曲的现代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战争点燃了个人的物质欲望,投机分子重新活跃起来。在这个空间里股票决定着个人的命运,所有的东西都是由物质价值来评价。无论身份卑微的市井无赖,还是地位尊崇的大学教授,表面上都是一样的。与文化界人士交往、强调自己高尚人格的田国宝全身心地投入到股价中,像“热锅里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的样子更加凸显了现代文明的消极性和破坏性。将股票公司比喻为“围场”或“战场”,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种半殖民地都市空间的特性。胡去恶和其他人要一起组织一家投资公司,“太平洋投资公司”的假想空间也与此相似。虽然有着远大的目标,但他们的计划不过是纸上谈兵,没有具体内容。这从投资公司的简章中也可以看出:“第一条命名:本公司定名为太平洋投资公司。第二条宗旨:提倡赚钱。第三条营业范围:投资于股票及其他工商业,将来更推广到文化事业,教育事业。第四条……”(42)他们对物质的欲望反映在这假想空间之中。作为欲望的载体,都市空间与作品前半部分描述的乡村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天你首先起身,用冷水洗过脸,扰扰头发,赶紧上设在大庙里的学堂去。那个以自立创办小学的老校长,你父亲的学生,因为你在大学念过书,也特别对你敬重。你弟弟顶无聊,起来得顶晚,他帮你父亲把杂货铺的牌门打开,将香烟,肥皂,毛巾整理好,然后坐下去读你父亲上天下午给他讲的古文;你父亲戴上老花眼镜,就在你弟弟对面,开始极吃力的读电机学或植物学;而在里边,你母亲则烧饭扫地,一切琐碎杂事归她负责。你们把屋后的荒园改成菜园,傍晚你弟弟这一天应做的功课完了,你父亲也把小铺关起来,他们带着水桶锄铲,和你母亲到园子里掘土下种。礼拜天你们整天团聚,大部分事件都话在园子里。(中略)你活画出衣服乡下和平空气的图画。(43)
此处描述的乡村充满着和谐、温暖的情调,可以说是胡去恶理想中的乌托邦。然而,师陀并没有把它当作都市的一种替代空间。因此,表面上虽然描写得很和谐,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乡村的怀旧或肯定。根据提姆·伊登斯尔所言,高度浪漫化的乡村修辞学随着近代浪漫主义的发展,被描绘成“守护民族灵魂的地方,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的本质民族精神停留的地方”,并一直应用于民族意识形态的生产。(44)师陀所描述的乡村是一个完整的、理想的空间,它反而与真实脱离,在神秘化的民族意识形态中产生裂痕。那本来就是一个并不存在的理想空间,结果只能被拆解,无法获得现实性。乡村不是胡去恶自己亲身经历的空间,而是经过林佩芳想象的空间,这一点也充分地说明了这种虚构性。这与师陀之前的乡土小说所具有的批评意识一脉相通。对于乡村和都市,师陀并没有试图抬高某一方,或贬低某一方,而是希望描写出自身对于两者复杂的心理结构。即,这个空间暴露出来的“历史与现实、理性与情感、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和由此产生的文化后果的忧虑,以及物质与精神进程不和谐性等一系列矛盾”。(45)因此,作品前半部分出现的理想化的乡村空间和随后出现的现代都市空间,形成了相互批判和对照的关系。
此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咖啡馆、跳舞场、电影院等等也值得关注。这些空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流行,成为都市人重要的文化空间。咖啡馆、跳舞场和电影院将都市包装一新,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使人们感受到时髦的都市感觉。但另一方面,在殖民统治者的立场上,这些空间在无意中可以减少殖民地大众的反抗,同时也成为管理和监督有效手段。商业性、娱乐性空间在战时状况下依然盛行,刺激大众情绪,这体现了半殖民地都市空间所具有的双重面貌。小说中的人物都沉迷于这些空间无法自拔,沉醉在现代文明带来的欢乐和幻想之中。他们经常在咖啡馆、跳舞场、电影院、饭馆、酒吧活动,这些空间象征了当时都市人的生活态度。
以田国秀为例,她喜欢打扮、跳舞、吃和出风头,经常把自己幻想成好莱坞演员瑙玛·希拉或费文·丽。其他人物也都认为自己的摩登生活方式才配得上上海这座现代都市。他们表面上与胡去恶交往,内心却轻视他,认为他愚笨迂腐。在陌生的上海,胡去恶也常常感到自卑和不安。这种挫折感与其说是在“流行”中被疏离的不安感,不如说是在“文明”中被疏远的不安感。(46)这种不安或焦躁就是激发他的潜在欲望的主要动因。从这个角度来看,胡去恶对空间的经验与他的心理状态相呼应。
我的膝盖碰过她吗?我的肩膀挤过别人,腿太硬,步子不合拍吗?谁也没有时间去想……我们卷在人堆里,就像卷在波涛里,一开始我是被动的,国秀有时候推我,有时候又把我施开。动作是缓慢的,在和谐,舒服与节奏中,我慢慢自由了。我们滑着,摆着,旋着,或是说游着,情绪随着音乐,旋律增高,动作越来越快,我心里直叫:“转呀!飞呀!”正在热烈到难分解之际,情绪高到不能再高,歌声也短促到不能短促时,忽然又回复到开头时的腔调。(47)
引文细致地描绘了胡去恶第一次去跳舞场时的感情变化。由此反映出他沉溺于都市物质生活的过程。特别是,描述跳舞场的一系列形象:熙熙攘攘的人群、嘈杂的音乐、闪烁的灯光……这些经常被作为象征都市的享乐和颓废的符号,出现在众多文学作品之中。在《结婚》一书中也有同样的描述。对于作为一名普通历史教员的他来说,在跳舞场的经验是他从未体会过的新鲜感觉,而这种刺激唤醒了他的潜在欲望。他兴奋地说:“亡了国也不用管它,及时行乐的时候!”(48)这句话流露出他的欲望。他总是认为自己学习过历史,能够彻底了解社会,但在物质的催化下,他所了解的历史反而失去了其本意。贴近现代社会和文明的冲动使他很快为都市的物质欲望所同化。但事实上,并不是他掌握了物质文明,而是物质文明吞噬了他。他还不知道由幻想组成的世界随时会被打破。所以当他发现自己被骗了,一切都是虚假的时候,空虚感就会被放大。他得知所有内情后——他失去了爱情、失去了钱、失去了最后的希望——小屋的回归象征性地表现出他的这种心理状态。
起初他望着屋顶发愣,屋顶上有一块大霉斑,去年夏天漏湿的,好像和他的被坑有什么关系,直望到头晕为止。随后他眼睛移到涂着臭虫血的墙上,由墙上移到斜倚的书堆上,由书堆又移到满是烂纸的桌子上,最后望望桌子上的玻璃杯。这一切原都跟他不能再熟的,现在却像老狗,眼巴巴望着他,又可怜又恭顺,仿佛说:“你也想到过我们吗?”他的确可怜它们,它们的确给他一种如见故人,又生疏又亲近的感觉。可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别的表示。他的眼睛是冷淡的,仿佛告诉它们:“我过去把你们忘了;可是我顾不了你们,你们去吧。”(49)
在熟悉变得陌生、陌生变得熟悉的客观距离上,空间才显现出它的本质。他的破旧的房子象征了被笼罩在他幻想中的近代都市空间的真相。在进步、文明、自由的美名下,他为现代的强大力量所迷惑,但他真正拥有的却只是空虚和无力。师陀通过象征性空间反复强调的是,对物质的渴望和盲目追求最终破坏了人类固有的生活方式。作为“殖民化而商品化的、销售而购买的、创造而破坏的、利用而误用的、投机而斗争的现象”,空间本身既蕴含着近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又体现了复杂错综的现代人的精神。(50)师陀对半殖民地都市上海的空间认识很好地体现了上述批判。
上海这一都市空间不断变化。如今,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面貌,无疑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文明、进步的上海,其现代性包含了更多的层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沦陷时期的上海更具有特殊的空间特性。当我们回忆起20世纪40年代时,不能不提的是“抗战”这一历史事实。在应对日本侵略的20世纪40年代,上海主要被看作是帝国主义权力压迫和掠夺的现场。在抵抗和胜利的民族主义下,“被占领”的历史事实只能被掩盖。在研究沦陷时期,我们有必要超越压迫/解放的二分法,考察更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研究也因为视角的变化,有了多种可能性。中国文学史在概括40年代文学时,往往强调解放区或国统区的抗战文学,而沦陷区文学则很少受到关注。当然,从沦陷区的政治形势来看,作家的活动必然会受到限制,因此沦陷区文学整体上呈现出浓厚的商业化、日常化的倾向。这也体现了被占领时期的时代状况和生存方式。即,战争状况下的文化心理和对人类基本生活条件的反思,在特定空间内以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关注沦陷时期在上海活动的各种作家和作品可以补充文学史的某种空缺。
从这方面来看,本论文考察了师陀的都市叙事。通过师陀的都市叙事可以了解到生活在战争时期人们的另一面。小说《结婚》以作家的个人经验为基础创作,在师陀的笔下,上海赤裸裸地表现出名誉、欲望、金钱、虚荣伪装之下的现代的本质。无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战争都是破坏人类生活的最暴力手段。小说背景的战时上海,物价暴涨,经济膨胀,生活每况愈下。这些危机加剧了人们之间的疏离和不信任。师陀细致地描绘了在上海这个欲望空间中人们逐渐物化、异化的过程。与解放区的革命叙事、30年代的现代主义不同,师陀的小说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现实。可以说,师陀的这种批评意识对当今现代社会也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1) 本文改编自作者的博士论文《沦陷时期上海文学的日常性研究》第四章“异化的都市日常”中的第三节。参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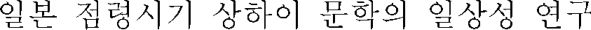 》,高丽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高丽大学博士论文,2017年。
(2) 耿德华著,张泉译:《被冷落的缪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3) 在韩国学界,师陀的相关研究不多。研究论文有金多正:《师陀乡土小说的作家意识研究》,高丽大学硕士论文,2013年;金多正:《<夜店>的主题意识考察》,《人文学研究》2014年第97号。
(4) 最具代表性的有钱理群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书中将师陀归类为京派小说家,从以下三个方面概括其艺术个性。第一,他农村人物贫富的清晰度很明显。第二,是他的讽刺的加重。第三,小说的叙述更讲究。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46页。
(5) 剧作家李健吾曾把师陀和沈从文的小说视为乡土文学之列,论及两者之间的差异。李健吾认为:在沈从文的小说世界里,作家当年内心的创伤已经结了痂,给人以安慰,而师陀则把他的经历活生生地展现出来,流露出抑郁不平和痛苦。耿德华著,张泉译:《被冷落的缪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88页。(www.daowen.com)
(6) 师陀:《<马兰>成书后录》,载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7) 杨义也指出:师陀从北平搬到上海是他转向都市文学的重要艺术转折点。杨义:《师陀:徘徊于乡土抒情和都市心理写照之间》,《文学评论》1990年第2期。另外,王欣认为中原、北平、上海是影响师陀创作的重要地域,这“三个不同地域的经历,使他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现代都市文化和西方殖民文化的相互影响。”王欣:《师陀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页。
(8) 师陀:《师陀自述》,载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9) 《结婚》于1945年初夏完成,从1946年9月9日到1947年4月22日在《文汇报》上分157次连载。之后单行本于1946年6月由上海晨光出版社出版。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7、314页。
(10) 师陀:《上海手札·上海》,《师陀全集》5,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7页。
(11)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5页。
(12)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著, 译:《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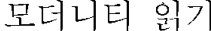 》,
》, ,2006年,第28—29页。
,2006年,第28—29页。
(13) 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54页。
(14) 关于这一点,师陀在《谈<结婚>的写作经过》一文中曾说道:“胡去恶搞来一把小攮子,准备替母亲报仇,是为他后来杀人作的伏线。”师陀:《谈<结婚>的写作经过》,载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15) 埃里希·弗洛姆通过精神分析学的框架,提出了人类存在的条件下产生的需求有以下五点:一、相属需求,二、超越需求,三、落实需求,四、统合需求,五、定向需求。可以说,胡去恶的需求与弗洛姆所说的相属需求或落实需求相适应,这是基于通过自己和他人之间的信赖和爱情等获得安全感的心理。参见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著, 译,《
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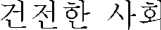 》,
》, ,1975年,第3章以及
,1975年,第3章以及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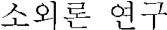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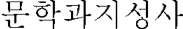 ,1978年,第133—137页。
,1978年,第133—137页。
(16)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7页。
(17)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32页。
(18)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著, 译:《
译:《 》,
》, ,1975年,第132页。
,1975年,第132页。
(20)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52页。
(21)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80页。
(22)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23)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99页。
(24)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25)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97页。
(26) 师陀:《谈<结婚>的写作经过》,载刘增杰编《师陀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146页。
(27)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28)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8页。
(29)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2页。
(30) 约翰·艾伦(John Allen):《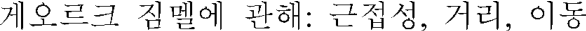 》,迈克·克朗(Mike Crang)、奈杰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主编,
》,迈克·克朗(Mike Crang)、奈杰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主编, 译:《
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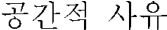 》,
》, ,2013年,第112页。
,2013年,第112页。
(31) 参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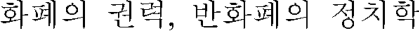 》,载
》,载 编《
编《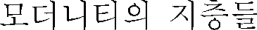 》,
》, ,2007年,第116—117页。这从钱亨的话中也可以看出:“我的亲爷叔!你真阿木林。上海是个什么地方?你要押款,你拿金条,金刚钻,股票,提单都行,可是你的稿子,哈,哈!我说句扫兴话,论斤称还不如旧报纸值钱!”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2007年,第116—117页。这从钱亨的话中也可以看出:“我的亲爷叔!你真阿木林。上海是个什么地方?你要押款,你拿金条,金刚钻,股票,提单都行,可是你的稿子,哈,哈!我说句扫兴话,论斤称还不如旧报纸值钱!”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9页。
(32)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28页。
(33) 解志熙:《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实存分析》,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
(34) 关于都市人的身份认同,许多研究者试图用丧失身份认同或场所感的陌生人、漫游者、游牧民等来表明其特性,这表明现代都市的社会和空间无法提供任何生活依据和归属感。参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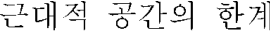 》,
》, ,2002年,第78页。
,2002年,第78页。
(35)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著, 译:《
译:《
 》,
》, ,2006年,第79页。
,2006年,第79页。
(36) 埃里希·弗洛姆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交换欲望已超越原来的单纯手段的功能,扩散到了经济领域以外的地方。“重要的是,人际关系中想要交换的动因也在起作用。爱情也往往是男女之间有利的交换。他们只是想尽可能地获得他们所能期待的东西。”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著, 译:《
译:《
 》,
》, ,2006年,第140页。
,2006年,第140页。
(37)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著, 译:《
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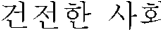 》,
》, ,1975年,第135页。
,1975年,第135页。
(38) 唐·米切尔(Don Mitchell), 外译:《
外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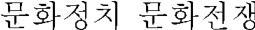 》,
》, ,2011年,第163页。
,2011年,第163页。
(39)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40) 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0页。
(41)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41页。
(42)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39页。
(43)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7—8页。
(44) 蒂姆·艾登索(Tim Edensor), 译:《
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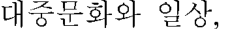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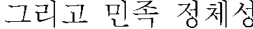 》,
》, ,2008年,第106页。
,2008年,第106页。
(45) 王欣:《师陀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7页。
(4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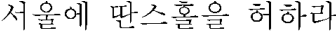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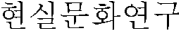 ,1999年,第76页。
,1999年,第76页。
(47)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48)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60页。
(49) 师陀:《结婚》,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年,第103—104页。
(50) 安迪·梅里菲尔德(Andy Merrifield),《昂利·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社会主义者》,迈克·克朗(Mike Crang)、奈杰尔·思瑞夫特(Nigel Thrift)主编, 译:《
译:《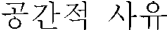 》,
》, ,2013年,第297页。
,2013年,第297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