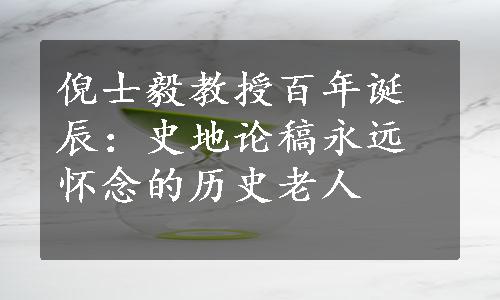
何忠礼
本月初,倪士毅先生的季子集华兄来找我,谈起今年打算为其父亲出版一部庆祝他百岁华诞的文集。文集共分六部分,前面五部分是倪师自己的论文,第六部分“附录”,筛选一些其他人记载与倪师的交往或祝寿文章,集华兄希望我也能写上一篇。我与倪师相识甚早,受教亦深,当即欣然从命。10日,我赴海南三亚度假,因为家事丛脞,又想到时间尚早,所以一时没有动笔。25日,接集华兄来信,说最近倪师病情有反复,这使我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因为我知道,对一个百岁老人而言,这可能会意味着什么。所以接信后,立即抛开其他杂事,回忆与倪师相处的岁月,他的道德、文章,特别是对我的多年教诲,着手进行撰写。
27日中午12时许,我完成了祝贺倪师百岁华诞的文章初稿。大约到下午三时半,当我正在考虑如何立好标题时,立舟兄来电告诉我,倪师已于12时45分归道山矣。噩耗传达来,令人泫然。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谁也摆脱不掉,但想到从此以后,与倪师阴阳两隔,再也听不到他的教诲时,岂有不痛惜哉。
在倪士毅先生从教的四十余年的时间里,受业弟子何止成百上千人,这中间,我自认为是受倪师教育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弟子中的一员。此话怎讲?恐怕还得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说起。
1958年秋天,我考入杭州师范学院(今天浙江师范大学的前身,当时地址在体育场路,今浙江日报社)历史系。在迎新晚会上,系总支李德斋书记向我们一一介绍了系里的教师,其中第一个被介绍的是一位个子不高,面露微笑,戴着金丝边眼镜,温文尔雅的中年老师,他就是作为系副主任(当时系里没有正主任)的倪士毅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倪先生。
1947年,倪先生从老浙大史地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以后,史地系成了新建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历史系,他就在该系出任讲师。那么为什么后来他会到杭州师范学院去任教呢?原来,当时正值“大跃进”的年代,各行各业都要跃进,于是许多专科学校不管是否具备条件,纷纷改成为学院或大学。刚刚成立于1956年的杭州师范专科学校,也被改名为杭州师范学院,原来的历史科也就成了历史系。可是,新建立的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严重缺乏合格的师资,所以省教育厅紧急从老牌的浙江师范学院历史系里面抽调了四位经验丰富的教师去充实那里的教师队伍,他们中有教授中国古代史的倪士毅先生、教授世界古代及中世纪史的王正平先生、教授美国史的徐敏先生和一位姓徐的先生(此人后来调外交部工作)。
可是,接踵而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宣告了“大跃进”的破产。中央及时调整政策,颁布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为此,从1961年下半年起,大批工厂下马,大批学校撤销或缩编,大批干部和工人下放,许多大学生下乡当了农民,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也在这个时候被撤销,所以倪先生就返回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这一下,原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学生可惨啦,多数被以各种原因强制去“支农”,只有小部分学生能够转入杭州大学历史系读书,我也是其中的一人,所以有幸继续跟随倪先生等其他老师学习历史。
1962年7月,我从杭州大学毕业后,在中学做了16年的教师。1978年政府宣布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遇见倪先生,他知道我过去在系里的成绩比较好,竭力鼓励我去报考研究生。我说自己年龄将近40,历史尤其是外语已经荒废多年,恐怕考不上了。他给了我10个字的忠告和鼓励:“男儿当自强,壮年不自卑。”是年10月,我考入杭州大学历史系,成为攻读宋代史方向的研究生。此时,倪先生已从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调到宋史研究室,于是他也成了我研读宋代史的老师。1981年10月,我研究生毕业后,留本校宋史研究室任教,虽然我与倪先生成了同事,实际上他仍旧是我的老师,而且有了更多的接触和求教的机会。所以我追随倪先生学历史,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了。这里还附带说一下,我爱人向幼琴,是我读杭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和杭州大学历史系读本科时的师妹,她同样也受教于倪师。所以,我在前面说“自认为是受倪师教育最多、关系最为密切的弟子中的一员”,并非虚语。
在读大学时,倪先生给我们讲授的是“中国古代史”。他虽然是温州人,但与其他温州籍的教师不同,上课时口齿清楚,基本上没有难懂的温州口音。他的书法很好,板书写得端正而漂亮,如果将它临摹下来,简直可以作为字帖来学习。倪先生上课的耐心和仔细程度,也为一般教师所不及,所以我每次听课,总能一字一句地把他所讲的内容全部记下来,课后复习看笔记,就如看书一样通畅、明了。(www.daowen.com)
倪先生的诲人不倦,在今天回想起来也深受感动。大学老师授课,多数人在下课后,一拍身上的粉笔灰,夹起讲义,就急匆匆地回去了,学生虽然有问题,很少能逮得到他们。倪先生则不然,他在下课后,总是有意识地慢慢离开教室,给学生以充分的提问题的时间,不嫌其烦地进行解释。所以他所授课的内容,学生们基本上当场就可以得到消化。
倪先生在老浙大读书时,是著名历史学家张荫麟、陈乐素两位先生的高足,加上他自己的勤奋好学,所以学问十分扎实,知识非常渊博。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他给我们讲授“中国古代目录学史”这门课程时,从西汉刘歆的《七略》,讲到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讲得十分系统,很多地方使用了归纳法和对比法,深入浅出,使学生较快地掌握了我国目录学的发展历程和每个时代目录学的特点。其中有不少论点是倪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如他认为:“目录学是史学研究的一把钥匙,不能等闲似之。凡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史学家,必须很好地掌握目录学知识。”又认为:“在西汉以前,史籍还不多,所以在刘歆所编纂的《七略》中,它尚附在其他各略中,并没有单独成为一略。可是到曹魏时,郑默编纂的《魏中经簿》,接着到西晋时,荀勖编纂的《中经新簿》,都将书籍分为甲乙丙丁四部,丙部即是史籍,它已从过去的附庸发展成为大国矣。这就充分反映了两汉史学的发展。”他的这些精辟论述,至今仍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倪先生将这门课程的讲义结集出版后,也送了我一部,更使我获益匪浅。后来,我在撰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一书时,在第二编《史料的鉴别和利用》这部分,说到应用目录学知识以鉴别史料真伪时,在某些方面就吸收了该书的研究成果。另外,倪师对浙江古代史和杭州地方史也颇有研究,留下了许多论著,其中不乏开创性的观点和宝贵的建议,不仅是一笔可观的学术财富,也为建设和保护好杭州的地方文化、古迹做出了很大贡献。
倪先生不仅治学严谨,而且一直孜孜不倦地做学问,到老仍笔耕不辍。听集华说,当倪先生已是九十几岁高龄,因为视力急剧下降,不能再看书时,他对自己早年没有及时去做白内障摘除手术而深感后悔。他说:“如果当时做了这个手术,我现在还能看书、写字,做些学问,不会像现在那样在医院里无所事事了。”听后令人动容。
倪先生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我跟随倪先生这么多年,从未见到他主动去申请一个奖,或者主动去申请一笔科研经费。他也从不以老资格自居,对系里的各项安排提出异议,指指点点。
倪先生又是一位忠厚长者,他待人和蔼可亲,几十年来,从未见到他发过一次脾气,或者在背后议论过别人的短处,对同事说的都是优点和长处,对学生更是爱护备至。兹略举自己亲身感受的一个小例子:说来有点难为情,记得大约在1978年7月上旬的某一天,我在杭州大学参加研究生复试,监考老师恰恰就是倪先生。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结束后,在场的十余名考生先后交卷离了场。我原来以为自己已答完了卷,所以正在逐一检查考卷的答案,猛然间发现,漏答了一道名词解释,此题占了8分分数。怎么办?是硬着头皮交上去,还是暂时赖着不交?我的脑子一下子乱了套。这时我抬头望了一下倪先生,看看他对我延时交卷的反映,是否要来催卷了。不料他看了我一眼后,又低下头去整理刚交上去的试卷了,脸上并没有流露出要来催我交卷的样子。这时我才安下心来继续答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考场里面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大约过了三五分钟光景,我将试题答完后站起来时,才发现倪先生已一言不发地站在我的身后。他对我微微一笑,似乎是对我一个委婉的批评,又像是对我的一种安慰,便将试卷拿走了。使我既感激,又感到有些无地自容。这个印象之深刻,直到今天仍记忆犹新。
时至今日,忠厚长者,淡泊名利,学问功底深厚,心无旁骛,一心只想着做学问的倪师,虽然走完了他一百岁的人生之路,但他却永远活在我们学生的心中。愿倪先生与一个月前刚刚离世的倪师母一起,在天堂过得安详而愉快。
2018年1月29日于三亚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杭州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主任——编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