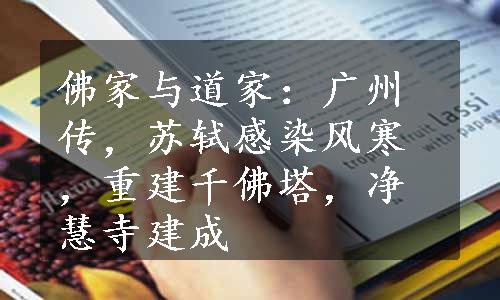
净慧寺自端拱二年(989)重修后,香火越来越旺。元代祐元年(1086),住持德超和尚从湖北请来高僧道琮说法,听众热烈非常,很多人专程远道赶来听法,其中一位是曾任凤翔郡宝鸡县(今属河南)主簿官的南海人林修居士,他是净慧寺的常客,听法之余,和寺僧倾谈寺院往事,大家说起当年舍利塔毁于兵燹,颇为咨嗟。林修感慨地说:“没有宝塔,何以极佛土之庄严,以尽吾邦归向之诚,而为邦人植福之地邪。”于是倡议重建宝塔,并慷慨地捐出万金。他的善举,得到本地绅商积极响应,纷纷解囊。
人们打算在宋初烧毁的千佛塔原址上,兴建新塔,但时隔百年,竟无法确认原址了。直到有人自称得到报梦,要把塔基的面积再扩大一点。大家遵从他梦中指点,扩大塔基,结果挖出了九口古井,位置刚好就在塔基四周,很可能就是五百多年前昙裕禅师挖的那九口井,这才确定了千佛塔的原址。在挖地基时还挖出一口巨鼎,里面藏有三剑一镜,熠熠生辉,如同新的一样。这件事轰动全城,人们蜂拥前来观看。
这时,大文学家苏轼到了广州。他是嘉祐二年(1057)的进士,曾在凤翔、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熙宁四年(1071),朝廷推行新法,苏轼上书分析新法的弊病,令新法倡导者王安石极感愤怒,两人因此产生矛盾,苏轼乃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元丰二年(1079),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下狱一百零三日,险遭杀身之祸。元丰八年(1085),神宗赵顼驾崩,哲宗赵煦即位,苏轼得以重新起用,但才过了九年,再次受到打压,被贬往惠州。
苏轼路过广州时,净慧寺宝塔正在施工。他下榻在不远的天庆观。逗留广州时间虽然很短,但他游览了白云山蒲涧,还去了扶胥镇的南海神庙参观,一路上兴致勃勃,完全不像被贬谪的人。他在天庆观休息时,和观中的道士谈古论今,或者邀约几个斗酒学士把盏欢谈,更唱迭和。苏轼酒意一上头,还在天庆观墙壁上,挥毫题写:“东坡饮酒此室,进士许毅甫自五羊来,邂逅一杯而别。”
苏轼在《广州女仙》一文中,讲了一件奇事:他在崇道大师何德顺知观的室中,见有神仙骑箕箒降临,自称女仙,赋诗立成,有超逸绝尘语。有人见她骑箕箒而至,以为是民间传说的紫姑神之类,但她作的诗句清新俊逸,又绝非紫姑神之辈可比。苏轼戏言:“崇道好事喜客,多与贤士大夫游,其必有以致之也欤?”
朝廷再把苏轼贬往儋州。苏轼去后,天庆观东庑新筑一座供奉道祖老子的“众妙堂”,何德顺知观寄书海南,请苏轼为新堂作文。苏轼欣然命笔,写下《众妙堂记》一文。这一篇文章,辗转经年,不知走了多少道路,才从儋州转到广州何德顺手中。何德顺勒石为碑,立于天庆观内。
元符三年(1100),赵煦驾崩,徽宗赵佶继位,次年改年号建中靖国。朝局虎变,许多前朝谪臣都获得赦还,朝廷三下赦令,苏轼从儋州北返。凉秋九月,他一身笠屐拄杖的装束,仆仆风尘,到达广州,仍下榻在天庆观。这次他因感染风寒,在广州逗留了约一个月。
净慧寺的千佛宝塔已经建好了。塔身高57米,高耸入云,是当时罕有的高层建筑。《重修广州净慧寺塔记》描述:“以为八觚九层,度高二百七十尺,龛藏贤劫千佛泊旃檀五百应真像,下瘗佛牙舍利,殉以珍宝,绀宇翚飞,丹槛离立,轮奂之盛,金碧照空。对严献殿,缭以廻廊,玮丽称是。”蕃坊以南,大江横陈,千帆相继。南宋人方信孺有一首诗《净慧寺千佛塔》,诗中写道:“客船江上东西路,常识嶙峋云外浮。”可见到南宋时,千佛塔还是珠江客船入港的航标。
环绕着宝塔的六株大榕树,虽是残秋时节,依然枝繁叶茂,浓翠欲滴。苏轼每天在榕树下散步,调养病体,当住持请苏轼留下墨宝时,他题写了“六榕”二字,后来净慧寺就改称六榕寺了。坊间猜测,“六榕”二字,到底有什么特别意义?据说,苏轼的爱妾在惠州去世,葬于西湖栖禅寺的松林中,寺僧建了一座亭,苏轼书榜“六如”,取《金刚经》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意。他在净慧寺题“六榕”,是否与“六如”相对,表达了跳出“六尘”的皈佛之心?
其实,苏轼性格开朗,被贬儋州,虽然身处逆境,亦从容面对,自得其乐。他自号“东坡居士”,与许多高僧大德都是知交。后世的一些研究者说,苏轼在儋州已表达出“心似已枯之木”的悲凉心境,但他有一首诗写道:
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
土人顿顿食薯芋,荐以薰鼠烧蝙蝠。
旧闻蜜唧尝呕吐,稍近虾蟆缘习俗。
十年京国厌肥羜,日日烝花压红玉。
从来此腹负将军,今者固宜安脱粟。
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僮仆。
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
却无半点“心如枯木”的样子。苏轼和净慧寺的和尚混得很熟,和天庆观的道士也称兄道弟。他给净慧寺题字,又给天庆观题诗。道可佛,佛亦可道。在他身上,更多体现的是儒、释、道三家的融合。
以《滕王阁序》名动天下的王勃,25岁那年途经广州,游览宝庄严寺,瞻仰宝塔,写下了《广州宝庄严寺舍利塔记》。在这篇文章中,他记述了一个故事:某年宝塔忽现瑞象,放出斑斓的光芒。“玉林照灼,金山具足,倏来忽往,类奔电之舍云;吐焰流精,若繁星之转汉”。宝塔放光,惊动城内居民纷纷涌去观看,“倾都共仰,溢郭周窥,士女几乎数里,光景动乎七重”。
宝庄严寺宝塔的放光现象,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明代正统五年(1440),陈琏的《重修净慧寺千佛塔碑》记载:“塔现神光,观者万余。”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黄衷的《重修净慧寺千佛宝塔颂》也记载,他亲眼所见,立秋以后某日,“有赤光满庭,烨烨如昼,比出四望,光自塔来,星彩顿掩”。两个月后,宝塔再次放光。《番禺县志》也记载了,在明代万历甲寅(1614)和天启辛酉(1621),宝塔都曾放光,一次五色,一次白色,“蒸腾璀璨,烁入重霄”。其后,在清康熙、咸丰年间都有放光的记录。
仅民国时期就有六次。1925年11月17日,有人把白喇嘛普仁所传的六字大明咒、白伞盖咒、黄度母咒,分别用镜框镶起,悬挂在塔的顶层内膛八门上端,十天后,这八门同时放射出青金色光芒。街上值班的警察看见了,大为惊诧,沿街拍门叫居民出来观看。
第二年的7月16日傍晚,塔顶层西南塔门右上角又忽然发出白光,就像一盏圆形的大光灯,光芒四射,历时一小时才熄灭。还有一次一连几晚,白光笼罩塔身,通体熠熠发光,再次惊动全城民众,纷纷涌来观看,一时造成万人空巷的热闹景象。(www.daowen.com)
1931年6月8日傍晚,六榕寺主持铁禅和尚和朋友在友石堂前的太湖石侧露天而坐,谈论宝塔放光的逸事,有人说:塔屡放光,我们发愿修塔,为什么不能放给我们看呢?在座即有人念起光明咒,两三人亦跟着念起来。塔的西南面忽然射出黄光一道,从六层闪到七层,往返回六层,再上七层,如此反复了三次。
几天后,这几位友人再到寺中相聚,各自又邀了一些亲友来,共有几十人,齐集园内补榕亭北面。到了晚上9点,众人一齐对塔行礼念咒,不会念咒的就念佛号。持续念了20分钟,在塔身五层以上各层,略发光影,色白如月映。众人不胜欢喜,发力念咒不断,又过了约5分钟,殊光骤放,五、六、七层塔门被光芒所罩,红墙绿瓦,都变成一片乳白色,八、九两层尤为夺目,有如半空中悬缀两重琉璃宝盖,内中点燃强光的炭精灯,通体透明,塔门都看不见了,色如珠光,不能复辨墙瓦,但感受到强光激射,入眼清凉。坐着的众人都起立作礼,念咒的继续使劲念咒。
这一发光的情况持续了一小时之久,城内街邻住户,空巷来观,由于时间持久,甚至有人开车来观看。寺内人满为患,街上也挤满了围观者。只见此塔八面的光状无异,不时有黄光如电闪般,由五层上闪至七层而灭,或由七层下闪至五层而灭。一小时内,如是上下闪光约十次。然后八、九两层的光芒渐渐收敛,塔门重新显现,但仍看不清红墙绿瓦,再过一会,各层白光同时收敛,绿瓦红墙亦可以看到了。又过了3分钟,白光尽敛,塔影隐约,月沉天黑,回复如初。至此,念佛咒者作结束语,大家都感到大欢喜,赞不绝口。
这几次千佛塔发光,持续时间都很长,亲临目睹的人极多,其中不乏社会名流,报纸做了大篇幅报道。至于放光原因,有各种解释,有说是塔尖放电现象,也有怀疑是和尚做了手脚,在塔里放置放光物,但都是猜测,谁也拿不出确证,最后不了了之。
在苏轼离开广州后一百多年,宝祐(1253—1258)初期,六榕寺忽然发生火灾,迅速延烧了几间殿堂。在熊熊的火光中,惊恐万状的信众,环跪在寺院外,合十祈祷,诵经念佛,很多人忍不住哭了起来。幸好大火没有烧及千佛塔,苏轼的题榜也安然无恙。火灾后,寺内不少建筑坍塌,部分和尚不得不带着六祖的铜像,转移到龟峰的西禅寺栖身。直到1913年,六祖铜像才回归六榕寺。
天庆观在苏轼走后,也发生了一些故事。清人樊封《南海百咏续编》记述,乾隆初年,住持道人黄三纯在井旁隙地开垦菜畦,挖了三四尺深,竟挖出一艘古洋舶,在船舱里找到大量古钱币。他由此推断,“汉魏时此处尚属汪洋耳”。南宋末年,天庆观改为玄妙观。元军攻陷广州时,玄妙观被焚毁,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宣慰使答刺海进行了重修。
元末明初道士萧虚集,居琪林观,以诗文名世,惯以琪林代称玄妙观。仿光孝寺山门背面有“诃林”匾额,玄妙观山门背面亦有“琪林”匾额,所以玄妙观又称“琪林观”。明代羊城八景之一“琪林苏井”,即指苏轼在天庆观所浚之井。
开元寺能够轻易地改为天庆观,说明道观与佛寺的形制、结构相似,互换角色,并没有太多障碍。道教的天庆观与佛教的光孝寺、六榕寺紧紧相邻,与伊斯兰教的光塔寺衡宇相望,构成了一幅奇特的宗教文化图景。
这样的现象,在广州并不罕见。越秀山南麓的三元宫,就是从最早的道观越岗院,变成佛教悟性寺,再变回道教的三元宫。道教虽然从晋代开始就建有道观,但大部分道士,仍是火居道士,也就是平时在家修行,衣食住行与一般人无异,只有遇到丧葬、禳鬼、治病等事时,应主人家邀请,才会换上道袍,去做法事。广州人把这些道士叫作“喃呒佬”,但凡有赞星、脱褐、礼斗、旺土、禳灾、打斋、作七等功德法事,便请他们出场。南宋以后,道教开始效法佛教,有了出家修行、住居宫观的规定。
越秀山上长满了高大挺拔的凤凰木、马尾松、木麻黄和木棉树,掺杂着许多山芝麻、土沉香等黑森森的灌木丛,奇形怪状,千姿百态,有时晚上还能听见野兽的嗥叫声,令人惊恐不安。三元宫隐藏在这片茂密的林木之中。明代诗人描写越秀山之夜:“月色长空满,凄清引猿啸。”附近甚至有老虎出没。清乾隆朝《南海县志》记载:“明崇祯十四年秋八月,虎至城北濠,居民环捕,竟逸去。”虽然这类大型动物并不常见,但当年这里的环境,仍然十分幽深,适合道家修炼。
三元宫是广州最有名的全真派十方丛林道观,所谓“三元”,是指道教所说的天官、地官、水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天官为上元,地官为中元,水官为下元,传统以农历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为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每逢这三大节日,全城的善男信女都会涌到三元宫上香致祭。1933年出版的《新年风俗志》记载:“元宵,观音山(越秀山)的三元宫最热闹了,市内的女人们,都上三元宫去;还有那疍妇、妓女,也都很高兴地去参拜,从朝到暮,路上满挤着人群。”
三元宫始建于东晋时代,当时的南海太守鲍靓信奉道教,在越秀山麓建造了越岗院,相传他年轻时曾拜仙人阴长生为师,学得炼丹和尸解之法,人们都称他为“神仙太守”。后来,有“小仙翁”之称的葛洪,拜鲍靓为师,钻研道术,并娶其女鲍姑为妻,在罗浮山养生修炼,成为有名的炼丹家、医药学家。
在坊间流传的故事中,鲍靓白天在衙门处理公务,晚上就乘着由两只鞋变成的燕子,飞到罗浮山与女婿一起研究仙术。葛洪以丹鼎生涯终老,而鲍靓活到一百多岁也死了,葬在丹阳石子岗上,后来有人盗挖他的墓,但棺材里只有一把大刀。
唐朝时,越岗院改为悟性寺,它是什么时候改为三元宫,众说不一,有说是明代,万历、崇祯两朝都有修葺重建,但明朝的广东方志,并不见有“三元宫”的观名。史料中最早出现三元宫之名,是清顺治十三年(1656)《修建三元殿记》碑;此碑由广东钦差巡抚李栖凤在平南王尚可喜及靖南王耿继茂攻下广州城之后所建,碑云李栖凤于广州“城北观音山之阳,集建太上三元宝殿……皈奉三元大帝”。
三元宫山门前有一副石刻楹联:“三元古观,百粤名山”,笔法雄健。在通往山门的石阶旁,盖有一座重檐山亭,悬挂着“幽林胜境”的匾额,两边刻楹联:“三元胜境留仙影,古观幽林觅鹤踪”。背面的匾额为“岭南福地”,楹联为:“身居闹市红尘外,宫在名山福地中”。山门内依次为王灵官殿、三元宝殿、老君宝殿,两侧有鲍姑宝殿、吕祖宝殿、关帝宝殿、天后宝殿、观音宝殿等配殿。一年四季,香火不绝。由三元宫道士造作的斛食炼度科仪本《济炼全科》,广泛流传于南海、香港和澳门等地道堂,直到20世纪后,仍被广东、香港、澳门等地的道教奉为最经典的施食炼度幽科仪。
广州人热衷于拜神,具有比北方人更强烈的敬神心理,这与广东是一个移民省份有关。历朝历代,从五湖四海来的移民,把自己家乡的神灵都带来了,佛祖、观音、北帝、城隍、洪圣、财神、风神、雷神、妈祖、黄大仙、三山国王、康公主帅、关帝、金花娘娘、土地公公、床头婆婆,各路神灵,数之不尽,灶有灶神,床有床神,厕所有厕所神,水井有水井神,广州成了万神之都。广州人生病了,不喜欢看医生,宁愿求神拜佛。南宋的《舆地纪胜》记载,广州“士人遇疾,唯祭鬼以祈福”。家住双槐洞的明人黄瑜在《双槐岁抄》中也写道:“南人凡病,皆谓之瘴。率不服药,唯事祭鬼。”
“草望春生,人望神扶”的心理,源于移民的不安全感、不稳定感和对命运的无力感,这种心理往往会延续几代人。广东人祭祖先、拜鬼神的风气,一向很盛,他们是多神的崇拜者,只要是神灵,都要虔诚礼拜,哪怕是一棵冒烟的老树、一块出汗的怪石、一截自燃的木头、一堆雨水冲不走的碎瓦泥胎,都可能会引来四乡八镇的民众,焚香跪叩。女人比男人更坚定地相信,“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对她们来说,观音菩萨、元始天尊、天后娘娘,或者其他各路神灵,基本没什么分别,无论拜哪个神,求的都是同一样事情:家宅平安,福禄寿全;连拜神的动作也都是一样的,统统是合十磕头,念念有词。
因为神灵多,佛诞、神诞也特别多。光是佛教,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药王菩萨、药师佛、阿弥陀佛、龙树菩萨、大势至菩萨等,都有自己的诞日。道教的北帝、车公、路头神、清水祖师、九天玄女、谷王、玉皇大帝等,甚至连五殿阎罗王、门官土地,都有诞日,难以细数。各种民间神诞,更多如牛毛,民国时番禺钟村镇,一年之中就有一百多个神诞,不仅有公共的神,各村还有自己的神。一个沙湾镇,就有5座佛寺和14所民间祭祀的祠庙,包括青龙庙、巡抚庙、华佗庙、玄坛庙、天后娘娘庙、观音堂、华光庙、康公主帅庙、三元庙、福善庙、关帝庙、窦母娘娘庙、义士祠、望海观音庙。广州城里的风神庙、龙王庙、真武庙、药王庙、天后宫、斗姥宫、关帝庙、金花庙等,也是布满了三街六巷,走到哪里,都会遇见。
以前荔湾、芳村都属水乡,常有水患,人们除了拜北帝、洪圣,还拜妈祖。民间传说,妈祖是福建莆田望族九牧林氏的后裔,精通医术,治病救人,又会观测气象,预知阴晴风雨。商船和渔船在海上遇险时,她会“乘席渡海”去打救。民间建庙祭祀,称她为天后、天妃、天上圣母、娘妈,是船工、海上商旅和渔民信奉的海上神灵。人们出海前都要拜祭,祈求妈祖护航;平安回航之后,则要进香答谢妈祖福佑。因此,北帝庙和天后宫,在水乡地区,星罗棋布,广州的第十甫、十三甫、怀远驿、新基街及新爵、坑口、南塘等地都有。
不同宗教的神灵同处一室的情形怪象,比比皆是。明代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凤到广州掌管市舶,他是著名的贪官,在大北门直街建了一座北帝庙,供奉北帝,但庙内却立了一块《观音大士像赞》碑,赞美观世音是“西方圣人,洵美且都。华发鬓结,玉骨琼肤。青莲妙相,金缕珠趺”。在21世纪的杨箕村北帝庙里,正殿供奉北帝,两侧还有观音殿、太岁殿和文武殿、财神殿。芳村黄大仙祠,除了供奉道教的黄大仙、吕洞宾,还有佛教的如来、弥勒、文殊、观音大士和韦驮,甚至有凡间的唐朝丞相魏徵。广州人信神,就是如此不拘小节,但求拜得方便,一次可多拜几家。
每逢神诞,民间都要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清人张渠的《粤东闻见录》说:“粤俗最喜迎神赛会,凡神诞,举国若狂。”人们搭起戏台,邀请僧侣打醮,菊部梨园天天演戏酬神,一连演好几天,管弦丝竹,大锣大鼓,通宵达旦。城厢各处,火树银花,红烛照夜。最热闹的是燃花炮、抢炮头活动。炮仗连连爆响,烟焰弥天,声势惊人。包裹在炮仗外的彩色纸,被炸得四纷五裂,有如花飞蝶舞。炮仗爆响前,围观者个个塞耳闭目,侧身低头以避;爆响后,无不凫趋雀跃,欢呼若狂,争相抢夺炮头。抢到炮头的人,便得到神灵庇佑,全年顺景、发财兼平安。第二年要酬还炮头。张渠感叹,这类酬神活动,通常“历数昼夜而后已。计一会之费,可抵中人数家之产。此亦粤之陋习”。
狂欢过后,一切归于平静。人们继续各自的营生,该开铺做生意的开铺,该下田耕种的下田,该去读书的,也负笈出门读书去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