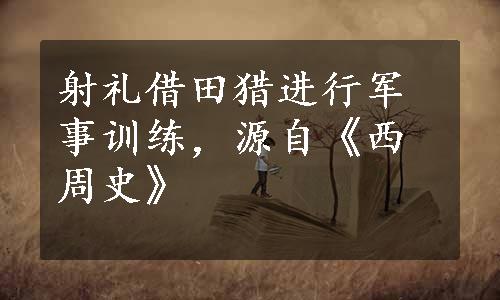
《仪礼》中关于射礼的记载,大概出于春秋战国间儒家的编辑,因为《大射礼》和《乡饮酒礼》中谈到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的,这在春秋末年以前是没有的[3]。但是从《诗经》中有关射礼的诗歌看来,这种礼的基本特点,在西周、春秋时早已形成。
《齐风·猗嗟》说:“仪既成兮,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射侯”即是射礼所射的“侯”,“正”即是“侯”中部的标的。《猗嗟》又说:“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贯”即是射礼中“不贯不释”的“贯”,“四矢”即是射礼中所说“乘矢”,按礼每个射者射一次,都必须射完四矢。《大雅·行苇》说:
敦弓既坚,四 既均,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句,既挟四
既均,舍矢既均,序宾以贤。敦弓既句,既挟四 ,四
,四 如树,序宾以不侮。
如树,序宾以不侮。
“舍矢既均”是说发射四矢都已射中了“侯”,“四 如树”是说发射四矢都已贯穿“侯”中,竖立在“侯”中。《小雅·宾之初筵》说:
如树”是说发射四矢都已贯穿“侯”中,竖立在“侯”中。《小雅·宾之初筵》说:
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射夫既同”是说许多射者都已经“比耦”,“献尔发功”是说大家都要奏其发射中的之功,“发彼有的”是说发射到“侯”的鹄的,“以祈尔爵”是说射中的目的在于祈求辞让酒爵,因为射礼要“饮不胜者”。《礼记·射义》解释说:“《诗》云:‘发彼有的,以祈尔爵’,祈,求也;求中以辞爵也。”从西周金文看来,由司射来教射的习俗也由来已久。静簋说:“王令(命)静司射学宫,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夷)仆学射”,又说:“静学(教)无 (
( )。”可见西周学校中确已设有“司射”,教导“小子”等学射。
)。”可见西周学校中确已设有“司射”,教导“小子”等学射。
古人经常借用狩猎来进行军事训练和演习。“大蒐礼”就是一种借狩猎来进行的军事演习,详第五章《“大蒐礼”新探》。这种射礼,同样起源于借用狩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我们从其礼节也还能看出来。其中最显著的一点,就是射礼把射中目标称为“获”,观察和报告射中情况的报告员就叫“获者”,“获者”看到有人射中“侯”的鹄的要扬旌唱“获”;同时计算射中次数和胜负的统计员就叫“释获者”,“释获者”要根据“获者”的唱“获”来计算射中次数叫做“释获”。“获”原是指狩猎中对鸟兽的擒获(不论是生擒或死擒),甲骨文中述及“隻”(获)得某种野兽的记录很多,在古文献上也多称狩猎所得为“获”,如《周易》“解”九二爻辞说:“田获三狐。”《周易》“巽”六四爻辞说:“田获三品。”[4]狩猎的目的在“获”,而射礼的射中目标也叫“获”,很明显,射礼如同大蒐礼一样,是起源于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乡射礼》说:“获者坐而获”,郑注:
射者中,则大言获。获,得也。射,讲武师田之类,是以中为获也。
郑玄这个解释,很中肯綮。
大概古人最初借用田猎来进行军事演习,后来发展为大蒐礼。同时在辟雍(大学)附近设有广大园林,以便练习射猎;也有在宫中建筑射庐来习射的,如趞曹鼎说:“龚(恭)王才(在)周新宫,王射于射卢(庐)”;匡卣说:“ (懿)王才(在)射卢(庐)。”师汤父鼎也说:“王才周新宫,才射庐。”更有把田猎中擒获的野兽作为习射的目标的。《尚书大传》说:
(懿)王才(在)射卢(庐)。”师汤父鼎也说:“王才周新宫,才射庐。”更有把田猎中擒获的野兽作为习射的目标的。《尚书大传》说:
习斗也者,男子之事也。然而战斗不可空习,故于蒐猎闲之也。闲之者,贯(惯)之也;贯之者,习之也。已祭,取馀获陈于泽,然后卿大夫相与射,命中者虽不中也取,命不中者虽中也不取。何以也?所以贵揖让之取,而贱勇力之取也。乡(向)之取也于囿中,勇力之取也;于泽,揖让之取也(陈寿祺辑本)。
《穀梁传·昭公八年》也说:
因蒐狩以习用武事,礼之大者也。……禽虽多,天子取三十焉,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射而中,田不得禽,则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则不得禽。是以古之贵仁义而贱勇力也。
《穀梁传》所说“其余与士众以习射于射宫”,即是《尚书大传》所说“取馀获陈于泽”而“相与射”,“泽”与“射宫”应在一地,即指辟雍。这样拿擒获的野兽用来习射,就是要大家练习射得“命中”,因此特别规定:尽管在田猎中没有擒获,只要这时射得“命中”就算“获”;如果田猎中有擒获而这时射不“命中”,还是不算“获”。“射”的算不算“获”,主要不在看田猎时有何擒获,却要看习射时是否“命中”。这就是射礼把射中目标称为“获”的来历。
射礼把射中目标称为“获”,因为射礼起源于狩猎,狩猎是以射中禽兽为“获”的。射礼把观察和报告射中情况的报告员称为“获者”,究其原始,“获者”就是狩猎中掌管擒获禽兽的人,也就是“虞”。《周礼·山虞》载:“乃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郑注:“弊田,田者止也。植犹树也。田止,树旗令获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获数也。”《周礼·泽虞》又载:“及弊田,植虞旌以属禽。”射礼中“获者”要扬旌唱获,怕就是沿袭虞人植“旌以属禽”的习惯。在大射仪中,“获者”称为“服不”。《周礼·服不氏》载:
服不氏掌养猛兽而教扰之,凡祭祀,共(供)猛兽;宾客之事,则抗皮;射则赞张侯,以旌居乏而待获。(www.daowen.com)
为什么这个在射礼中掌管扬旌唱获的官员,又是掌养猛兽、提供猛兽和兽皮的官员呢?怕也是由于射礼起源于狩猎的关系吧!看来服不氏原是狩猎中掌管擒获野兽的官员,有时擒获活的野兽就需要养着,以便祭祀上需用,因而同时成为掌养猛兽的官员。
古时“习射”,大别有二,即“礼射”和“主皮之射”。“礼射”张“侯”来射,着重于按照一定的礼仪;“主皮之射”张兽皮来射,着重于“获”(射中),不讲究礼仪。“礼射”采取按礼依次“比耦”而射的办法,“主皮之射”则采取淘汰制的比赛办法,胜者能够再射,败者则被淘汰。所以《仪礼·乡射礼》说:“礼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胜者又射,不胜者降。”[5]“礼射”着重在训练,“主皮之射”着重于比赛胜负。《论语·八佾》说:“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意思是说:“古之道”所以要“射不主皮”,因为主皮之射讲究“力”,而人们的“力”原来就有强弱之分。
“礼射”和“主皮之射”虽有区别,但是究其原始,“礼射”该即起源于“主皮之射”。因为从“习射”的发展过程来看,“主皮之射”以射兽皮为目标,比用擒获来的野兽来习射要简便得多,“礼射”用“侯”来代替兽皮为目标,比“主皮之射”更为进步。《礼记·乐记》说:
武王克殷……散军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
所谓“郊射”,要奏《貍首》和《驺虞》,当即举行“礼射”。“贯革之射”是否即是“主皮之射”,过去经学家还有不同意见,但都是纯粹的习武之射,是无疑的。这里说:周武王克殷后,因推行“礼射”,就代替了纯粹的习武之射。“礼射”不一定是武王开始推行的,但是,由于“礼射”的推行,代替了纯粹的习武之射,该是事实。《周礼·乡大夫》郑注:“庶民无射礼,因田猎分禽,则有主皮。主皮者,张皮射之,无侯也。”郑玄认为“礼射”属于贵族,庶人没有“礼射”,而有“主皮之射”。其实,“礼射”就是起源于“主皮之射”,因为“礼不下庶人”,庶民依然行着“主皮之射”。
“礼射”的起源于“主皮之射”,从“礼射”用“侯”来代替“主皮之射”所用的兽皮,也可看到。据《周礼·司裘》,天子“大射”用虎侯、熊侯、豹侯,诸侯“大射”用熊侯、豹侯,卿大夫用麋侯,都设有“鹄”。据《考工记·梓人》,大射“张皮侯而棲鹄”,宾射“张五采之侯”,燕射“张兽侯”。据《仪礼·乡射礼》,天子用熊侯,诸侯用麋侯,大夫用布侯画虎豹,士用布侯画鹿豕。据郑玄注解,虎侯、熊侯等,即所谓“皮侯”,是用各种兽皮加以装饰的;画有虎、豹、鹿、豕的“布侯”,即所谓“兽侯”,是在布制的“侯”上画有各种兽的图像的。《仪礼·大射礼》说诸侯“大射”所用的“侯”,有大侯、参侯、干侯。郑玄认为大侯即熊侯,“参”应读为“糁”,即“杂侯”,“豹鹄而麋饰”;“干”应读为“豻”,即《周礼·射人》“士以三耦射豻侯”的“豻侯”,“豻鹄豻饰”。各种礼书上所谈礼射用的“侯”,虽然有些出入,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就是比较高级的“侯”直接用兽皮为装饰和制作“鹄”,比较低级的“侯”就只画上某种野兽图像。为什么“礼射”用的“侯”一定要用某种兽皮来装饰或者画上某种兽形呢?因为它原来就是用来代替兽皮的。《周礼·司裘》郑注说:“谓之鹄者,取名于 鹄,
鹄, 鹄小鸟而难中,是以中之为隽。”
鹄小鸟而难中,是以中之为隽。” 鹄,《淮南子·氾论训》高注、《广雅·释鸟》认为是鹊,《说文》认为是山鹊,确是一种“小鸟而难中”的。《考工记》说:“张侯而栖鹄”,“栖”原是鸟息止的意思,“鹄”而称“栖”,其原始本为小鸟可知。那么,不仅“侯”的制作,起源于代替兽皮,而且“侯”中设“鹄”,其原始,就是在兽皮中心放着
鹄,《淮南子·氾论训》高注、《广雅·释鸟》认为是鹊,《说文》认为是山鹊,确是一种“小鸟而难中”的。《考工记》说:“张侯而栖鹄”,“栖”原是鸟息止的意思,“鹄”而称“栖”,其原始本为小鸟可知。那么,不仅“侯”的制作,起源于代替兽皮,而且“侯”中设“鹄”,其原始,就是在兽皮中心放着 鹄作为标的。射礼“张侯而栖鹄”,就是沿此风习而来。
鹄作为标的。射礼“张侯而栖鹄”,就是沿此风习而来。
“礼射”起源于“主皮之射”,其目的也是习射讲武,所以“礼射”除了讲究礼节之外,也还包含有“主皮之射”的内容。《周礼·乡大夫》载:
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
淩廷堪著有《周官乡射五物考》(《礼经释例·射例》附录),对此有详细的解说。他认为,“一曰和,二曰容”,是指第一番射,这时不统计射中次数,但取其容仪合于礼节,所以称为“和”与“容”;“三曰主皮”,是指第二番射,这时讲究射中贯穿,所以称为“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是指第三番射,这时既要容仪合于礼节,步伐和发射都要合乎音乐的节奏,所以既要有“和容”,又要能“兴舞”。凌氏这个解说,比较通达。但是,既然“礼射不主皮”,为什么射礼的第二番射又叫“主皮”呢?乡射礼射的是布侯而不是皮侯,为什么不叫“主布”而叫“主皮”呢?我们认为,礼射的第二番射和“主皮之射”有不同之处,前面已经谈过,“主皮之射”着重在比赛胜负,采取淘汰制的比赛办法,胜者能够再射,败者则被淘汰;而“礼射”着重在训练,采用轮流比射的办法。但是,射礼的第二番射也有和“主皮之射”相同之处,即主皮之射要射中而贯穿,射礼的第二番射也是如此,司射在第二番射时发布命令说:“不贯不释”,就是以“贯”作为主要要求的。因为射礼的第二番射有着“主皮之射”要贯穿的特点,亦称为“主皮”。
方苞认为“习射尚功”(《礼记·王制》),当以贯革为贤,因而“疑士大夫虽画布为侯,必以木为匡,蒙以布,实草于其中,而著于侯之背面以受矢”(《仪礼析疑》)。这个推想很对。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刻纹燕乐画像壶,上列的画像中,就有举行射礼的情况,描写有一对射者(所谓“比耦”)正从堂上向堂下之“侯”发射,“侯”有相当的厚度,射中的矢正贯穿于“侯”中。上海博物馆藏有一件刻纹燕乐画像椭杯,其中也画有举行射礼的情况,描写有一对射者刚向“侯”射毕,有一矢中“侯”之“的”,另一矢稍偏,二矢射中后都贯穿在“侯”中。
图六十三 故宫博物院藏刻纹燕乐画像壶所刻画像中的射礼图
乡射礼的第三番射以用乐节奏为特点,奏的是《驺虞》。为什么要奏《驺虞》呢?《召南·驺虞》说:
彼茁者葭,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 ,于嗟乎驺虞!
,于嗟乎驺虞!
图六十四 上海博物馆藏刻纹燕乐画像椭杯所刻画像中的射礼图
驺虞,有的说是掌鸟兽的官,有的说是“白虎黑文”[6]。但这是一首描写田猎的诗,是可以肯定的。这诗描写的,是在壮盛的芦苇和蓬蒿中田猎,一发而射中五头野猪的情况[7]。“壹发五豝”和“壹发五 ”,是形容田猎所“获”的多。乡射礼的第三番射要奏这样描写田猎获得多的诗歌作为节奏,很清楚,也是因为射礼起源于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
”,是形容田猎所“获”的多。乡射礼的第三番射要奏这样描写田猎获得多的诗歌作为节奏,很清楚,也是因为射礼起源于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