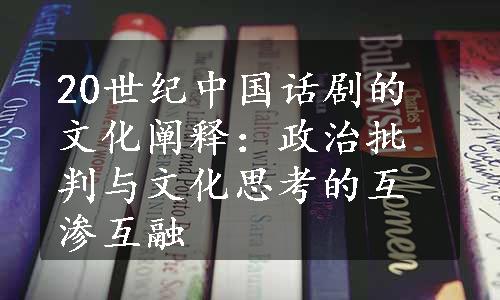
如果我们把此一阶段的讽刺喜剧创作,置放在更为宽泛的文化语境中进行历史性的观照,那么我们不难发现,把政治意识涵纳于文化意识之中,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利追求和透辟入微的文化反思相结合,以强烈的政治敏感和深刻的文化眼光综合交织去打探社会现实,构成了政治讽刺喜剧的共同艺术追求。无论是直言“怒书”的陈白尘,还是崇尚“宣传剧”的老舍,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履践着政治与文化双重自觉的写作追求。一方面,在国家危难、民族危难的历史紧要关头,作为时代的艺术家,他们自觉地听从时代情绪、观众心理及剧作家本人内心的欲求,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度,主动现身于揭露黑暗的政治现实和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文学主战场,运用“辛辣的嘲弄”和“激愤的讽刺”创作了一批宣泄情感、忧愤深广的“暴露性”喜剧;而另一方面,置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新旧文化交替这样的历史语境和写作传统中,他们的戏剧创作也更多地植入了一些文化的关注。在他们的写作意识中,文化问题是与民族复兴、国家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文化批判是与历史批判、政治批判、人的批判、民族批判纠集在一起的。
在《大地龙蛇·序》中,老舍曾这样直陈自己的创作动机,“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它有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在抗战中,我们认识了固有文化的力量,可也看见了我们的缺失。”[5]这句话明白无误地透露出老舍试图从文化视角探讨国家问题、民族问题的用心,也可以看做是政治讽刺喜剧作家的共同创作心态。如果我们把此一阶段的政治讽刺喜剧看做一个复合式的意义结构的话,那么我们不难看出,在再现现实的表层结构上,所有剧作展现的是比较具体切实的当时的社会生活,以一种对具体历史氛围的营造和历史感受的真实书写达到针砭时弊的艺术目的。剧作家们着意刻画的是“抗战”这一特定环境下生存着的鲜活的“社会性”群像和其他各类极具个性的人物。如《残雾》(老舍)描写国民党政府官僚洗局长,家里专制统治,在外贪权好色,最后上了女汉奸的当而失官被捕。《魔窟》(陈白尘)暴露的是沦陷区“一幅汉奸、卖国贼的群丑图”。立意皆在于讽刺大后方的国民党统治政权内部的污浊社会现象。而《后方小喜剧》《面子问题》通过描画一群在抗战当头,国民政府基层机构中那些不知忧国,只知争个人权势和“面子”的卑琐小人物的可笑和内部争斗,嘲讽了国民党统治下的官僚机构的“问题”人物。《乱世男女》《归去来兮》则把讽刺的锋芒指向知识分子。前者嘲弄了一批由南京逃难至后方的满口空话、大话的“都市的渣滓”,其中包括“无聊文人蒲是今”“冒牌编辑吴秋萍”“洋翻译家苗轶欧”“中国名士王浩然”“女诗人紫波”等等,他们表面上高雅、积极、热情,骨子里却卑琐、冷漠、无知。后者勾画了乔仁山这么一个多所顾虑,略示悲观,看不上别人的行动,自己更懒于行动的俄罗斯式的时代“零余者”形象,尖刻地讽刺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内容和形式自相矛盾的严重分裂和寄生于他们身上的劣根性。尤其是陈白尘的《升官图》,更是以漫画式的戏谑手法,通过两个为躲避官府追捕,而逃到一所古老住宅的强盗的一场臆想式的升官发财黄粱梦,有意识地让群魔登台亮相,自我揭丑相互拨打,以一种虚拟的图景,映射了国民党官僚政治沆瀣一气、弄权作势、大肆捞钱的丑恶。此剧在重庆连演40余场,在上海更是连演100余场,被誉为一部新式的“官场现形记”。所有这些剧作,都有非常强烈的现实指向性和政治批判功能,有些剧作甚至是取材于当时的真实生活。如《魔窟》,作者陈白尘自述就是“取于某报一篇题名叫做《宝山陷落傀儡小剧》的通讯”[6]。这些剧作充分表达了作家们忧愤深广的时代情绪,同时也形象、直观、鲜明地揭示了当时政治权力和社会生活中某些糜烂、腐朽的荒唐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它因为对现实采取了逼真性的模拟因而被广大受众所接受,具备了相当的教育意义和认知功能。
但是在文化表意的深层结构上,我们却不能不注意政治讽刺喜剧的另外一种审美品质,即作品中浸润出的深沉文化思考。作为五四新文化孕养的一代剧作家,尤其是像老舍、丁西林等更是学贯中西的学者型作家,关注民族文化、批判民族文化痼疾,关注“改造国民性”和“传统文化再生”问题,毫无疑问成为他们写作中的一种自觉追求。我们不妨看看讽刺喜剧剧作中的一些具体人物。可以说,他们剧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可以看作一种相对应的文化原型来解读。《结婚进行曲》沿袭了五四时期的文化母题,描写19岁的女青年追求自立而四处碰壁,着重探讨了女性人格独立、社会权利、生存权利的问题。《面子问题》中的佟秘书、佟小姐、投机破产而信口开河的夫妻俩,他们活着似乎就是为争一副能在人前获得尊重的至上的“面子”——中国传统的“面子”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地根植他们的生存理念之中,以至于国难当头、国将不国的大失“面子”也不能动摇他们捍卫个人一己“面子”的决心。《残雾》中的洗老太太、《归去来兮》中的乔妻,无疑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她们毫无政治理想,沉迷于旧有生活模式之中。洗老太太恪守“夫贵妻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哪个局长没有个三妻四妾的?”的生活信条;乔妻对“夫权”的自觉臣服,虽然家庭行将分崩离析,仍不做抗争,还从传统伦理法则出发规劝乔仁山娶妻生子延续香火。洗老太太和乔妻在传统伦理道德层面上是勾连在一起的。而作为“夫权”体系的强势一极,洗局长和乔绅无疑是传统伦理威权的象征性书写,他们浓缩了男权社会的所有因素,独断专行、野蛮霸道,享受“性别政治”赋予的绝对权威。(www.daowen.com)
在这些剧作中,作家对文化问题的探讨往往是与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的。如果说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造成了政治叙事对文化叙事的某种潜抑,从而使某些剧本当中的文化叙事成为一种隐逸性叙事文本,容易给我们的解读带来某种疏忽的话,那么,在他们的另外一些作品中,文化视角的审美观照却是被取了近景。如《大地龙蛇》,老舍就是应东方文化协会之邀,以“东方文化”为叙写构架创作的一部作品。通过熟读孔孟的赵庠琛先生一家从抗战后期到20年后的生活故事,把抗战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东方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连接在一起。虽然这部戏结构比较单一,人物设计也多有理念化的成分(似乎是代表某种文化、伦理的傀儡),但是在运用文化视角观照历史与现实,文化意识与政治意识的融合方面还是有明显表现的。尤其是《归去来兮》和丁西林的《妙峰山》,更是在一种文化的注视与关怀中,对讽刺喜剧题材的一次开拓与创造。前者原拟名《新罕穆烈特》(今译“哈姆雷特”),借喻莎士比亚笔下西方文学的不朽典型,指涉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的年青一代废物,颇具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意味。后者则营造了一个身兼留学生、大学教授和山大王多重身份的王老虎形象,寄托着作者把传统的侠义文化与英国式的豁达、幽默的绅士风度结合起来,以建立现代中国人的新风范的人文理想。不管我们怎么评价作者们的文化观点,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作品留给我们的文化启悟是深远的,有些问题比如东西文化比较和传统文化的出路问题甚至在今天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政治和文化的双重视角构成了抗战前期到40年代政治讽刺喜剧的复合叙事结构和本体特征。在以上的分析中,本文只是为了论述的方便,才把它们归纳为结构上的二重性。实际上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政治”与“文化”并不是互为表里或截然对立的,就两者的关系而言,正如前文所述,政治和文化作为人类体现自身存在,实现自己终极目的的一种实践形态,具有内在同一性。政治是文化的一种存在形式。就像马克思分析的那样,它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7]。而从政治讽刺喜剧的文本构成上看,却是以视点互渗方式来达到两者融合的,政治是文化的合理延伸,文化是政治的深化和拓展。政治因为文化的渗入,获得了历史的厚重感;文化因为依附于政治,才变得真实具体和富有现实感。正是因为采取了政治和文化双重观照的方式,抗战前期到40年代的政治讽刺喜剧,才能在准确表现当时社会政治生活,尊重时代审美需要,受到广大民众欢迎的同时,进一步在更为广泛的文化时空中表达了对人类自身真实生存处境的热切关注,抵达了黑格尔所说的“人类普遍的精神旨趣”的审美高度。这一点我们不难从作品的具体分析中看出。而就作品所达到的艺术成就来看,我认为正是政治和文化视点的双重观照,才使得政治讽刺喜剧逃离了后来文学史“重写”派对政治文本的清洗,得以重新进入我们的批评视野。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