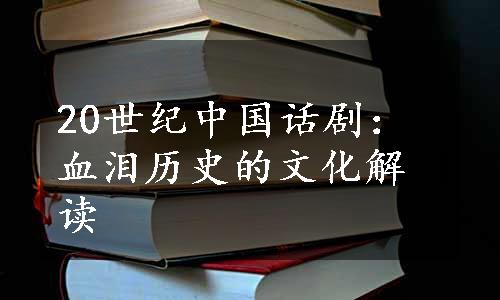
在《雷雨·序》中,曹禺说,起初有了《雷雨》模糊影像时,逗起他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和一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但“写到末了,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1]曹禺前期创作对人的生命、对人类命运进行着紧张而痛苦的思考,甚至乐于使用乌托邦式的宗教情绪去审阅人的生活,但他并没有割断人与其生活着的世界的联系,通过对人生存的这个世界的打量和审视,去发现阻滞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痼疾存在。可以说,曹禺的整个艺术世界,是建构在以人为中心的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之中的,他把悲剧的根系深深地扎进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土壤中,对传统的道德文明给予了决绝的批判。
家族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体系的缩影。“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作他的表层构造。”[2]家族制度最大弊害是家长专制,对尊卑有序男女有别的家庭角色的心理认同,对“人”这个社会主体的个体价值的理性忽视,以及因之而扩张的外力压制。
周朴园是父权、夫权的象征。“他的脸带着多年的世故和劳碌,一种冷峭的目光和偶然在嘴角逼出的冷笑,看出他平日的专横、自私和倔强。”[3]为了将家庭成员纳入“最圆满、最有秩序”的轨道,他说一不二,苛酷地要求每一个人,从精神上、心灵上折磨着妻子和儿女,扼制他们的人性,窒息他们跳动的心灵。周冲善良、天真而充满幻想,然而在严厉的父亲面前却很懦弱。繁漪是周朴园的妻子,年轻,聪明,不甘于沦为丈夫的附庸、玩偶,即引起周朴园的不满,对她冷落之外,用种种可以利用的伦理标准来钳制她,直至给她扣上“神经病”的帽子,把她“磨成了石头一样的死人”。曾皓家道趋于衰落,已失去周朴园那样的绝对权威,但他仍坚持“以诗礼为不可更改的信条”。“他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缛礼,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4],动辄教训儿孙。儿媳曾思懿是曾家伦理纲常的执行者,当瑞贞不听她的话喝下安胎药时,她勃然变色,声色俱厉地斥责道:“叫她喝,要她喝!她要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曾思懿尽管是女性,但在文化内涵上却是一种男权符号,一种父权符号。
家庭制度表面重视人伦亲情,然而温情脉脉的背后制造的是虚伪、荒谬和淋漓的鲜血。如傅立叶所说:“再没有比家庭小组(指家庭制度——引者)占支配地位的文明社会和宗法社会更虚伪的了。野蛮社会比我们所处的社会更具有血腥味,更富于压迫性,但虚伪毕竟要少一些。”[5]曹禺笔下周朴园们的作恶,并非那样直捷痛快,他们要冠冕堂皇得多,也阴损得多。周朴园“真心”地“关心”繁漪“药喝了没有”,“请大夫来看看”;曾皓死死拉住愫方,却还言不由衷地表白“不肯嫁的女儿,我不是一样养么”。周、曾作为男权代表,对女性而言,带来的是无穷尽的压逼和眼泪。繁漪在这枯井一样的周公馆,闷得透不过气来;愫方在精致而死寂的曾家旧宅磨去青春和朝气,一点点地把世界缩成一颗寂寞的心。在周家、曾家还有焦家(焦阎王固然死了,但那张诡秘的相片却无时无刻不笼罩着剧中每一个人,仇虎对他的相片连开三枪,或许也是一种象征,对其阴魂笼罩的反叛),他们是种种罪恶的制造者、支撑者,尽管他最终去处是隐入历史的黑暗,但他们的力量依然那么强大,以至使所有人特别是女性,陷入孤立无告的悲惨境地。
生命活力的获得是以人对自己生命主体性的拥有为前提的,家庭制度对人的主体性肆意践踏、玷污,生命活力于是被窒息和扭曲。在曹禺剧中,封建家庭子辈形象都有着畏缩、怯弱、无聊、空虚的精神特征。周萍本来并不缺乏年轻人的激情,也不满父亲的专横,正是这一点使他赢得繁漪的爱情,周冲的敬重。然而他“性格上那些粗涩的渣渣经过了教育、提炼,成为精细而优美了”,因此,“在他灰暗的眼神里,你看见了不定、犹豫、怯弱同矛盾。”[6]对繁漪的疏离是他“蛮力”消蚀的表现。半是慑于父亲的威严和所谓道德谴责,半是为着厌倦,他转向单纯善良的四凤;而对一心一意指望他的四凤,他也怯于门第观念不敢负起责任。在无法解决的重重矛盾中,最终只能发出“我够了,我是活厌了的人”的哀叹,饮弹而亡。如果说周萍因精神委靡而异化为“情感和矛盾的奴隶”,焦大星则有着相似的精神历程。他本来体貌不凡,“身体魁伟,亮晶的眼有的是宣泄不出的热情”,[7]但母亲与妻子为他的争斗使他由苦恼而趋于怯弱。焦母在剧中代表着父权,她以挑拨儿子与儿媳的情感来维系自己的威势,焦大星怕极了疼他又控制他的母亲,他想躲开母亲与媳妇的争夺,终究只是白费了半天力气。像这样的男子,对女人来说是“恶”的意义上的好人,他的怯弱恰是最不能原谅的品格。无怪金子轻蔑地称他是一辈子没长大,总是在娘怀里吮咂儿的“孩子”。与周萍、焦大星相比,曾文清身上更具有传统士大夫家庭的烙印,他外表清俊飘逸,谈吐不俗,琴棋书画,茶道养鸽,无一不精,然而他生活在“仿佛生来就该长满鬣须,迈着四方步”的曾家,养成沉滞、懒散的个性。面对真诚爱他的表妹愫方,他不敢表达内心情感,只会躲到一边去吟诵陆游《钗头凤》。他从不敢涉足社会,即使下决心走出家门,外面的风雨一下就把他吓了回来。在安逸、寄生的生活中他已经泡酥了骨头,麻木了神经,就像是养惯了的鸽子,再也飞不动了。在宗法社会里,父(母)辈为了家庭的延续,总是按照家族制度规定的行为准则为子辈们确定人生道路,铸造他们的灵魂,特别是家庭中长子,是家族文化的继承者,被赋予了极大的期望,也承受了更大的压力。周萍、曾文清们除了心甘情愿地放弃独立的意志和人格,满足家族的要求,别无选择。(www.daowen.com)
家族文化不仅肆意扼杀家庭内人的主体生命,而且在更大范围内限制了人的心灵空间和精神视野,使社会各阶层的人性发生着畸形的异化现象。与世家子弟不同,仇虎不属于封建家庭,他是黑暗制度下的受害者和叛逆者,复仇是他向恶势力挑战的特定的方式,然而他的复仇是典型的家族复仇,是以血亲利害为尺度的。按封建伦理,“父之仇,弗与共戴天”(《礼记·曲礼上》),按孔颖达疏:“父是子之天,彼杀己父,是杀己之天,故必报杀之,不可与共处于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父仇子报以行孝道,成了仇虎惟一的生存价值;而仅从家庭立场出发的报复行为具有极大盲目性,很容易违背普通世道人情,表现为非人性的残忍。当仇虎发现焦阎王已死,复仇对象不复存在,便在家族情绪催动下,以“父债子还”为由,残酷地杀害了焦大星和小黑子,以使焦阎王“断子绝孙”。然而这又使他陷进与人类道德本性的冲突之中,导致他的精神分裂,以至最后的毁灭。仇虎激烈的复仇行动最终演变为家族宗法观念的外化,他的反抗愈激烈,愈彻底,表明他受传统的束缚愈深,从而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悖论,文化的悲剧,作品由此达到了令人震惊的历史深度。
家族文化在五四以后新文学作品中受到了解构和颠覆,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遏制人的个体生命、造成人的异化,除古老的宗法家族制度外,还应包括现代都市文明。资本主义突破封建桎梏得到一定程度发展,是一种时代的进步,然而无限制获利的欲望,对物质、金钱的狂热追求,同样会束缚人性的健康伸展,使人在高度物质文明中间迷失了自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货币乃是对个性的普遍颠倒: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的(现实)特性相矛盾的特性。”[8]
曹禺作为一位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不只抨击了传统家庭文明,而且对现代都市文明的非人道性进行了深刻的揭示。与家族文明一样,畸形繁荣的都市文明同样是人性异化的渊薮。《雷雨》中的周朴园在家庭是暴君,在社会则是贪婪凶狠的资本家,他为积攒资本而不择手段,昧着良心故意让承包的江堤出险,淹死200多名小工,为的是从每个小工性命扣下300元钱。这同英国的圈地运动一样充满了灭绝人性的血腥。为了煤矿公司的利益他叫警察开枪打死30名工人;而当周冲指责他不给受伤工人抚恤金,他不屑一顾地训斥道:“现在一般年轻人,跟工人谈谈说两三句不关痛痒同情的话,像是一种很时髦的事情!”这些场景和对话充分显示了人性在金融社会的极端异化。在《日出》中《雷雨》的血缘纠葛已不复存在,代之以人与人残酷的拼斗。从大都市的高级宾馆到宝和下处这人间地狱,到处是颠狂、混乱、挣扎和呼号,一片郁热、紧张和焦虑的气氛。金钱像一个紧箍咒,套在每个人心头,摄去了他们的灵魂。人们在金钱的驱策下,疯狂着、格斗着、奔跑着、厮杀着,人人想尽办法抓钱。潘月亭耍尽伎俩,笼络异己又剪除心患,裁员减薪又虚张声势地加入公债投机,企图逃避破产结局;李石清为了钱,压抑着人的自尊,对有钱人阿谀逢迎,以无聊的凑趣去逗人家高兴。当金钱诱惑和肉体欲望结合到一块时,就会产生光怪陆离的交易:粗俗臃肿的顾八奶奶因为有钱,惹得油头粉面的胡四当她的面首;张乔治因为有钱,就可随心所欲地抛弃妻儿,朝三暮四地向一个又一个女人求婚。金钱在制造种种风流和荣耀故事的同时,也在制造着更多的欺凌和压迫的惨剧,小录事黄省三病入膏肓,还是一天到晚抄写,以图十块二毛五去养活三个孩子,然而这微薄的希望也不能满足,最后竟落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惨境。叔本华说:“欲望按其实质来说就是痛苦”;“如果我们对人生作整体地考察,如果我们只强调它的最基本的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喜剧的意味”。[9]人们对金钱、物质的欲望越是强烈,他也就将承担更大的痛苦。陈白露曾经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新女性,她有过对爱情的憧憬,然而平淡的婚姻生活击碎了她的爱情梦;她走进城市一心追求自由的理想,想扮演强者的角色,但受不住奢华生活的诱惑,她从婚姻的笼中飞出来,却投入更封闭的金丝笼。她讨厌自己的生活,厌恶把自己的青春买走的客人们,但腐朽的生活方式,使她丧失了挣脱牢笼的勇气和能力,在对世界彻底绝望后同自己的青春诀别。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