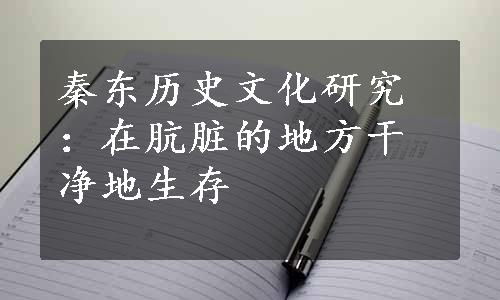
“在肮脏的地方干净地活着”是贾平凹《高兴》后记之一《我和高兴》中所说的。这也正是贾平凹《高兴》所要表达的意思。刘高兴在西安城的困境中迸发出来的顽强精神体现了《高兴》的厚重。流落都市的拾荒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城市中艰难地生存。当生存意味着艰辛,生活体现为痛苦的时候,面对《高兴》,“高兴”从何而来?当然,“贾平凹热爱艺术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艺术具有一般的娱乐功能,不是因为艺术可以给予人以浅层的精神怡悦。贾平凹热爱艺术是因为只有艺术最便于伸展和泄导他的生命意识,使他得到生命体验。他是以生命体验拥抱艺术的。”[5]《高兴》中,“我们”生活的大环境是千年历史文化古城西安,小环境则是肮脏的“破烂世界”。“我们”虽然身处垃圾世界,操持贱业,但“我们”活得踏实、淡然、潇洒而快活。
1.刘高兴:“泥塘里长出来的一枝莲”
在这个喧嚣杂乱物欲横流的社会里,利欲熏心和虚伪必定导致精神的极度贫乏和失落。蝇营狗苟,我们习以为常,沉重的肉身活得高贵而嚣张,灵魂却活得卑劣到龌龊,我们心安理得。“‘重物质,轻精神’,‘一手软,一手硬’,已成了时代的严重偏颇。人类已经因此坠落了自己的生存的境界和人性的品位,并且,由于精神的昏睡,多数的人们对此仍然浑浑噩噩,一无所知。”[6]刘高兴对自我精神方面的某些东西的追求深化了其内涵,他追求的正是被都市人遗弃了的精神层面的东西。“不能有恨,恨了就更难在西安生活。”这是刘高兴说给五福听的,同时也是说给他自己的。要在西安这个大城市生活,不能有恨,要爱!刘高兴真诚地热爱这个城市。他是怀揣着梦想和希望来到西安城的,也曾用畏怯、呆滞的目光打量这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或蹬着三轮车或拉着架子车,走街串巷,提着蛇皮袋子,拿着一把铁钩,一双长满老茧的手,在散发着酸臭味的垃圾桶里,翻翻拣拣,在肮脏的垃圾桶里“刨食”。当刘高兴为捡到的三个空易拉罐而心情愉快的时候,旁边的小孩告诉他,“不要动垃圾,垃圾不卫生”,一个穿着长裙扭动着水蛇腰的漂亮女人经过身边,一边走一边手在鼻子前扇动。然而,垃圾是他们的“粮食”,他们以此为生。是的,垃圾有味不卫生,但拾破烂并不妨碍他们理直气壮、干干净净地活着。正如刘高兴所说:“咱是拾破烂的,咱不能自己也是破烂。”“我刘高兴不是随便的人,我随便了就不是人。”“你瞧那草,大树长它的大树,小草长它的小草,小草不自卑。”他那宽广、坚忍、包容一切的性格,使他“越是活得沉重,也就越懂得轻松,越是活得苦难,他才越要享受着快乐”。刘高兴满脸的汗水,一身的疲惫,卑微如草芥却坚忍地活着。
在底层民众的群体心理上,自然选择传统的民间道德,他们善良、仁爱、诚实、淳朴、讲义气。但是,这些远不足以使他们在生活的重压下自适自足,在他们承受苦难承认命运不可更改的同时,对生活的未来仍然存有微薄而廉价的希望。乐观的心态让他们看淡了生活所带给他们的苦难,从而也理所当然地将那些苦难作为生活本身的一部分去接受。如此一来,生命力即被磨砺得更加坚韧。生命的本真与价值并没有在卑微庸碌中削弱,精神尊严和内心的道德秩序在贫瘠困窘中坚定地维持着。漂泊是行者的宿命,他们在宿命与挣扎中变得坚韧,在坚韧中享受生命的自在与生活的意趣。然而,他们的内心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感伤、落寞与悲凉。刘高兴身上有着中国农民与生俱来的淳朴与善良、豁达与乐观。他说“我刘高兴要高兴着,并不是我就没有烦恼,可你心中有乌鸦在叫也要有小鸟在唱呀”!他坚持哭着过不如笑着活。显然,刘高兴不同于梁晓声笔下的陈奂生,他不是一个沉闷、抑郁、消极等待的观望者。
当生命的尊严和人性的芬芳被世俗物欲不断吞噬的时候,贾平凹却从刘高兴朴素的生存状态中找到了人性中失落的醇芳,进而升华出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高兴》给卑微生命以人性的关爱。刘高兴得不到高兴却依然高兴着。在肮脏的地方,他干净地活着,并且活得纯粹而高贵。他用精神的纯洁来超脱充满宿命的苦难的轮回。刘高兴将卑微如尘的生命活得光彩照人,他让我们在那无尽的垃圾堆里嗅出了人性的芳醇与清香。(www.daowen.com)
2.孟夷纯: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
前面我们说过,刘高兴拾破烂的生活并不妨碍他理直气壮、干净清白地活着,同时也不妨碍他对爱情的向往。刘高兴在清风镇提亲受挫后,吹了三天三夜的箫,大有“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之感。他买了一双高跟鞋,来到西安城里寻找他的爱情。他坚信“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这样高跟鞋在《高兴》里便成了一个浪漫爱情故事的隐喻。高跟鞋象征着优雅、高贵和富裕的生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高跟鞋是刘高兴渴求爱情圆满、生活幸福的慰藉和支撑。刘高兴终于找到了高跟尖头皮鞋的主人——孟夷纯。
孟夷纯是进城打工的另一类,哥哥被人杀害,父亲因此而病死。因为当地穷,想让警察追凶,她必须承担办案经费,所以到西安来打工。她“在饭馆里洗过碗,也做过保姆”,挣来的钱却只能维持她自己的生活。认识美容美发店的老板后,“老板知道了我的遭遇,鼓动我出了台”,挣来的钱,她一次次地寄给了当地的派出所。“明明知道她是妓女,我怎么就要爱上?”刘高兴这个拾荒者爱上了西安城里的女人,他并不鄙视妓女,他肯定孟夷纯的清白,相信她只是处境不好,认为她是污泥里生长出的荷花。
“在小说中她是作为刘高兴的对应物出现的,构成他城市理想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高跟尖头皮鞋’引出并贯穿始终,承载着作者一贯的‘男/女’主人公的情感线索。作者对这一人物塑造也不含任何邪恶成分,反而把她当成观音菩萨的化身,闪烁着纯净高贵的光辉”。[7]她的出现安定了刘高兴那颗压抑着的浮躁的心。“这一次见面,我再一次认定了孟夷纯真是我的菩萨,原来我给她送钱并不是我在帮助她,而是她在引渡我”。锁骨菩萨是做妓的,菩萨又都是圣洁的,孟夷纯在刘高兴心中正是那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