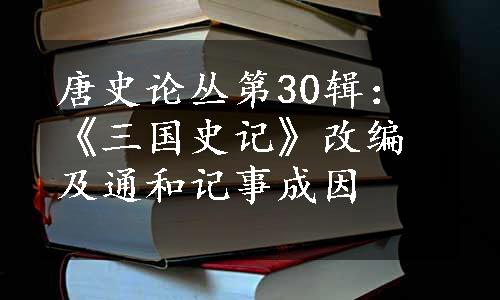
上引《隋书·百济传》中,被直线划出的部分是本文讨论的重点—百济“通和”高句丽的记事。这段记事被系于大业三年(607)之下,内容说百济威德王扶余璋“请兵”隋朝的同时,暗自与高句丽“通和”,且不怀好意,窥伺隋朝。窥伺隋朝的目的是什么,史无记载。根据当时的背景,很有可能指窃取隋朝关于对高句丽作战的情报。如此描述之下,百济俨然成了一个背叛者,但这是历史事实吗?
金富轼编撰《三国史记》的时候,应该对这段记事的可信度有过踌躇,他将此记事和其他相关记事做了重新编排,大致有以下三点调整:
其一,《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百济武王八年三月条”,虽然比较完整地抄录了《隋书·百济传》“大业三年条”的内容,但唯独没有抄录“通和”记事。
其二,“通和”记事被编入《三国史记》卷二〇“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三年(612)条七月条”之下,其文曰:
(隋军)至萨水,军半济,我军自后击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不可禁止。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渌水,行四百五十里。将军天水王仁恭为殿,击我军,却之。来护儿闻(宇文)述等败,亦引还。唯卫文升一军独全。初,九军度辽,凡三十万五千。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失亡荡尽。帝大怒,锁系述等,癸卯引还。初,百济王璋遣使请讨高句丽,帝使之觇我动静,璋内与我潜通。隋军将出,璋使其臣国智牟入隋请师期,帝大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告以期会。及隋军渡辽,百济亦严兵境上,声言助隋,实持两端。[17]
波浪线部分同样抄自《隋书·百济传》,相关分析下文详述。
其三,《隋书·百济传》的波浪线部分被分拆成两条,分别系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相应的年份之下,即《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十二年(611)二月条”:
遣使入隋朝贡。隋炀帝将征高句丽,王使国智牟入请军期。帝悦,厚加赏赐,遣尚书起部郎席律来,与王相谋。[18]
以及《三国史记》卷二七“百济武王十三年(612)条”:
隋六军度辽,王严兵于境,声言助隋,实持两端。[19]
为了更加清晰地表示《三国史记》和《隋书·百济传》的承袭关系,笔者特加了对应记号,以下再以表格的形式归纳整理,如示:
《三国史记》改编《隋书·百济传》记事对照表(www.daowen.com)
波浪线前半部分记述,611年隋朝即将出兵高句丽之际,百济武王再次派出使节,向隋朝问定军期。隋炀帝派出尚书起部郎席律赴百济商议。首先,假使隋朝方面在607年掌握百济“通和”高句丽的情报,那么不可能再在611年派人去和百济商量,所以“通和”记事出现在《隋书·百济传》“大业三年(607)”之下是不合理的。金富轼应该察觉到其中的不合理性,才没有将其录于《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因此,可以判定“通和”记事属于事后追述。
其次,隋朝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有可能得知百济“通和”高句丽呢?日本学者井上直树提出了一种假说:607年隋朝使节裴世清出访倭国,根据《元兴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所引“丈六佛光背铭”可知,他曾暂住飞鸟寺(又名法兴寺、元兴寺)。当时,高句丽僧慧慈、百济僧慧聪都活跃在倭国的政治舞台上,裴世清或许通过高句丽僧和百济僧的交谈,察觉到百济“通和”高句丽,回国后将此情况做了汇报[20]。裴世清大概在608年年末回到隋朝,假使这个时候隋朝朝廷得知百济“通和”高句丽,那么和上述情况一样,不可能再在611年派出使者。于是,比较合理的推断应该是,隋朝不早于611年得知“通和”消息。
波浪线后半部分记述,隋朝大军渡过辽河,准备向高句丽发起进攻。这个时候,百济“严兵于境”,即陈兵不前。百济既然和隋约定军期,便有义务配合隋军出兵高句丽。事实上,百济确实做好了战争动员,但是为何陈兵不前呢?
众所周知,隋炀帝612年第一次征讨高句丽的结果是惨败。仅以上引史料来看,隋将宇文述率领的主力“九军”三十余万人,逃回辽东城者只有近三千,来护儿率领的水军精兵四万余众,最后生还者不过千人。试想,面对隋军兵败如山倒的局面,百济选择陈兵守境,不贸然进军,这难道不是合理的行为吗?杨昭全、何彤梅共著的《中国—朝鲜·韩国关系史》对百济从请战、助战终至观战的原因提出了以下两点意见:第一,对隋击败高句丽没有信心;第二,担心贸然北上助隋,恐遭新罗乘机进兵[21]。笔者以为,这两点意见甚为中肯。
正是因为百济囿于自保、弃隋不顾的行为,引起了隋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隋炀帝的震怒。盛怒之下,隋炀帝怀疑百济声称助隋伐丽,其实是“实持两端”。所谓“实持两端”,即又“通和”隋,又“通和”高句丽。“通和”记事的本源应该就是出自这种“实持两端”的认识。换而言之,“通和”记事不是对客观事实的记述,它是中国方面对百济陈兵不前的一种解读。那么,如此解读的主体,是隋朝的最高执政者隋炀帝,还是《隋书》的编撰者呢?笔者以为,两者皆是。
隋炀帝如此解读,与征讨高句丽失败有关。第一次征伐高句丽时,隋朝动员了一百余万兵士,后勤补给人员更是翻倍。有学者研究认为,隋炀帝对高句丽的这场战争追求的是“不战而胜”(必胜而后战)[22]。所以,他邀请突厥启民可汗随行,想要借此夸耀隋朝的国威。在战略安排上,从第一军开拔到全军出师,总共花费四十天。如此声势浩大的军事行动,何需百济窥伺?隋朝出兵征讨高句丽这事,在当时谁人不知、何人不晓?结果,隋朝战败。自尊心极度受挫的隋炀帝,之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征讨高句丽。在清算战败责任方面,隋炀帝首先处死了尚书右丞刘士龙,因为他没有识破高句丽大将乙支文德的诈降。其次,把领兵将军宇文述、于仲文等削为平民。这些行为都表示出隋炀帝自己拒绝承担战败责任。假使百济“通和”高句丽确有其事,难以想象凭隋炀帝的性格会对此毫不责罚。相反,正因为没有惩罚措施,说明“通和”不过是隋炀帝个人的揣测。其目的,或为了宣泄情绪,或为了转移视听,甚至或有推卸战败责任的可能性。
唐人如此解读,与灭亡百济有关。悉知,唐朝是在新罗的请求之下,出兵灭了百济。虽然唐朝作为朝鲜半岛三国的宗主国,肩负调停并稳定半岛局势的责任和义务,但在法理上欠缺出兵百济的正义性。假如先朝史书中的百济形象是一个暗中“通和”高句丽且窥伺中国的“间谍”,那么唐朝军事打击百济的“道义”便可以彰显。而且,反映唐人对百济武王扶余璋印象的《旧唐书·百济传》,也描写他“虽外称顺命,内实相仇如故”[23],这与“通和”记事所述“璋内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可谓如出一辙。因此,唐人完全有可能把当代的意图和印象投射到前代,从而影响了对隋丽战争中百济陈兵不前一事的理解。
综合上述两点,“通和”记事的出现应该经历了这样一段过程:611年,隋炀帝派出席律赴百济商定军期的时候,仍还相信在百济的配合之下,对高句丽的战争将会非常顺利。612年,隋军大败,同时隋炀帝得知百济陈兵国境,没有出力相助。由是,他把百济的这个行为解读成与高句丽“通和”,即所谓“实持两端”。隋炀帝的这个揣测应该被记录在了隋代的起居注或实录之中。等到唐代史官修撰《隋书》的时候,基于当时的现实需要,不仅认可隋炀帝的判断,而且在607年百济使者王孝邻“请兵”的记事之后,特意点明“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以示其“狡诈”。
“通和”记事的出现—尤其是被系于607年,完全解构了百济“亲隋”的正面形象。后代学者读来,不仅怀疑百济早在598年第一次“请兵”隋朝的时候就已“通和”高句丽,而且容易得出百济最后灭亡完全是咎由自取的结果。然而,这不是当时济丽关系的真实写照。历史的书写,总是以支配者的意志示人,本文讨论的“通和”记事,即属此类。
最后,让我们回到金富轼《三国史记》改编《隋书·百济传》的问题。如果说金富轼在《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百济武王八年三月条”中删除“通和”记事,表现了他对这段记述的不信,那么把“通和”记事系于《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婴阳王二十三年七月条”之下,则表现了他认为“通和”记事应该出现的时间点。上文已述,隋炀帝得知百济陈兵不前的时间,不早于612年的隋丽战争,所以“通和”记事的出现也应该不早于612年。因此,金富轼对《隋书·百济传》的改编,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剖析这段记事的性质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