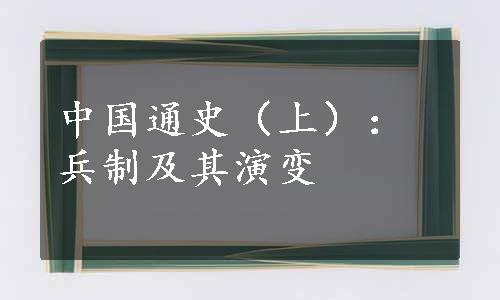
中国的兵制,约可分为八期。
第(一)期,在古代,有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征服之族,全体当兵,被征服之族则否,是为部分民兵制。
第(二)期,后来战争剧烈了,动员的军队多,向来不服兵役的人民,亦都加入兵役,是为全体皆兵制。
第(三)期,天下统一了,不但用不着全体皆兵,即一部分人当兵,亦觉其过剩。偶尔用兵,为顾恤民力起见,多用罪人及降服的异族。因此,人民疏于军事,遂招致降服的异族的叛乱,是即所谓五胡乱华。而中国在这时代,因乱事时起,地方政府擅权,中央政府不能驾驭,遂发生所谓州郡之兵。
第(四)期,五胡乱华的末期,异族渐次和中国同化,人数减少,而战斗顾甚剧烈,不得已,乃用汉人为兵。又因财政艰窘,不得不令其耕以自养。于是又发生一种部分民兵制,是为周、隋、唐的府兵。
第(五)期,承平之世,兵力是不能不腐败的。府兵之制,因此废坏。而其时适值边方多事,遂发生所谓藩镇之兵。因此引起内乱。内乱之后,藩镇遍于内地,唐室卒因之分裂。
第(六)期,宋承唐、五代之后,竭力集权于中央。中央要有强大的常备军。又觑破兵民分业在经济上的利益。于是有极端的募兵制。
第(七)期,元以异族,入主中原,在军事上,自然另有一番措置。明朝却东施效颦。其结果,到底因淤滞而败。
第(八)期,清亦以异族入主,然不久兵力即腐败。中叶曾因内乱,一度建立较强大的陆军。然值时局大变,此项军队,应付旧局面则有余,追随新时代则不足。对外屡次败北。而国内的军纪,却又久坏。遂酿成晚清以来的内乱。直至最近,始因外力的压迫,走上一条旷古未有的新途径。
以上用鸟瞰之法,揭示一个大纲。以下再逐段加以说明。
第(一)期的阶级制度,看第四、第八两章,已可明白。从前的人,都说古代是寓兵于农的,寓兵于农,便是兵农合一,井田既废,兵农始分,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寓兵于农,乃谓以农器为兵器,说见《六韬·农器篇》。古代兵器是铜做的,农器是铁做的。兵器都藏在公家,临战才发给(所谓授甲、授兵),也只能供给正式军队用,乡下保卫团一类的兵,是不能给与的。然敌兵打来,不能真个制梃以自卫。所以有如《六韬》之说,教其以某种农器,当某种兵器。古无称当兵的人为兵的,寓兵于农,如何能释为兵农合一呢?江永《群经补义》中有一段,驳正此说。他举《管子》的参国伍鄙,参国,即所谓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和高子、国子,各帅五乡。伍鄙,即三十家为邑,十邑为卒,十卒为乡,三乡为县,十县为属,乃所以处农人(案所引《管子》,见《小匡篇》)。又引阳虎欲作乱,壬辰戒都车,令癸巳至(案见《左氏》定公八年)。以证兵常近国都。其说可谓甚精。案《周官》夏官序官: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大司徒,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则六军适出六乡。六乡之外有六遂,郑《注》说:遂以军法如六乡。其实乡列出兵法,无田制,遂陈田制,无出兵法,郑《注》是错误的(说本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司马法非周制说》)。六乡出兵,六遂则否,亦兵在国中之证。这除用征服之族居国,被征服之族居野,无可解释。或谓难道古代各国,都有征服和被征服的阶级吗?即谓都有此阶级,亦安能都用此治法,千篇一律呢?殊不知(一)古代之国,数逾千百,我们略知其情形的,不过十数,安知其千篇一律?(二)何况制度是可以互相模仿的。世既有黩武之国,即素尚平和之国,亦不得不肆力于军事组织以相应,既肆力于军事组织,其制度,自然可以相像的。所以虽非被征服之族,其中的军事领袖及武士,亦可以逐渐和民众相离,而与征服之族,同其位置。(三)又况战士必须讲守御,要讲守御,自不得不居险;而农业,势不能不向平原发展;有相同的环境,自可有相同的制度。(四)又况我们所知道的十余国,如求其根源,都是同一或极相接近的部族,又何怪其文化的相同呢?所以以古代为部分民兵制,实无疑义。
古代之国,其兵数是不甚多的。说古代军队组织的,无人不引据《周官》。不过以《周官》之文,在群经中独为完具罢了。其实《周官》之制,是和他书不合的。案《诗经·鲁颂》:“公徒三万”,则万人为一军。《管子·小匡篇》说军队组织之法正如此(五人为伍,五十人为小戎,二百人为卒,二千人为旅,万人一军)。《白虎通义·三军篇》说:“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亦以一军为本万人。《说文》以四千人为一军,则据既加二千人后立说。《谷梁》襄公十一年,“古者天子六师,诸侯一军”(这个军字,和师字同义。变换其字面,以免重复,古书有此文法),一师当得二千人。《公羊》隐公五年何《注》:“二千五百人称师,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五百”两字必后人据《周官》说妄增。然则古文家所说的军队组织,较今文家扩充了,人数增多了。此亦今文家所说制度,代表较早的时期,古文家说,代表较晚的时期的一证。当兵的一部分人,居于山险之地,山险之地,是行畦田之制的,而《司马法》所述赋法,都以井田之制为基本,如此,当兵的义务,就扩及全国人了。《司马法》之说,已见第八章,兹不再引。案《司马法》以终十为同,同方百里,同十为封,封十为畿,畿方千里。如前一说:一封当得车千乘,士万人,徒二万人;一畿当得车万乘,士十万人,徒二十万人。后一说: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外,定出赋的六千四百井,所以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一封有戎马四千匹,兵车千乘。一畿有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见于《汉书·刑法志》。若计其人数,则一同七千五百,一封七万五千,一畿七十五万。《史记·周本纪》说:牧野之战,纣发卒七十万人,以拒武王;《孙子·用间篇》说:“内外骚动,殆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都系本此以立说。《司马法》之说,固系学者所虚拟,亦必和实际的制度相近。春秋时,各国用兵,最多不过数万。至战国时,却阬降斩级,动以万计。此等记载,必不能全属子虚,新增的兵,从何处来呢?我们看《左氏》成公二年,记齐顷公鞍战败北逃回去的时候,“见保者曰:勉之,齐师败矣”,可见其时正式的军队虽败于外,各地方守御之兵仍在。而《战国策》载苏秦说齐宣王之言,说“韩魏战而胜秦,则兵半折,四境不守;战而不胜,国以危亡随其后”;可见各地方守御之兵,都已调出去,充作正式军队了。这是战国时兵数骤增之由。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全国皆兵的,怕莫此时若了。
秦汉统一以后,全国皆兵之制,便开始破坏。《汉书·刑法志》说:“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汉官仪》(建武七年)说:“高祖令天下郡国,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立秋后讲肄课试。”则汉兵制实沿自秦。《汉书·高帝纪》注引《汉仪注》(二年)说:“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昭帝纪注》引如淳说(元凤四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是为卒更。贫者欲得雇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此为秦汉时人民服兵役及戍边之制。法虽如此,事实上已不能行。晁错说秦人谪发之制,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见《汉书》本传),此即汉世所谓七科谪(见《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注》引张晏说)。二世时,山东兵起,章邯亦将骊山徒免刑以击之。则用罪人为兵,实不自汉代始。汉自武帝初年以前,用郡国兵之时多,武帝中年以后,亦多用谪发。此其原因,乃为免得扰动平民起见。《贾子书·属远篇》说:“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十里而至。秦输将起海上,一钱之赋,十钱之费弗能致。”此为古制不能行的最大原因。封建时代,人民习于战争,征戍并非所惧。然路途太远,旷日持久,则生业尽废。又《史记·货殖传》说,七国兵起,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则当时从军的人,所费川资亦甚巨。列侯不免借贷,何况平民?生业尽废,再重以路途往来之费,人民在经济上,就不堪负担了。这是物质上的原因。至于在精神上,小国寡民之时,国与民的利害,较相一致,至国家扩大时,即不能尽然,何况统一之后?王恢说战国时一代国之力,即可以制匈奴(见《汉书·韩安国传》)。而秦汉时骚动全国,究竟宣元时匈奴之来朝,还是因其内乱之故,即由于此。在物质方面,人民的生计,不能不加以顾恤;在精神方面,当时的用兵,不免要招致怨恨;就不得不渐废郡国调发之制,而改用谪发、谪戍了。这在当时,亦有令农民得以专心耕种之益。然合前后而观之,则人民因此而忘却当兵的义务,而各地方的武备,也日益空虚了。所以在政治上,一时的利害,有时与永久的利害,是相反的。调剂于两者之间,就要看政治家的眼光和手腕了。
民兵制度的破坏,形式上是在后汉光武之时的。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七年,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自此各郡国遂无所谓兵备了(后来有些紧要的去处,亦复置都尉。又有因乱事临时设立的。然不是经常、普遍的制度),而外强中弱之机,亦于此时开始。汉武帝置七校尉,中有越骑、胡骑及长水(见《汉书·百官公卿表》。长水,颜师古云:胡名)。其时用兵,亦兼用属国骑等,然不恃为主要的兵力。后汉光武的定天下,所靠的实在是上谷渔阳的兵,边兵强而内地弱的机缄,肇见于此。安帝以后,羌乱频仍,凉州一隅,迄未宁静,该地方的羌、胡,尤强悍好斗。中国人好斗的性质,诚不能如此等浅演的降夷,然战争本不是单靠野蛮好杀的事。以当时中国之力,谓不足以制五胡的跳梁,决无此理。五胡乱华的原因,全由于中国的分裂。分裂之世,势必军人专权,专权的军人,初起时或者略有权谋,或则有些犷悍的性质。然到后来,年代积久了,则必入于骄奢淫佚。一骄奢淫佚,则政治紊乱,军纪腐败,有较强的外力加以压迫,即如山崩川溃,不可复止。西晋初年,君臣的苟安、奢侈,正是军阀擅权的结果,五胡扰乱的原因。五胡乱华之世,是不甚用中国人当兵的(说已见第四章)。其时用汉兵的,除非所需兵数太多,异族人数不足,乃调发以充数。如石虎伐燕,苻秦寇晋诸役是。这种军队,自然不会有什么战斗力的(军队所靠的是训练。当时的五胡,既不用汉人做主力的军队,自然无所谓训练。《北齐书·高昂传》说:高祖讨尔朱兆于韩陵,昂自领乡人部曲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纯将汉儿,恐不济事,今当割鲜卑兵千余人,共相参杂,于意如何?”昂对曰:“敖曹所将部曲,练习已久,前后战斗,不减鲜卑。今若杂之,情不相合。愿自领汉军,不烦更配。”高祖然之。及战,高祖不利,反借昂等以致克捷。可见军队只重训练,并非民族本有的强弱)。所以从刘石倡乱以来,至于南北朝之末,北方的兵权,始终在异族手里。这是汉族难于恢复的大原因。不然,五胡可乘的机会,正多着呢,然则南方又何以不能乘机北伐?此则仍由军人专横,中央权力不能统一之故。试看晋朝东渡以后,荆、扬两州的相持,宋、齐、梁、陈之世,中央和地方政府互相争斗的情形,便可知道。
北强南弱之势,是从东晋后养成的。三国以前,军事上的形势,是北以持重胜,南以剽悍胜。论军队素质的佳良,虽南优于北,论社会文明的程度,则北优于南,军事上胜败的原因,实在于此。后世论者,以为由于人民风气的强弱,实在是错误的(秦虽并六国,然刘邦起沛,项籍起吴,卒以亡秦,实在是秦亡于楚。所以当时的人,还乐道南公“亡秦必楚”之言,以为应验。刘项成败,原因在战略上,不关民气强弱,是显而易见的。吴楚七国之乱,声势亦极煊赫,所以终于无成,则因当时天下安定,不容有变,而吴王又不知兵之故。孙策、孙权、周瑜、鲁肃、诸葛恪、陆逊、陆抗等,以十不逮一的土地人民,矫然与北方相抗,且有吞并中原之志,而魏亦竟无如之何,均可见南方风气的强悍)。东晋以后,文明的重心,转移于南,训卒厉兵,本可于短期间奏恢复之烈。所以终无成功,而南北分裂,竟达于二百六十九年之久,其结果且卒并于北,则全因是时,承袭汉末的余毒,(一)士大夫衰颓不振,(二)军人拥兵相猜,而南方的政权,顾全在此等北来的人手中之故。试设想:以孙吴的君臣,移而置之于东晋,究竟北方能否恢复?便可见得。“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无怪杜甫要对吕蒙营而感慨了。经过这长时期的腐化,而南弱的形势遂成。而北方当是时,则因长期的战斗,而造成一武力重心。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一条,说周、隋、唐三代之祖,皆出武川,可见自南北朝末至唐初,武力的重心,实未曾变。案五胡之中,氐、羌、羯民族皆小,强悍而人数较多的,只有匈奴、鲜卑。匈奴久据中原之地,其形势实较鲜卑为佳。但其人太觉凶暴,羯亦然。被冉闵大加杀戮后,其势遂衰。此时北方之地,本来即可平靖。然自东晋以前,虎斗龙争,多在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数省境内。辽宁、热、察、绥之地,是比较安静的。鲜卑人休养生息于此,转觉气完力厚。当时的鲜卑人,实在是乐于平和生活,不愿向中原侵略的,所以北魏平文帝、昭成帝两代,都因要南侵为其下所杀(见《魏书·序纪》)。然到道武帝,卒肆其凶暴,强迫其下,侵入中原(道武帝伐燕,大疫,群下咸思还北。帝曰:“四海之人,皆可与为国,在吾所以抚之耳,何恤乎无民?”群臣乃不敢复言,见《魏书·本纪》皇始二年。案《序纪》说:穆帝“明刑峻法,诸部民多以违命得罪。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或有室家相携,而赴死所。人问何之,答曰:当往就诛。”其残酷如此。道武帝这话,已经给史家文饰得很温婉的了。若照他的原语,记录下来,那便是“你们要回去,我就要把你们全数杀掉”。所以群臣不敢复言了)。此时割据中原的异族,既已奄奄待毙,宋武帝又因内部矛盾深刻,不暇经略北方,北方遂为所据。然自孝文帝南迁以前,元魏立国的重心,仍在平城。属于南方的侵略,仅是发展问题,对于北方的防御,却是生死问题,所以要于平城附近设六镇,以武力为拱卫。南迁以后,因待遇的不平等,而酿成六镇之乱。因六镇之乱而造成一个尔朱氏,连高氏、贺拔氏、宇文氏等,一齐带入中原。龙争虎斗者,又历五六十年,然后统一于隋。隋、唐先世,到底是汉族还是异族,近人多有辩论。然民族是论文化的,不是论血统的。近人所辩论的,都是血统问题,在民族斗争史上,实在无甚意义。至于隋唐的先世,曾经渐染胡风,也是武川一系中的人物,则无可讳言。所以自尔朱氏之起至唐初,实在是武川的武力,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时代。要到唐贞观以后,此项文化的色彩,才渐渐淡灭(唐初的隐太子、巢剌王、常山愍王等,还都系带有胡化色彩的人)。五胡乱华的已事,虽然已成过去,然在军事上,重用异族的风气,还有存留。试看唐朝用蕃将蕃兵之多,便可明白。论史者多以汉唐并称。论唐朝的武功,其成就,自较汉朝为尤大。然此乃世运为之(主要的是中外交通的进步)。若论军事上的实力,则唐朝何能和汉朝比?汉朝对外的征讨,十之八九是发本国兵出去打的,唐朝则多是以夷制夷。这以一时论,亦可使中国的人民减轻负担,然通全局而观之,则亦足以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之所以蓄意反叛,沙陀突厥之所以横行中原,都由于此。就是宋朝的始终不振,也和这有间接的关系。因为久已柔靡的风气,不易于短时期中训练之使其变为强悍。而唐朝府兵的废坏,亦和其阁置不用,很有关系的。
府兵之制起于周。籍民为兵,蠲其租调,而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分为百府,每府以一郎将主之,而分属于二十四军(当时以一柱国主二大将,一将军统二开府,开府各领一军),其众合计不满五万。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属于诸卫将军。唐制,诸府皆称折冲府。各置折冲都尉,而以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国六百三十四府,在关中的二百六十一府,以为强干弱枝之计。府兵之制:平时耕以自养。战时调集,命将统之。师还则将上所佩印,兵各还其府。(一)无养兵之费,而有多兵之用。(二)兵皆有业之民,无无家可归之弊。(三)将帅又不能拥兵自重。这是与藩镇之兵及宋募兵之制相较的优点,从前的论者多称之。但兵不唯其名,当有其实。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时,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于唐时征讨,多用蕃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其故,乃当时的风气使之,而亦可谓时势及国家之政策使之。兵之精强,在于训练。主兵者之能勤于训练,则在豫期其军队之有用。若时值承平,上下都不以军事为意,则精神不能不懈弛;精神一懈弛,训练自然随之而废了。所以唐代府兵制度的废坏,和唐初时局的承平,及唐代外攘,不甚调发大兵,都有关系。高宗、武后时,业已名存实亡。到玄宗时,就竟不能给宿卫了(唐时宿卫之兵,都由诸府调来,按期更换,谓之“番上”。番即现在的班字)。时相张说,知其无法整顿,乃请宿卫改用募兵,谓之彍骑,自此诸府更徒存虚籍了。(www.daowen.com)
唐初边兵屯戍的,大的称军,小的称城镇守捉,皆有使以主之。统属军,城镇守捉的曰道。道有大总管,后改称大都督。大都督带使持节的,人称之为节度使。睿宗后遂以为官名。唐初边兵甚少。武后时,国威陵替。北则突厥,东北则奚、契丹,西南则吐蕃皆跋扈。玄宗时,乃于边陲置节度使,以事经略。而自东北至西北边之兵尤强。天下遂成偏重之势。安禄山、史思明皆以胡人而怀野心,卒酿成天宝之乱。乱后藩镇遂遍于内地。其中安史余孽,唐朝不能彻底铲除,亦皆授以节度使。诸镇遂互相结约,以土地传子孙,不奉朝廷的命令。肃、代两世,皆姑息养痈。德宗思整顿之,而兵力不足,反召朱泚之叛。后虽削平朱泚,然河北、淮西,遂不能问。宪宗以九牛二虎之力,讨平淮西,河北亦闻风自服。然及穆宗时,河北即复叛。自此终唐之世,不能戡定了。唐朝藩镇,始终据土自专的,固然只有河北,然其余地方,亦不免时有变乱。且即在平时,朝廷指挥统驭之力,亦总不甚完全。所以肃、代以还,已隐伏分裂之势。至黄巢乱后,遂溃决不可收拾了。然藩镇固能梗命,而把持中央政府,使之不能振作的,则禁军之患,尤甚于藩镇。
禁军是唐初从征的兵,无家可归的。政府给以渭北闲田,留为宿卫。号称元从禁军。此本国家施恩之意,并非仗以战斗。玄宗时破吐蕃,于临洮之西置神策军。安史之乱,军使成如璆遣将卫伯玉率千人入援,屯于陕州。后如璆死,神策军之地,陷于吐蕃,乃即以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仍屯于陕,而中官鱼朝恩以观军容使监其军。伯玉死,军遂统于朝恩。代宗时,吐蕃陷长安,代宗奔陕,朝恩以神策军扈从还京。其后遂列为禁军,京西多为其防地。德宗自奉天归,怀疑朝臣,以中官统其军。其时边兵赏赐甚薄,而神策军颇为优厚,诸将遂多请遥隶神策军,军额扩充至十五万。中官之势,遂不可制。“自穆宗以来八世,而为宦官所立者七君。”(《唐书·僖宗纪》赞语,参看《廿二史札记·唐代宦官之祸》条)顺宗、文宗、昭宗皆以欲诛宦官,但或遭废杀,或见幽囚。当时的宦官,已成非用兵力不能铲除之势。然在宦官监制之下,朝廷又无从得有兵力(文宗时,郑注欲夺宦官之兵而败)。昭宗欲自练兵以除宦官而败。召外兵,则明知宦官除而政权将入除宦官者之手,所以其事始终无人敢为。然相持至于唐末,卒不得不出于此一途。于是宦官尽而唐亦为朱梁所篡了。宦官之祸,是历代多有的,拥兵为患的,却只有唐朝(后汉末,蹇硕欲图握兵,旋为何进所杀)。总之,政权根本之地,不可有拥兵自重的人,宦官亦不过其中之一罢了。
禁兵把持于内,藩镇偃蹇于外,唐朝的政局,终已不可收拾,遂分裂而为五代十国。唐时的节度使,虽不听政府的命令,而亦不能节制其军队。军队不满意于节度使,往往哗变而杀之,而别立一人。政府无如之何,只得加以任命。狡黠的人,遂运动军士,杀军帅而拥戴自己。即其父子兄弟相继的,亦非厚加赏赐,以饵其军士不可。凡此者,殆已成为通常之局。所谓“地擅于将,将擅于兵”。五代十国,唯南平始终称王,余皆称帝,然论其实,则仍不过一节度使而已。宋太祖黄袍加身,即系唐时拥立节度使的故事,其余证据,不必列举。事势至此,固非大加整顿不可。所以宋太祖务要削弱藩镇,而加强中央之兵。
宋朝的兵制:兵之种类有四:曰禁军,是为中央军,均属三衙。曰厢军,是为地方兵,属于诸州。曰乡兵,系民兵,仅保卫本地方,不出戍。曰蕃兵,则系异族团结为兵,而用乡兵之法的。太祖用周世宗之策,将厢军之强者,悉升为禁军,其留为厢军者,不甚教阅,仅堪给役而已。乡兵、蕃兵,本非国家正式的军队,可以弗论。所以武力的重心,实在禁军。全国须戍守的地方,乃遣禁军更番前往,谓之“番戍”。昔人议论宋朝兵制的,大都加以诋毁。甚至以为唐朝的所以强,宋朝的所以弱,即由于藩镇的存废。这真是瞽目之谈。唐朝强盛时,何尝有什么藩镇?到玄宗设立藩镇时,业已因国威陵替,改取守势了。从前对外之策,重在防患未然。必须如汉之设度辽将军、西域都护,唐之设诸都护府,对于降伏的部落,(一)监视其行动,(二)通达其情意,(三)并处理各部族间相互的关系。总而言之,不使其(一)互相并吞,(二)坐致强大,是为防患未然。其设置,是全然在夷狄境内,而不在中国境内的,此之谓“守在四夷”。是为上策。经营自己的边境,已落第二义了。然果其士马精强,障塞完固,中央的军令森严,边将亦奉令维谨,尚不失为中策。若如唐朝的藩镇擅土,则必自下策而入于无策的。因为军队最怕的是骄,骄则必不听命令,不能对外而要内讧;内讧势必引外力以为助;这是千古一辙的。以唐朝幽州兵之强,而不能制一契丹,使其坐大;藩镇遍于内地,而黄巢横行南北,如入无人之境,卒召沙陀之兵,然后把他打平;五代时,又因中央和藩镇的内讧,而引起契丹的侵入;都是铁一般强,山一般大的证据。藩镇的为祸为福,可无待于言了。宋朝的兵,是全出于招募的,和府兵之制相反,论者亦恒右唐而左宋,这亦是耳食之谈。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是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其性质,此辈在经济上,即是所谓“无赖”,又其性质,不能勤事生产,欲惩治之、感化之极难。只有营伍之中,规律最为森严,或可约束之,使之改变。此辈性行虽然不良,然苟能束之以纪律,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利用养兵之费,销纳其一部分,既可救济此辈生活上的无赖,而饷项亦不为虚糜。假若一个募兵,在伍的年限,是十年到二十年,则其人已经过长期的训练;裁遣之日,年力就衰,大多数的性质,必已改变,可以从事于生产,变作一个良民了。以经济原理论,本来宜于分业,平民出饷以养兵,而于战阵之事,全不过问,从经济的立场论,是有益无损的。若谓行募兵之制,则民不知兵,则举国皆兵,实至今日乃有此需要。在昔日,兵苟真能御敌,平民原不须全体当兵。所以说募兵之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自有其相当的价值。宋代立法之时,亦自有深意。不过所行不能副其所期,遂至利未形而害已见罢了。宋朝兵制之弊在于:(一)兵力的逐渐腐败。(二)番戍之制:(甲)兵不知将,将不知兵,不便于指挥统驭。(乙)而兵士居其地不久,既不熟习地形,又和当地的人民,没有联络。(丙)三年番代一次,道途之费,却等于三年一次出征。(三)而其尤大的,则在带兵的人,利于兵多,(子)既可缺额刻饷以自肥,(丑)又可役使之以图利。乞免者既不易得许,每逢水旱偏灾,又多以招兵为救荒之策;于是兵数递增。宋开国之时,不满二十二万。太祖末年,已增至三十七万。太宗末年,增至六十六万。真宗末年,增至九十一万。仁宗时,西夏兵起,增至一百二十五万。后虽稍减,仍有一百一十六万。欧阳修说:“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远至吴、楚,莫不尽取以归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重,至于不可复加。”养兵之多如此,即使能战,亦伏危机,何况并不能战,对辽对夏,都是隐忍受侮;而西夏入寇时,仍驱乡兵以御敌呢?当时兵多之害,人人知之,然皆顾虑召变而不敢裁。直至王安石出,才大加淘汰。把不任禁军的降为厢军,不任厢军的免为民。兵额减至过半。又革去番戍之制,择要地使之屯驻,而置将以统之(以第一第二为名,全国共九十一将)。安石在军事上,虽然无甚成就,然其裁兵的勇气,是值得称道的。唯其所行民兵之制,则无甚成绩,而且有弊端。
王安石民兵之法,是和保伍之制连带的。他立保甲之法,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设大保长。五百家为一都保,设都保正副。家有两丁的,以其一为保丁。其初日轮若干人儆盗,后乃教以武艺,籍为民兵。民兵成绩,新党亦颇自诩(如《宋史》载章惇之言,谓“仕宦及有力之家,子弟欣然趋赴,马上艺事,往往胜诸军”之类)。然据《宋史》所载司马光、王岩叟的奏疏,则其(一)有名无实,以及(二)保正长巡检使等的诛求,真是暗无天日。我们不敢说新党的话全属子虚,然这怕是少数,其大多数,一定如旧党所说的。因为此等行政上的弊窦,随处可以发现。民兵之制,必要的条件有二:(一)为强敌压迫于外。如此,举国上下,才有忧勤惕厉的精神,民虽劳而不怨。(二)则行政上的监督,必须严密。官吏及保伍之长,才不敢倚势虐民。当时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不免弊余于利。至于伍保之法,起源甚古。《周官》大司徒说:“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賙。五州为乡,使之相宾。”这原和《孟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意相同,乃使之互相救恤。商君令什伍相司(同伺)连坐,才使之互相稽察。前者为社会上固有的组织,后者则政治上之所要求。此唯乱时可以行之。在平时,则犯大恶者(如谋反叛逆之类),非极其秘密,即徒党众多,声势浩大(如江湖豪侠之类);或其人特别凶悍,为良民所畏(如土豪劣绅之类);必非人民所能检举。若使之检举小恶,则徒破坏社会伦理,而为官吏开敲诈之门,其事必不能行。所以自王安石创此法后,历代都只于乱时用以清除奸宄,在平时总是有名无实,或并其名而无之的(伍保之法,历代法律上本来都有,并不待王安石的保甲,然亦都不能行)。
裁募兵,行民兵,是宋朝兵制的一变。自此募兵之数减少。元祐时,旧党执政,民兵之制又废。然募兵之额,亦迄未恢复。徽宗时,更利其缺额,封桩其饷,以充上供,于是募兵亦衰。至金人入犯,以陕西为著名多兵之地,种师道将以入援,仅得一万五千人而已。以兵多著名的北宋,而其结果至于如此,岂非奇谈?
南渡之初,军旅寡弱。当时诸将之兵,多是靠招降群盗或召募,以资补充的。其中较为强大的,当推所谓御前五军。杨沂中为中军,总宿卫。张俊为前军,韩世忠为后军,岳飞为左军,刘光世为右军,皆屯驻于外。是为四大将。光世死,其军叛降伪齐(一部分不叛的,归于张俊),以四川吴玠之军补其缺。其时岳飞驻湖北,韩世忠驻淮东,张俊驻江东,皆立宣抚司。宗弼再入犯,秦桧决意言和,召三人入京,皆除枢密副使,罢三宣抚司,以副校统其兵,称为统制御前军马。驻扎之地仍旧,谓之某州驻扎御前诸军。四川之兵,亦以御前诸军为号。直达朝廷,帅臣不得节制。其饷,则特设总领以司之,不得自筹。其事略见《文献通考·兵考》。
北族在历史上,是个侵略民族。这是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在地理上,(一)瘠土的民族,常向沃土的民族侵略。(二)但又必具有地形平坦,利于集合的条件。所以像天山南路,沙漠绵延,人所居住的,都是星罗棋布的泉地,像海中的岛屿一般;又或仰雪水灌溉,依天山之麓而建国;以至青海、西藏,山岭崎岖,交通太觉不便;则土虽瘠,亦不能成为侵略民族。历史上侵掠的事实,以蒙古高原为最多,而辽吉二省间的女真,在近代,亦曾两度成为侵略民族。这是因为蒙古高原,地瘠而平,于侵掠的条件,最为完具。而辽吉两省,地形亦是比较平坦的;且与繁荣的地方相接近,亦有以引起其侵略之欲望。北族如匈奴突厥等,虽然强悍,初未尝侵入中国。五胡虽占据中国的一部分,然久居塞内,等于中国的乱民,而其制度亦无足观。只有辽、金、元、清四朝,是以一个异民族的资格,侵入中国的;而其制度,亦和中国较有关系。今略述其事如下。
四朝之中,辽和中国的关系最浅。辽的建国,系合部族及州县而成。部族是他的本族和所征服的北方的游牧民族。州县则取自中国之地。其兵力,亦是以部族为基本的。部族的离合,及其所居之地,都系由政府指定,不能自由。其人民全体皆隶兵籍。当兵的素质,极为佳良。《辽史》称其“各安旧风,狃习劳事,不见纷华异物而迁。故能家给人足,戒备整完。卒之虎视四方,强朝弱附,部族实为之爪牙”,可谓不诬了。但辽立国虽以部族为基本,而其组织军队,亦非全不用汉人。世徒见辽时的五京乡丁,只保卫本地方,不出戍,以为辽朝全不用汉人做正式军队,其实不然。辽制有所谓宫卫军者,每帝即位,辄置之。出则扈从,入则居守,葬则因以守陵。计其丁数,凡有四十万八千,出骑兵十万一千。所谓不待调发州县部族,而十万之兵已具。这是辽朝很有力的常备军。然其置之也,则必“分州县,析部族”。又太祖征讨四方,皇后述律氏居守,亦摘蕃汉精锐三十万为属珊军。可见辽的军队中,亦非无汉人了。此外辽又有所谓大首领部族军,乃亲王大臣的私甲,亦可率之以从征。国家有事,亦可向其量借。又北方部族,服属于辽的,谓之属国,亦得向其量借兵粮。契丹的疆域颇大,兵亦颇多而强,但其组织不坚凝。所以天祚失道,金兵一临,就土崩瓦解。这不是辽的兵力不足以御金,乃是并没有从事于抵御。其立国本无根柢,所以土崩瓦解之后,亦就更无人从事于复国运动。耶律大石虽然有意于恢复,在旧地,亦竟不能自立了。
金朝的情形,与辽又异。辽虽风气敦朴,然畜牧极盛,其人民并不贫穷的。金则起于瘠土,人民非常困穷。然亦因此而养成其耐劳而好侵掠的性质。《金史》说其“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致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可见其侵掠的动机了。金本系一小部族,其兵全系集合女真诸部族而成。战时的统帅,即系平时的部长。在平时称为孛堇,战时则称为猛安谋克。猛安译言千夫长,谋克译言百夫长,这未必真是千夫和百夫,不过依其众寡,略分等级罢了。金朝的兵,其初战斗力是极强的,但迁入中原之后,腐败亦很速。看《廿二史札记·金用兵先后强弱不同》一条,便可知道。金朝因其部落的寡少,自伐宋以后,即参用汉兵。其初契丹、渤海、汉人等,投降金朝的,亦都授以猛安谋克。女真的猛安谋克户,杂居汉地的,亦听其与契丹、汉人相婚姻,以相固结。熙宗以后,渐想把兵柄收归本族,于是罢汉人和渤海人猛安谋克的承袭。移剌窝斡乱后,又将契丹户分散,隶属于诸猛安谋克。世宗时,将猛安谋克户移入中原,其人既已腐败到既不能耕,又不能战,而宣宗南迁,仍倚为心腹,外不能抗敌,而内敛怨于民。金朝的速亡,实在是其自私本族,有以自召之的。总而言之:文明程度落后的民族,与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遇,是无法免于被同化的。像金朝、清朝这种用尽心机,而仍不免于灭亡,还不如像北魏孝文帝一般,自动同化于中国的好。
元朝的兵制,也是以压制为政策的。其兵出于本部族的,谓之蒙古军。出于诸部族的,谓之探马赤军。既入中原后,取汉人为军,谓之汉军。其取兵之法,有以户论的,亦有以丁论的。兵事已定之后,曾经当过兵的人,即定入兵籍,子孙世代为兵。其贫穷的,将几户合并应役。甚贫或无后的人,则落其兵籍,别以民补。此外无他变动。其灭宋所得的兵,谓之新附军。带兵的人,“视兵数之多寡,为爵秩之崇卑”,名为万户、千户、百户。皆分上、中、下。初制,万户、千户死阵者,子孙袭职,死于病者降一等。后来不论大小及身故的原因,一概袭职。所以元朝的军官,可视为一个特殊阶级。世祖和二三大臣定计:使宗王分镇边徼及襟喉之地。河、洛、山东,是他们所视为腹心之地,用蒙古军、探马赤军戍守。江南则用汉军及新附军,但其列城,亦有用万户、千户、百户戍守的。元朝的兵籍,汉人是不许阅看的。所以占据中国近百年,无人知其兵数。观其屯戍之制,是很有深心的。但到后来,其人亦都入洪炉而俱化。末叶兵起时,宗王和世袭的军官,并不能护卫他。
元朝以异族入据中国,此等猜防之法,固然无怪其然。明朝以本族人做本族的皇帝,却亦暗袭其法,那就很为无谓了。明制:以五千六百人为卫。一千一百十二人为千户所,一百十二人为百户所(什伍之长,历代都即在其什伍之人数内,明朝则在其外。每一百户所,有总旗二人,小旗十人,所以共为一百十二人)。卫设都指挥使,隶属于五军都督府。兵的来路有三种:第(一)种从征,是开国时固有的兵。第(二)种归附,是敌国兵投降的。第(三)种谪发,则是刑法上罚令当兵的,俗话谓之“充军”。从征和归附,固然是世代为兵,谪发亦然。身死之后,要调其继承人,继承人绝掉,还要调其亲族去补充的,谓之“句丁”。这明是以元朝的兵籍法为本,而加以补充的。五军都督府,多用明初勋臣的子孙,也是模仿元朝军官世袭之制。治天下不可以有私心。有私心,要把一群人团结为一党,互相护卫,以把持天下的权利,其结果,总是要自受其害的。军官世袭之制,后来腐败到无可挽救,即其一端。金朝和元朝,都是异族,他们社会进化的程度本浅,离封建之世未远,猛安谋克和万户千户百户,要行世袭之制,还无怪其然。明朝则明是本族人,却亦重视开国功臣的子孙,把他看作特别阶级,其私心就不可恕了。抱封建思想的人,总以为某一阶级的人,其特权和权利,既全靠我做皇帝才能维持,他们一定会拥护我。所以把这一阶级的人看得特别亲密。殊不知这种特权阶级,到后来荒淫无度,知识志气都没有了。何谓权利?怕他都不大明白。明白了;明白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了;明白自己的权利,如何才得维持了;因其懦弱无用,眼看着他人抢夺他的权利,他亦无如之何。所谓贵戚世臣,理应与国同休戚的,却从来没有这回事,即由于此。武力是不能持久的。持久了,非腐败不可。这其原因,由于战争是社会的变态而非其常态。变态是有其原因的,原因消失了,变态亦即随之而消失。所以从历史上看来,从没有一支真正强盛到几十年的军队(因不遇强敌,甚或不遇战事,未至溃败决裂,是有的。然这只算是侥幸。极强大的军队,转瞬化为无用,这种事实,是举不胜举的。以宋武帝的兵力,而到文帝时即一蹶不振,即其一例。又如明末李成梁的兵力,亦是不堪一击的,侥幸他未与满洲兵相遇罢了。然而军事的败坏,其机实隐伏于成梁之时,这又是其一例。军队的腐败,其表现于外的,在精神方面,为士气的衰颓;在物质方面,则为积弊的深痼;虽有良将,亦无从整顿,非解散之而另造不可。世人不知其原理,往往想就军队本身设法整顿,其实这是无法可设的。因为军队是社会的一部分,不能不受广大社会的影响。在社会学上,较低的原理,是要受较高的原理的统驭的)。“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无备”,这种思想,亦是以常识论则是,而经不起科学评判的。因为到有事时,预备着的军队,往往无用,而仍要临时更造。府兵和卫所,是很相类的制度。府兵到后来,全不能维持其兵额。明朝对于卫所的兵额,是努力维持的,所以其缺额不至如唐朝之甚。然以多数的兵力,对北边,始终只能维持守势(现在北边的长城,十分之九,都是明朝所造)。末年满洲兵进来,竟尔一败涂地;则其兵力亦有等于无。此皆特殊的武力不能持久之证。
清朝太祖崛起,以八旗编制其民。太宗之世,蒙古和汉人归降的,亦都用同一的组织。这亦和金朝人以猛安谋克授渤海汉人一样。中国平定之后,以八旗兵驻防各处,亦和金朝移猛安谋克户于中原,及元朝镇戍之制,用意相同。唯金代的猛安谋克户,系散居于民间;元朝万户分驻各处,和汉人往来,亦无禁限。清朝驻防的旗兵,则系和汉人分城而居的,所以其冲突不如金元之烈。但其人因此与汉人隔绝,和中国的社会,全无关系,到末造,要筹画旗民生计,就全无办法了。清代的汉兵,谓之绿旗,亦称绿营。中叶以前的用兵,是外征以八旗为主,内乱以绿营为主的。八旗兵在关外时,战斗之力颇强。中国军队强悍的,亦多只能取守势,野战总是失利时居多(洪承畴松山之战,是其一例)。然入关后腐败亦颇速。三藩乱时,八旗兵已不足用了。自此至太平天国兴起时,内地粗觉平安,对外亦无甚激烈的战斗。武功虽盛,实多侥天之幸。所以太平军一起,就势如破竹了。
中国近代,历史上有两种潮流潜伏着。推波助澜,今犹未已,非通观前后,是不能觉悟出这种趋势来的。这两种潮流:其(一)是南方势力的兴起。南部数省,向来和大局无甚关系。自明桂王据云贵与清朝相抗;吴三桂举兵,虽然终于失败,亦能震荡中原;而西南一隅,始隐然为重于天下。其后太平军兴,征伐几遍全国。虽又以失败终,然自清末革命,至国民政府北伐之成功,始终以西南为根据。现在的抗战,还是以此为民族复兴的策源地的。其(二)是全国皆兵制的恢复。自秦朝统一以后,兵民渐渐分离,至后汉之初,而民兵之制遂废,至今已近二千年了。康有为说,中国当承平时代,是没有兵的。虽亦有称为兵的一种人,其实性质全与普通人民无异(见《欧洲十一国游记》)。此之谓有兵之名,无兵之实。旷观历代,都是当需要用兵时,则产生出一支真正的军队来;事过境迁,用兵的需要不存,此种军队,亦即凋谢,而只剩些有名无实的军队,充作仪仗之用了。此其原理,即由于上文所说的战争是社会的变态,原不足怪。但在今日,帝国主义跋扈之秋,非恢复全国皆兵之制,是断不足以自卫的。更无论扶助其他弱小民族了。这一个转变,自然是极艰难。但环境既已如此,决不容许我们的不变。当中国和欧美人初接触时,全未知道需要改变。所想出来的法子,如引诱他们上岸,而不和他在海面作战;如以灵活的小船,制他笨重的大船等;全是些闭着眼睛的妄论。到咸同间,外患更深了。所谓中兴将帅,(一)因经验较多,(二)与欧美人颇有相当的接触。才知道现在的局面,非复历史上所有。欲图适应,非有相当的改革不可。于是有造成一支军队以适应时势的思想。设船政局、制造局,以改良器械;陆军则改练洋操;亦曾成立过海军;都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即至清末,要想推行征兵制,其实所取的办法,离民兵之制尚远,还不过是这种思想。民国二十余年,兵制全未革新,且复演了历史上武人割据之局。然时代的潮流,奔腾澎湃,终不容我不卷入旋涡。抗战以来,我们就一步步地,走入举国皆兵之路了。这两种文化,现在还在演变的中途,我们很不容易看出其伟大。然在将来,作历史的人,一定要认此为划时代的大转变,是毫无可疑的。这两种文化,实在还只是一种。不过因为这种转变,强迫着我们,发生一种新组织,以与时代相适应,而时代之所以有此要求,则缘世界交通而起。在中国,受世界交通影响最早的是南部。和旧文化关系最浅的,亦是南部,受旧文化的影响较浅,正是迎受新文化的一个预备条件。所以近代改革的原动力,全出于南方;南方始终代表着一个开明的势力(太平天国虽然不成气候,湘淮军诸首领,虽然颇有学问,然以新旧论,则太平天国,仍是代表新的,湘淮军人物,仍是代表旧的。不过新的还未成熟,旧的也还余力未尽罢了)。千回百折,似弱而卒底于有成。
几千年以来,内部比较平安,外部亦无真正大敌。因此,养成中国(一)长期间无兵,只有需要时,才产生真正的军队;(二)而这军队,在全国人中,只占一极小部分。在今日,又渐渐地改变,而走上全国皆兵的路了。而亘古未曾开发的资源,今日亦正在开发。以此广大的资源,供此众多民族之用,今后世界的战争,不更将增加其惨酷的程度么?不,战争只是社会的变态。现在世界上战争的惨酷,都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这亦是社会的一个变态,不过较诸既往,情形特别严重罢了。变态是决不能持久的。资本的帝国主义,已在开始崩溃了。我们虽有横绝一世的武力,大势所趋,决然要用之于打倒帝国主义之途,断不会加入帝国主义之内,而成为破坏世界和平的一分子。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