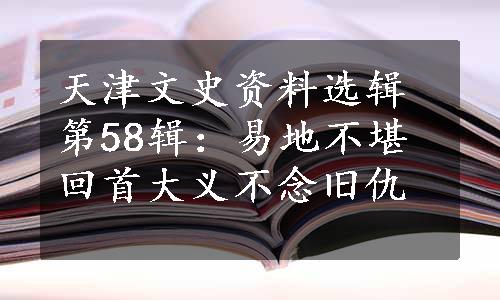
1949年5、6月的一天早饭后,李所长到监室,要我立即收拾好行李跟他下楼,这时我的伙食已改为一般犯人的标准,因此我猜疑可能要对我进行公审,或许会拉出去枪毙。在收拾行李时,不自觉地流露出紧张的神情,李所长看出我慌张的样子笑着说:“你又在瞎想啥!现在给你换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免得你成天捉臭虫。”下楼后让我上了一辆有窗帘的小汽车,行车约10分钟停下,我走出定睛一看,正停在解放前稽查处看守所后院的大门口,李所长说:“跟我来!”这时我思想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谁能料到,我原先关押犯人的地方,今天我要被关押在这里!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踏上看守所大门的台阶时,顷刻间回忆起半年前我检查看守所的情景:那时陪同的有督察长、科长、看守所长,进大门时两旁的警卫立正行军礼。走进监室大门后,由于关押的人犯超员,走廊内臭气熏天,我用手绢捂着嘴,快步从楼下走到楼上环绕一周。偶尔听到监室房门上的小窗口有人连喊:“长官!我来了几个月还没过堂,我冤枉啊!”我带着似乎发慈悲的语调,转身告知司法科长,应查查是什么案子,羁押的案子必须按办案程序及时尽快结案移送,绝不能拖延。司法科长无可奈何地说:“送来的案子居多证据不足,只能催促送案单位提供证据,因此拖延了时间。”
正当我回味着过去,李所长说:“进来吧,就住这间房子。”我仔细一看,是楼下走廊尽头最大的一个监室。进去后地板擦得锃亮,四周墙壁粉刷得雪白,门的对面墙上有带铁丝网的两个窗户,光线充足还较清爽。在我铺床位时又送来二人,经过互相了解,一位是班志洲,安徽人,中统分子,1947年曾任党通局(即中统)天津区副区长,1948年任华北剿总联合秘书处秘书。另一人是1945年日降后天津市首任市长张廷谔之侄张树德,张的爱人是中共前辈江韵清之女。解放前该张与中共地工有联系,解放后因在接收工作中手续欠清被关押。张有鸦片嗜好,经常卧床,精神不振,不多日后调走。该室一连送进5人,有戴笠生前的随身副官贾金南。1946年初戴在北平将贾特意留在南京为其布置住房,同年3月17日戴乘飞机南去失事后,贾一直在南京守灵,1947年贾调任平津铁路局警务处天津警务段段长至解放。有军统电讯特务舒季衡(又名舒宝铨)。该舒原在国民党海军及招商轮充当过电台报务员。抗战初期在武汉参加军统组织,先后在军统局湖北站、长沙电讯总台、军统局浙江站任过站台报务员。1941年间被军统派遣潜入日占区天津,建立军统局天津独立潜伏电台,自任台长。舒妻徐爱莲担任译电、交通。1946年任国民党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专门委员。该局撤销后筹建“天津华声广播电台”,自任经理。有解放前天津《中华日报》社社长齐协民(中统分子)。有天津市警察局副局长王清溪(王曾留学法国学警察)。有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直属通讯员吕一民。当时政府将我们7人编为一个“改造小组”,指定我为小组长。这以后的活动是这样的:每日读读报纸,谈谈认识,此外通过互相启发,写写交待问题的材料。
这个新的看守所所有监室内无厕所,室内放一粗瓷尿桶,每日早、晚由警卫监视,各监室挨次上厕所一次。有一天早上各监室轮流上厕所时,对面女监室的一个女犯乘警卫不注意,偷偷从我们监室的小窗口上丢进一个纸卷,经别人拾起一看,是写给我的,于是递交给我。我仔细一看,开头称呼我为“李站长”,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她叫商××,是保密局天津站学运组组员,近来每晚深夜××年龄较大的看守人员,不断溜进室内对她调戏,并说如依从他,可得到从轻处理,她还是少女不能受此污辱,请设法对她营救。我看完后虽然对该女非常生疏,但不论怎样在共产党的监狱里,竟然也会发生这样的事!这和国民党监狱里的为非作歹有啥两样!我决定要将此事向李所长报告,当时有个别好心人劝我不要多事,以免招来祸害,我带着正经的面孔说:“咱们既然表示要靠拢政府接受改造,就应该把这件事对政府反映。”说实话当时我要向政府反映的用意是,想对共产党作一考验,看你共产党是否也同国民党一样,包庇有不法行为的部下。于是我及时向警卫报告,要求和李所长谈话。当李所长将我叫到他办公室后,我将商女写的东西交给了李,同时我对李说:“为了一个少女免于被人遭蹋,我大胆将这封信交给政府。”李所长当时大致看了一下,没对我表示任何态度,只说:“你回去吧。”从这天起,我们再没看见这位年龄较大的看守。过了几天,吴科长去看守所找我谈话:“你能将商××写的纸条交给政府,是愿意靠拢政府的具体表现。你应该完全相信,共产党是有严格纪律的。我们对自己的人犯了错误,决不姑息,必须严加教育使其彻底改正。你现在才30多岁,人生的道路对你来说还有几十年,要作一个真正的人并不那么容易,政府希望你们认真学习,从各个方面去改造自己,将来争取成为一个能够被人民饶恕的人。”吴科长对我这几句语重心长的教诲,在当时也可算作是触动我开始接受改造的起点吧!我回到小组后,将吴科长对我谈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大家,有的说:“真替你捏了一把汗!”有的说:“从来都是官官相护,这在过去,看守人员对待一个犯人是想咋就咋,可共产党就不是这样,难怪人家会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就以这件小事,对我们改造小组的每个人来说,受了一次活生生的教育。
同年6月间的一天,李所长将我叫到办公室。我刚走进去,一眼就看见爱妻刘华淑坐在对面的桌子旁,她见我进去,马上站起来向我走近几步,嘴角在颤动着,却说不出一句话。我忙问她:“啥时从上海回来?”她答:“我是搭平沪通车的首班车回到北平的。”我问:“北平家里的两位老人都好吧?”她答:“都很好,只是老母亲成天在念叨你,院里的房东家经常去劝慰老人,同乡们也不断去照顾家里。有时街道派出所的同志也去开导老人们,还对老人们说,你学习一个时期就会回来的。”我说:“你回北平后可对老人们说,我在天津受到政府的格外照顾,等我办完交待手续就会回来的。”妻又说:“我去上海后,最初临时住在同乡开设的钱庄,后来在弄堂里租了一间房,经常还去钱庄吃饭,一次在钱庄看到一本《NEWS》杂志,在翻阅中发现了一段天津解放后的报导,其中看到你被人民政府定为战争罪犯,我立即休克倒地,经过抢救情绪才安定下来。后来有你过去的好友们,劝我随他们去台北暂时躲避,当时我考虑你既被定为战犯,恐怕短时间内得不到自由,说不定还会被判处长期徒刑,家中老人谁来照顾?我只答应他们想想再定。后来我又考虑,如果去了台北,谁也不敢保证共产党就打不到台北。没多久共产党打进了上海,我看到人家共产党的军队很守纪律,不论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的,尤其是当兵的很少在马路上游逛,也不随便进商店买东西。我看共产党并不是那么可怕,于是决定等通车后回北平去。”
妻子走后我回到监室,思想上翻腾起近10年的往事。爱妻算得上一个苦命人,抗战初期我就弃学从戎离家远走,1940年初爱妻千里迢迢奔向豫北太行山寻夫,几经周折始得团聚。1942年初我在中条山晋南一带遭日军俘虏,后被关押在山西临汾日军俘虏收容所,在罚苦役修飞机场时,逃出日战区回到西安。1942年12月间因内部分脏不均,被军统关押在西安看守所达两年零10个月。这一次在天津解放战争中被俘,将来即使不被枪毙也得长期关押,解放前我既没弄下金条,也没购置下房产,只靠几个山西同乡商人搞点投机倒把生意。过去人们常说:“官久必富。”总认为只要能爬上高官,就自然会有富禄,其实未必尽然。所幸妻从上海回来,双亲总算有人照顾了,家中的生活也只能靠变卖家俱衣物和妻的几件首饰暂时维持。
这以后又出现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有一天李所长叫我去办公室,我刚走进去看见办公桌旁坐着一个身穿黄军服、头戴大沿帽的年青干部。这位干部微带笑容问我:“你还认识我么?”我定睛一看有些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是谁。这个干部说:“你还记得你在北平稽查处时,处理过我的问题吗?”我猛然想起这是被特务逮捕的中共地工报务员陈××,于是忙答:“记得!记得!”当时我思想上突然感到有些恐惧,认为这肯定是来报复的,因我在审讯他时,他坚持说收发报机因出故障,被领导人取走修理,也不知道在何处修理,当时特务们胁迫陈的掩护人交出电台后,陈仍一口咬定电台已被取走修理。后来我在审讯陈时,将电台掩护人及电台一并带至审讯室,陈十分气愤,我斥责陈“太不老实”!孰料陈昂首将头摆过去,一语不发。我指着陈说:“今天要教训教训你,治治你的不老实。”遂对陈的掩护人说:“我要你打他几个嘴巴,教训教训他,要他向你学习彻底谈清问题。”这个掩护人走过去对陈说:“事已至此不应再隐瞒,为了我的家人安全,我已把事实经过全部谈了。”因为问题已基本搞清,我令特务们将陈等带下时,我走过去向陈的背后狠狠踢了一脚,并说:“你才20来岁,还有收发报技术,你的罪责并不严重,何必这样固执,我很生气你这不老实态度。”正当我低头回忆上述情况时,陈似乎看出我有思想顾虑,于是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说:“我是因公来天津的,顺便来给你讲讲政府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这是说了算数的。共产党对你们是不讲报复的,你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对革命、对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罪行,当然这和国民党的反动制度也是分不开的,只要能够认真学习,背叛过去,彻底交清问题,政府是会给你们出路的。共产党闹革命是为了改造人类改造社会,并不是从肉体上把你们消灭掉。听看守的同志介绍,你还愿向政府靠拢,希望你能认清形势,丢掉一切幻想,争取将来政府对你的宽大处理。解放后我曾去过你在北平的家里,你的两位老人都很好,你应安心学习认真改造思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非铁石心肠,焉能无动于衷?我饱含着惭愧忏悔的热泪,站起来对陈深深鞠了一躬,并带着激情说:“谢谢你对我的宽恕!”因当时情绪过于激动再也谈不下去,李所长送我回到监室。(www.daowen.com)
我的情绪稍稍平静后,将我会见陈的详细经过向大家作了介绍,大家听后,有的说:“这在历史上也是稀有的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天经地义的,共产党居然是有仇不报,反而慰勉自己过去的仇人要作好人,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还有人说:“共产党能以德服人,当然会受到人民的拥护爱戴。”共产党不计前嫌宽宏大量的气派,通过这次会见,在我心灵深处撒下了良种,对我以后消除顾虑,进一步靠拢政府,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我想起了一句谚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天晚上我又反复思量,我决不能辜负陈同志对我的谆谆教诲。我又回忆起在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所谓的“政治犯”,原先是开设“反省院”,后来是成立“青训大队”,都是采取威胁利诱的手段,强迫革命人士叛变投敌,而共产党却是诱导人们接受真理,以德服人,自然会使人心服口服。
我们这个改造小组,还是受到一定特殊优待的,每天能到院子里放风一次,每周改善两次伙食,家属也可定期去送衣物。进入冬季的一天中午,我们正在院子里晒太阳,李所长领着一位带照像机的干部,要给我们每个人照单身像,因事前李所长没对大家说明照像的用意,于是每个人在拍照时都带有狐疑懊丧的神态。在轮到给我拍摄时,我立即回忆起过去军统对关押的犯人秘密处死前,必须要照像,处死后也得拍照,防止在执行时,犯人家属买通刽子手,来个冒名顶替、抽梁换柱。那天照完像后,个个疑感不解,总认为凶多吉少,我将组里大家的思想情况向李所长作了汇报,李所长特地到我们小组说:“为啥政府只给你们几个人照像,不给其他小组照像,这是政府的需要,你们这些人总好疑神疑鬼,说明你们对政府的政策并没有完全相信。”后来才知道这是天津市公安局搞一次“公安展览”,将我们的照片同时展出。
接连不断的爆竹声,迎来了1950年的除夕之夜,饭后每人几乎都在垂头想心思,有的低声哼着京剧自慰,有的蒙头躺卧,有的站在窗前向天空凝视。突然政府工作人员郑干事提着一个白布包匆匆进来,并叫一人跟他去,不一会抬来一张小方桌,桌上放着两条床板凳子,郑干事对大家说:“来,来,来,谁会打麻将?咱们来赢糖吃!”说着摆好桌子打开白布包,里面有一个麻将匣子,另有一条香烟和一大包糖果。因为只有两条凳子不够用,平时善于在生活上出点子的戴笠的副官贾金南说:“有办法,把大家的被子褥子摞起来还是沙发哩!”说时迟那时快,不一会清脆的麻将声使室内的气氛一下变得活跃起来,个个脸上的愁容刹时变成了笑容。因为只能有四人上场,为了利益均沾,定下了一个制度,谁在庄上输了谁就下场,由场下的人顶替,这样一来只要轮到庄家,总是煞费苦心小心翼翼,总怕下台。每人嘴里吃着糖,手里拿着烟,不觉得已过深夜,但每个人还是精神充沛,毫无倦意。最后还是郑干事提出,天快亮了大家该休息了,临走时只把牌拿走,香烟糖果留给了大家享用。入睡时我兴奋得连眼都闭不上,政府在除夕之夜对我们这样照顾,真是称得上用心良苦。这位郑干事看上去还不到30岁,也不像个工农出身的干部,竟然能在除夕之夜抛开和家人欢聚的良宵,陪着我们这些罪犯在一起打牌,这种精神的确令人难以理解!
次日春节早餐,炊事员给我们送来一盆热气腾腾的水饺。开始时大家还是分着吃,不一会又端去一大盆,并告诉大家随便吃,特别交待千万不要吃坏肚子。这顿香喷喷的饺子吃完后,个个都挺着肚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以帮助消化。
春节过后,政府给组里发了一本《社会发展简史》小册子,要大家认真学习,进行讨论。这个小册子开始是讲从类人猿到人的进化过程,以后是从原始社会到各类社会的发展史。开始时大家对此兴趣不大,认为是研究人类学的问题,我虽然没公开自己的态度,但在内心里曾想:我是基督教家庭,幼年在教会学校上学时,《圣经》上说人是上帝造的,上帝用一堆泥,捏了一个人吹了一口气,就成了一个名叫亚当的人,后来又造了一个女人叫夏娃,人类就是这样繁殖起来的;上了中学后才从书本上知道,人的祖先是类人猿,周口店还发掘出有类人猿的头盖骨。讨论中有人提出:究竟类人猿与人的分界线是什么?有人说:类人猿能直立起来行走就可称作为人。有人说:类人猿的尾巴退化了就算是人。在一次各组学习汇报会上,别的小组也提出这个问题,李所长当即指出,在学习中讨论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大家应从各种社会发展阶段中提出问题进行讨论,最后才能逐渐认识社会主义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关于类人猿与人的分水岭,有人认为是火的发明,由生食变为熟食就可称之为人,总的说人是由劳动创造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