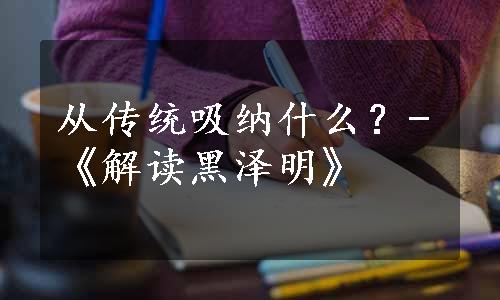
5.1.1.1 有国艺=有国粹?
在张艺谋等人获得世界声誉、创造所谓中国当代电影大师神话的时候,中国的传统艺术帮了他们的大忙。《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中无处不在的京剧、《千里走单骑》中古老而神秘的傩戏、《活着》中朦胧古朴的皮影、《十面埋伏》中杀气腾腾的长袖善舞,以及《黄土地》、《红高粱》中的原生态歌舞、《英雄》中出神入化的书法、围棋与剑术……这些都是中国的“国艺”,而它们在中国电影中的存在形态与能和歌舞伎在黑泽明作品中的存在形态却并不相同。
对外国人来说,戏曲恐怕是最有中国味的艺术形式之一,而戏曲在张、陈的电影中出现的次数也最多。《大红灯笼高高挂》中,三太太梅珊原是京剧演员,清晨时分常常会穿上戏装在空空的屋顶上载歌载舞,清脆的嗓音、婉转的曲调、妙曼的舞姿飘荡在阴冷、压抑、沉重的大宅院上空,象征着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沉埋。而当她被家法处置后,四太太颂莲为了报复杀人者,在三太太的院子里点起红灯、昼夜不息地用留声机播放京剧,红彤彤的灯光、无限重复的旋律营造出一种诡异凄凉的氛围,如同含恨的冤魂在不尽地诉说。谈到冤魂,让我们想起黑泽明作品中的“梦幻能”,其实京剧中表现冤魂怨鬼的剧目并不少,但张艺谋在这里使用的是一出讲述寻常家庭纠纷与误会的《御碑亭》,作为客观对应物反映梅珊的悲剧命运显然缺乏力度。所幸的是当代电影观众中熟悉京剧的人不是很多,对这个应该看作瑕疵的处理并未发觉,但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张艺谋对京剧也并不是很熟悉。对他来说,京剧只是一个构成中国味道的元素,与红灯笼、足疗一样,换成评剧、豫剧也不会对影片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霸王别姬》是以京剧演员的成长经历和爱恨纠葛为主要内容的影片,作品中到处是京剧元素——科班、戏园子、名剧片段,但实际上,京剧在这里和在《大红灯笼高高挂》里一样,也只是存在于形式的表层,并未参与影片的叙事本身。影片真正的着眼点是京剧中的男旦现象,科班对男孩子们强制的性倒错训练、男性优伶之间讳莫如深的断背情结是导演最感兴趣的东西。陈凯歌在内容上夸大了这些所谓的行业秘密,引起观众的猎奇心理,在形式上又用京剧元素为影片披上华丽而看似真实的外衣。其实,稍有京剧知识的人就很容易从中发现荒唐可笑的情节。在现实生活中,恐怕没有一个科班老师会让全体学男性行当的男孩子合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所有学女性行当的男孩子齐念“我本是女娇娘,又不是男儿郎”,因为这根本不是普遍通用的练习曲,就像体育学校的老师不会让所有学生每天都跳水一样。导演这样处理,只不过是为了夸大这种性倒错训练的广泛和深入,便于两个主人公沿着通向两种性别取向的道路成长,为日后的故事做合理铺垫。陈凯歌也让演员在大部分时间里画着京剧的脸谱出现,但是与黑泽明让演员凝视能面的意图不一样,他并没有要求演员表现出脸谱上所呈现的那个人物。段小楼所勾画的霸王脸谱有着深深的仿佛注满泪水的眼窝,眉毛呈现出汉字的“寿”,在京剧中象征着刚愎自用、英年早逝的大英雄,饱含着人们的敬仰和惋惜。而影片中张丰毅实际上只是顶着这张脸走来走去,显示他是京剧演员而已,并未像黑泽明在《蜘蛛巢城》里所做的那样,让鹫津在弑君时突然现出“平太”面,造成极大的震撼力。影片虽然处处写京剧,但没有一处运用京剧的方法、体现京剧的审美特质。《霸王别姬》中霸王与虞姬的故事实际上和段小楼与程蝶衣的故事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创作者只是相中了剧中阳刚与柔美的搭配、“从一而终”的理念,用这个外在的故事把两个主人公拴在一起。
虽然《御碑亭》写的是受委屈的妻子数落丈夫、《霸王别姬》写的是忠贞不渝的爱情,但它们与影片中主人公被迫害致死的悲剧、男人间纠缠不清的断背情结完全是两回事,这两个戏中戏不可能在象征层面对故事做出阐释和评价。其实,在黑泽明的电影里也出现过“戏中戏”。《影子武士》里当织田信长得知宿敌武田信玄确实已经离世时,站起身来且歌且唱。
信长:哼……毕竟是信玄哪,死了之后还巧妙地骗了我信长三年!
他说完倏地站起来,且歌且舞。
人生五十年
比起生生死死人世间
无非一梦幻
丈夫受命生于斯
英名该永驻,常在人间[1]
这段歌舞来自于“梦幻能”剧目《敦盛》,表现的是如嫩芽般早逝的少年武士平敦盛的幽魂向法师显现,通过舞蹈述说往事,感谢法师为自己诵经,消除心中仇恨的故事。织田信长在这里跳起敦盛之舞,不仅是为自己所敬仰的敌手安魂,同时也表达出一种世事无常、人生苦短的悲叹,这是隐藏于外表强悍的武者胸中最脆弱的心弦。显然,这段戏中戏,并不只是色彩元素,它构成了真正的客观对应物参与了影片的叙事。
从《霸王别姬》到《梅兰芳》,京剧的色彩元素已经被陈凯歌使用到了极限,但观众从极为满意到不满与质疑的态度转变,透露出大众审美能力的提升,今后再想以眼花缭乱来麻痹观众恐怕不太可能了。张艺谋大概很早就看出了这个苗头,于是他抛开京剧,继续新一期的考古挖掘,《活着》中的皮影戏、《千里走单骑》中的傩戏、《英雄》中的书法与剑术、《十面埋伏》中的唐朝舞蹈,这些都比京剧更古老,也因此显得更神秘。实际上,它们与京剧一样,在张艺谋的电影里仍然只是炮制“中国味”的作料,如果将它们换成另一种民族艺术,丝毫不会使影片有实质性的改变。我们这样说,张艺谋可能会不服气,在以下这段采访对话中,他非常自信地表明自己也像黑泽明一样使用了戏曲的叙事方式。
新京报:你在影片中用了很多很中国化的叙述方式,比如“折子戏”式的结构等等。但是很多观众似乎还不能完全接受。
张艺谋:这其实是我从中国传统戏曲里借鉴的手法。中国戏曲讲究“宽可走马、密不透风”,我一直喜欢这种东西。如果是拍一个写实电影,哪怕没有任何故事,就拍这个人的生活细节就可以了。但是武侠电影的世界本身是虚拟的,也谈不上生活化,所以它的创作常常要借鉴中国美学,包括中国戏论、画论里的东西,我很喜欢这些经典的、东方式的创作定律。它其实是潜移默化渗透在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深处的,相反是我每次跟美国人谈这些他们总是理解不了。[2]
这段谈话看似冠冕堂皇,实际上却暴露出对话双方在戏曲知识上的欠缺。所谓“折子戏”,是为了适应观众的欣赏需求,撷取全剧中的精彩段落,独立演出,比如《牡丹亭》里的《游园》、《惊梦》、《拾画》、《叫画》等,折子戏演出是一种戏曲演出形式,而非叙事形式。如果我们从张艺谋的多部电影中选取精彩段落,编辑成片,可以命名为“张艺谋折子戏专辑”,但不能用“折子戏式的结构”来解释一部影片情节的松散杂乱和比例失调。而“虚拟”则是一种表演方法,说的是在戏曲舞台上演员模仿的生活动作是逼真的,但动作所附着的物质实体并不存在,如演员通过动作表现上楼、下楼、开门、关门,虽然舞台上并没有真实的楼梯和门,但观众通过演员对生活动作惟妙惟肖的模仿,获得一种真实感。京剧演员运用虚拟的方法来表演,并不等于说京剧的内容都是虚无缥缈的。按照张艺谋的想法,“武侠电影的世界”是“虚拟”的,那将意味着这是一个海市蜃楼的世界,而他想要追求的种种“大爱”与“大侠”的精神将失去依附而成为凭空想象。他在这里提起“虚拟”恐怕只是想借用这个概念为影片内容的空洞开脱。这样的误读绝不是渗透在中国人审美心理深处的“经典的、东方式的创作定律”,中国人尚且不懂,外国人又怎么能明白。而且,外国人在欣赏中国传统艺术时并不存在巨大障碍,对黑泽明运用能乐形式的作品也看得津津有味,如果张艺谋的影片真的与中国绘画、戏曲同根同源的话,外国人又怎么会突然不懂了呢?用中外文化的差异来解释《十面埋伏》在奥斯卡的落败,实在是个牵强的理由。黑泽明运用传统艺术的叙述模式、表演方法来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传统艺术元素不仅为影片增加了浓郁的民族风格,而且参与影片叙事本身,如果抽离了这些元素,影片的叙事方式将发生很大改变。但在张、陈的作品中,中国的国艺只是作为吸引西方观众的色彩元素存在,它们所包含的美学理念与影片的叙事本身没有必然联系,随时可以拆解和置换,不会影响影片的形态。(www.daowen.com)
5.1.1.2 大师光环=真实感动?
《霸王别姬》是一部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娱乐片,因此这种只把京剧当色彩组件加以运用的方法,并未给影片带来明显的危害,但在接下来的一部以京剧大师为主角的影片中,这种方法的弊端就暴露无遗了。这次导演不仅全方位地使用了京剧的色彩,还拉进了一位京剧大师。
《梅兰芳》在上映前掀起了一场很大的宣传战,虽然没有《无极》的前期宣传那么离谱,但也着实可观,然而上映之后观众的反映却比较模棱两可:要说有什么毛病吧,又说不出来,要说好看吧,又总觉得欠缺一种很重要的东西,总之并不感动。其实,观众的感觉是准确的,之所以表述起来有些暧昧,是因为大多数电影观众对京剧的历史和京剧艺术本身不太熟悉。如果我们把那层由京剧、旧中国社会百态、明星阵容共同编织的、闪闪发光的网拨开,同时放下对大师盲目的崇拜,仅仅把《梅兰芳》当作一部传记片来分析,就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论。影片选取了主人公“梅兰芳”人生中的三个阶段来表现其成长历程和崇高人格:年少时战胜梨园行的守旧势力、青年时代为艺术舍弃真爱、抗战时期为民族大义远离舞台。实际上,这是三个典型得不能再典型的事件,在50年代的中国电影中早已不知道出现过多少次。但内容落套还不是最致命的问题,关键是作为一部传记片,它缺乏足够的真实性。
传记文学(biographical literature)是记述人物生平事迹的文学形式,与小说的显著区别在于,纪实性是传记文学的基本要求。当然,传记中也不可避免地会渗透进作者的想象推断和情感评价,并允许作者作某些想象性的描写,但在总体上所记述的人物和事件必须是符合史实的。传记文学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纪传体”以其朴实雅洁又富于文学色彩的写法,成为后世历代编修正史的标准文体,被鲁迅先生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传记片与传记文学虽然属于不同艺术门类,但二者在真实性上存在共识。
若想将《梅兰芳》界定为传记片的话,恐怕存在一定困难:片中的三位主人公梅兰芳、福芝芳和孟小冬用了真名,而与情节发展关系重大的两个人物——十三燕、邱如白却是虚构的,前者是被少年梅兰芳战胜的梨园守旧势力的代表,后者是将梅兰芳塑造为艺术大师的功臣。如果说熟悉京剧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两个人物影射的是谭鑫培和齐如山,多少具有生活原型的话,那么第三个段落中,那个一直仰慕梅兰芳并为其自杀的日本军官田中隆一,根本找不到原型。有人说他影射的是与梅兰芳交谊甚厚的日本人波多野乾一,但波多野乾一是位戏剧家,更没有在战时自杀。按照影片的叙述,这几个人物都在传记主人公的人生道路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他们倘若真实地存在过,为什么要顶着假名字出现呢?如果这是出于对名人后代的忌惮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说服力也微乎其微。《梅兰芳》与《英雄》不一样,后者是故事片,如同传奇和小说一样,可以肆无忌惮地虚构和离奇,历史上真实存在的秦王可以自由地与虚幻的剑客们对话,而不用负历史责任。《梅兰芳》标榜自身是有突破性的大师传记,显然不应该以故事片的标准来要求。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推断:作者之所以让真实的历史人物顶着假名字登场,原因就在于片中所展示的事件并不真实。导演可以把真实事件放在虚构人物身上,但要是把虚构事件硬安在真实人物身上,难免要惹上官司,因此只能让真实的梅兰芳与几个他根本不认识的虚构人物对话。影片上映后,立刻有相当多的京剧界内人士和研究者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致的考证说明,谭鑫培、齐如山在真实历史语境中与梅兰芳的关系绝非影片所呈现的那样,这验证了我们此前的推断。
谭鑫培是公认的京剧鼻祖,他在京剧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不在于守旧,而恰恰在于以积极的开拓进取让京剧艺术从草创阶段步入成熟。齐如山作为梅兰芳艺术道路上志同道合的伙伴,对其人格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引导作用。陈凯歌为了突出梅兰芳的创新,就无情地把谭鑫培塑造成梳着小辫、沉浸于自我陶醉的老古董十三燕;为了解释梅孟的分手,就把齐如山处理成艺术至上主义的疯子邱如白。这种简单粗暴的篡改不仅剥夺了影片的历史真实性,同时也因其违背事件发展与人物性格的自然逻辑而使影片失去了合理性。十三燕的古怪和邱如白的疯狂虽然令观众觉得新奇刺激,但在短暂的兴奋之后,当人们想追寻其行为的内在逻辑和动机时,却注定要失望。《梅兰芳》在国内获奖无数,这些奖项的颁发是基于艺术至上的理由,表示对影片本身的信服,还是基于主题先行的思维定势,出于对大师盛名的仰慕?实际上,陈凯歌所拍的不是梅兰芳,而依旧是程蝶衣,是一个任凭他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任意驱遣的虚构人物。毕竟,京剧象征着伟大的国粹,大师象征着伟大的民族精神,请问:它如何能不获奖?在不少知名评论家被《梅兰芳》唬得晕头转向时,已经有一些人开始质疑影片对历史和政治的图解,质疑其“爱国主义”标签的生硬,以及艺术表现上的夸张、做作。如果这些质疑与京剧的相关知识结合起来,那将是最有力的批评,可惜的是京剧研究者大多不关心影视,而影视观众又对京剧知之甚少。陈凯歌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巧妙地借助“主旋律”的优势,以弘扬民族文化的姿态,用一大堆子虚乌有的事件把无法发言的大师和不了解实情的观众、评委娱乐一番,堂而皇之地捧得奖杯。
5.1.1.3 原始本能=民族精神?
寻根的最初意图是寻找深埋于地下的民族精神的根,而这种意图的前提是现在的文化已经萎缩没落,必须通过反思、批判和探索,重建民族精神。既然现实的文化已失去生命力,那么寻根就必将离开现实、城市和社会人,向着历史、边缘和本能展开。《黄土地》与《红高粱》完全符合这三个方向:从时间上来看,故事都发生在过去;从空间来看,故事都发生在未开发的蛮荒之地;从属性上来看,故事中的人物都是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原住民。在寻根大潮中跃上风口浪尖的张艺谋和陈凯歌,被自然地赋予了通过电影进行诗意启蒙的历史使命,而他们闯进国际视野的神话,更使人们确信他们的电影代表着精英文化,其思想内核就是伟大的民族精神。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当年的精英神话已经被无情地消解,没有人再把张、陈的电影看作民族精神的载体。为什么甚嚣尘上的“民族精神”会坚持不了短短的20年,张艺谋等人挖掘出的民族文化之根又究竟是什么?
《红高粱》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张艺谋非常自豪地从民族精神的角度解释自己的作品,他说:
我觉得,造成我们民族精神萎缩的原因之一是穷,所谓“人穷志短,马瘦毛长”。而我偏要在影片里把人的志气往高里提。……人创造艺术,就是想对世界、对人生发言。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就到艺术里去寻求。《红高粱》实际上是我创造的一个理想的精神世界。我之所以把它拍得轰轰烈烈、张张扬扬,就是想展示一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表达“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这样一个拙直浅显的道理。对于当今中国人来讲,这种生命态度是很需要的。……人们都应该意识到,生命的自由狂放,这本身就是生命的美,我们再不能让自己被动地或在各种人为的框框和套子里。[3]
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刚刚成就了丑小鸭神话的张艺谋那份扬眉吐气的痛快,他显然也把自己列为精英文化的一分子,认为自己的作品是自由的赞歌、生命活力的赞歌。的确,《红高粱》展现了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这是一个完全不受现代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束缚的没有“框框和套子”的世界。影片的结构极为松散,出嫁、野合、酿酒、打鬼子,每个段落与其他段落之间都不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前三个段落是原生态生活场景的集中展示——用女人换牲口的物物交换、从没说过话的男人与女人在高粱地里仪式化的交合、匪夷所思的酿酒工艺。如果我们把最后一个段落抽离,或者替换为打土匪、斗地主之类的情节,那么整部影片的思想性将完全改变。而张艺谋的聪明之处,就在于用“打鬼子”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调动起人们潜意识中的民族感情,激起他们“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的热情,使他们主动把影片提升到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人们狂热地赞扬颠轿、野合,似乎它们都是为了打鬼子而做的准备活动,其实这只是原始的欲望和冲动,与抗日战争没有必然联系。
张艺谋想展示的那种痛快淋漓的人生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原始本能的释放与狂欢。本书无意讨论狂欢化诗学的问题,只想借用一下巴赫金理论中的这一表述形式。“狂欢化”的渊源是狂欢节,而狂欢节的主要特征是无等级性、宣泄性、颠覆性和大众性。人们不分身份贵贱都可以参加狂欢节,通过纵情的笑宣泄现实的心理负担,无拘无束地颠覆现存制度和规范,重新构造和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原始的自由体验。《红高粱》中的“我爷爷”不正是狂欢节上的主角吗?像高粱一样天生地长、无拘无束,不受任何文明枷锁的束缚,在自然地怀抱中畅快地享受着本能获得满足的欢愉。
在压抑过度又骤然开放的历史时期,这种原始的野性似乎就是生机勃勃的“民族精神”,凭借这种精神,中国人就能享受到“生命的自由狂放”。然而,原始本能不会也不可能等同于民族精神,且不说对原始本能的过度弘扬,就等于否定了几千年的文明历程,单就是原始本能好坏杂陈的特点,就使将其作为民族精神的努力缺乏可操作性。大家可能还记得汶川大地震中那个弃学生逃走的老师,他说自己的行为是出于逃生的本能。那么,如果原始本能等同于民族精神的话,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岂不成了临阵脱逃?这样的推论,显然没有人愿意接受。
张艺谋其后的电影中,原始本能仍然占据着显著位置,但此前的自由狂放变成了愚昧和悲哀。在《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中火红的高粱地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深宅大院,喝酒颠轿的汉子也不见了,变成了受尽屈辱、低眉顺眼、被动挨打的可怜虫。生命的赞歌为什么一下子成了生命的哀歌?张艺谋使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他把原始本能提高到民族精神的高度,把自己提升为高扬民族精神的斗士,那么观众势必期待他以后的作品也要贯彻这种精神。但是能够承办狂欢节的舞台并不是很多,电影终归要从高粱地回到现实中来,在有“框框和套子”的现实语境中,难道就只有愚昧落后而没有民族精神了吗?张艺谋对此避而不答,开始挖掘民族历史中极丑的一面,继而在现实题材的作品中通过凡人小事歌颂一些闪光的性格侧面,而最近则沉迷于“虚拟”的历史中,阐释虚幻的“大爱”。
根据黑格尔的思想,每个民族都能提炼出一种可以称之为民族精神的东西,想要准确描述中国的民族精神的确不太容易,但它并不是遗世而独立的。黑泽明觉得能乐体现着日本人的民族精神,其实,在张艺谋和陈凯歌时常引用的民族传统艺术中,不也一样闪耀着我们的民族精神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