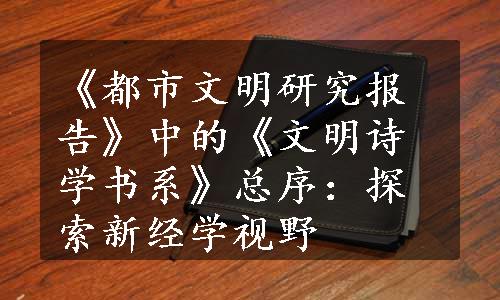
张大为
康德式的所谓现代性美学,建立在后来黑格尔、尼采等人从西方思想史与文明史线索出发指出的现代生活的观念化、理论化基础之上。西方的所谓现代性哲学、现代性思想的“深刻”与浅陋,或许都与这一情形有些关系。康德看起来似乎对这种关系深有体会,也辨析得很清楚,用康德自己著名的比喻来说,现实当中的100块钱比100块钱的单纯概念有着更多的东西,我们不能拿着算术运算的结果,就向银行索要100块钱。这似乎是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犯的错误,但包括康德本人在内,这种现代文明的观念化与理论化造成的现实后果却恰恰是,现代生活往往将自己的基础建立在算术公式般的抽象性之上。比如,康德美学就告诉我们,各种算术运算能力的和谐游戏,就是审美愉悦的来源。或许康德自己并非不清楚,这样的“美感”和审美愉悦本身,不能保证你的运算结果一定是正确的,更不能保证你真的拥有100块钱。但各种所谓现代性的美学和审美诗学观念,已然陷落在康德式的概念圈套与思维圈套当中不能自拔。中国学者通过宗白华翻译的半部《判断力批判》,研究了半个世纪“美学”,康德哲学和康德美学以其“平庸的深刻”,对于包括中国当代主流诗学范式——审美诗学在内的现代文学艺术理论,所造成的影响难以估计。而据一种被称为“认识论的审美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新近观念声称,现代生活与现代社会的建构原则,就是以这种很可能是稀里糊涂的“美感”和“审美愉悦”为中心的“审美化”原则。如果事情真是这样的话,西方文明要是不走向“虚无”与“没落”,才是值得奇怪的事情。
对于文艺理论或者诗学问题来说,这里涉及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文学经验与文学意义的“本体论”层面上的构成与归属问题:“文学首先是审美的……”“文学必须通过审美的方式……”“文学就是文学……”“文学必须根据它本身的属性……”“基于文学本体论的依据……”当人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在用某种形式性的、概念性的东西,来界定内容与实在本身,已经是在用“想象”“虚构”属性,论证一个“文学本体论”世界的自足性,或者说,已经用文学的“想象”“虚构”性的“审美本质”,置换、架空了现实经验的优先性:文学现在已经是一个“想象”“虚构”性的“本体”和“世界”了。这就像是在强调“地球必须是圆的”,但如果地球现在已经萎缩,或被置换为一个地球仪,甚至一颗小米粒,我们该怎么办?在中华文明传统当中,“惟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文学经验与文学意义,比之生活经验与客观世界的意义构成,更加不可能是“想象”与“虚构”——后者是为了让这一核心的经验和真实性得以更准确、更清晰、更全面、更“真实”地显现出来的手段,根本上服务于文学经验和文学意义的客观性呈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周易·系辞上》),文学修辞鼓动与驱遣的是世界经验的客观性的存在,这表明文学经验和文学意义根本上是客观性的、现实性的世界性存在,而非文学性的“虚构”“想象”与拟制。
在此前提下,“物相杂”为“文”(《周易·系辞下》),“弥纶天地”(《周易·系辞上》)、“错画”“交文”(许慎《说文解字》)为“文”,“经纬天地”(孔颖达《尚书正义》)为“文”,文化学术总称为“文”(《论语·先进》),“天地之心”(刘勰《文心雕龙·原道》)为“文”,有文字著于竹帛为“文”(章太炎《国学概论》)。在文明诗学的意义上,中华文明传统当中的文学是“弥纶天地”“经纬天地”之道,是“物相杂”之文,是对于世界经验和世界意义的经纬组织、错综编织、“杂物撰德”(《周易·系辞下》),或者说“戏剧化”的组撰、呈现,而不是康德式的审美地球仪。在这个意义上,是文学修辞让这个世界“明”亮、光“明”起来,是为“天下文明”。文学的世界,是一方逐渐明亮起来的天下江山、山河大地、生活时空、人伦性情场景,而不是一个人造的、仿制的甚至伪造的供人摆弄的“审美地球仪”,这才是文明诗学之“文”——“明”的文学本体论观念。所谓的“情深而文明”(《礼记·乐记》)一类观念,也要从这个方向上去理解,而不能理解为浪漫主义式的主体论、情感论。这样的文明诗学观念,可以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古典诗学观念相参证,也可以与弗莱所谓作为“调节”性的艺术观念相沟通。(www.daowen.com)
这样,在文明诗学的概念系统当中,“文明”的概念,意味着某种自然性基础与自然属性。中华文明通彻的自然属性,意味着中华文明的“身体”,就像“动则循卦节,静则因彖辞”(《周易参同契·天符进退章》)的自然身体一样,可以以实践的途径,通达文明经验的自然正确性与自然整全性,并直达自然法则的最高真理性和神圣性,而非必须首先经由哲学理念、概念理性的范导、反思与中介。西方式的哲学理性与理论理性,在这里没有高于文明体系的、作为世界理念原型的柏拉图式的重要性,而是具有派生性,或者说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结构位置与作用机制:我们把这种内在于文明自然机理、自然格局当中的理性叫作“文明理性”;把这种文明整体上的自然圆融性或者自然的“自然”属性,叫作文明的诗性,或者反过来,将具有这种整体性圆融的自然属性的文明体系称之为诗性文明。文明诗学的问题性,文明诗学意义上的文学的属性、地位与机能,要在这其间来理解、寻找和定位;反过来,文明诗学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修辞,不仅仅具有情感性、虚构性、审美性,同样也分有健全的文明理性以及综罗整全的文明经验与自然正确的文明价值判断意义上的深广的文明性格局。
在一个多世纪之前,中国现代学术体系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参照了西方现代相关领域的观念系统与知识结构构成。然而在今天,这其中的弊端和问题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尤其是从源头上丧失了传统经学那种对于文明总体性、根本性问题的思考视野与处置能力。文明诗学希望做到的不只是简单的学术视野的扩展与学科的交叉、叠加,而是走出学术理性的抽象空转与自我合理化,在对于东方和中国文明传统的高度自觉和价值融通的基础上,重建学术理性、理论思维与文明生活世界之间的内在关联,重建能实践的、“有用”的学术理性。如果做得好的话,文明诗学式的“文明”性的问题界面,可以成为一种“新经学”视野,成为对于传统经学之整全性与根本性的文明生活秩序视野的继承或替代性选择。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讲,文明诗学只能是更加宏大的知识系统与研究规划当中的一个部分,还应该有文明儒学、文明国学、文明史学、文明礼学……但它们相互之间,不再是互不连通的小格子间之间的关系,而应该是棱镜的不同维面的关系,或者互相交叠的花瓣的关系。
西方所谓现代性的文明方案,是一套有着重大缺陷的文明方案,中国在包括学术思想、文学诗学在内的文明价值认知与文明发展道路上,一定要避免走上简单认同和复制这种“现代方案”的路途。中华文明能够5000年绵延不绝,绝非是偶然的结果,而是源自其内在的文明机理、文明价值、文明理想的合理性。中华文明的未来,完全无需以西方那样所谓“现代”的工商业文明、消费主义文明为样板;中华文明的复兴,意味着以中华文明内在的自然正确性与高贵性,重新界定人类文明的定义与标准,乃至重新界定人与人性本身的定义与标准!这是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达到过的辉煌,也是中华文明在未来应有的抱负。谨将这套《文明诗学书系》,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破晓之际!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