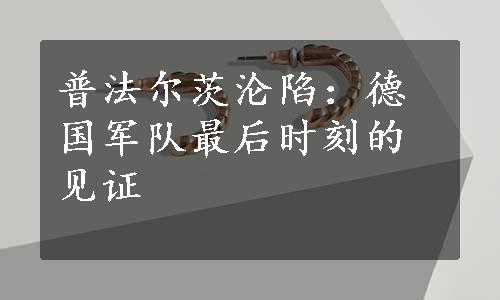
1945年3月,普法尔茨、雷马根到了危如累卵的地步。第7 集团军右翼被切断;敌人正进攻奥彭海姆方向,如果同时再以坦克大军对沃姆斯―路德维希港方向上的克罗伊茨纳赫(Kreuznach)形成一次突击,恐怕将置整个G 集团军群于险境。另外,普法尔茨中间两个集团军的内侧已被突破,被迫退向中间,并被局部包围。很明显,普法尔茨是守不住了,“自由行动”也没指望了。
因极度重视急转直下的形势,我在3月16日—17日、21—22日期间四次前往普法尔茨。很多事情都取决于第7 集团军的作为,他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战术将决定第1 集团军的命运,而不是后者的需求调节他们的运动速度。第7 集团军任务艰巨,但单纯从战术观点看,第1 集团军处境更艰难,全赖守在莱茵河一线的左侧翼枢纽,这就必须调整向中部撤退的步伐。普法尔茨森林成为焦点和枢纽点,保住它对于后来的机动必不可少。
在我的司令部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那次会议被一阵空袭短暂打断过[3]),我正同施佩尔部长、劳士领先生[4]探讨问题,有报告传来,称美军坦克已到达凯泽斯劳滕。而一个好消息是第7 集团军右翼以绵软的抗击拖住了敌人的前进速度。我亲自确认了施派尔(Speyer)和盖默斯海姆(Germersheim)两地的莱茵河桥头堡是巩固的,它们得到了高射炮的有力加强。于是自3月16日开始,我夜夜都能观察到后卫部队从那边源源不断撤回了莱茵河东岸。我们的空军受命不惜一切代价也要阻止施派尔方向上任何从莱茵河北边冲过来的敌人,令我如释重负的是,幸而敌人还没推进到这一步。
撤往莱茵河东岸的最后几天,行动由各军长和师长自行掌控。多亏他们奋力克服了不计其数的困难,比如交通拥堵,比如水泄不通的公路、小道和村庄所遭受的敌机空袭,马队、汽车和通讯线路陷入瘫痪。第1 集团军参谋部功不可没,当G 集团军群和第7 集团军不得不在莱茵河东岸建立防御时,第1 集团军参谋部自3月21日起便接管了莱茵―普法尔茨地区所有部队的指挥权。3月21日我军撤出路德维希港后,只剩下施派尔、盖默斯海姆和马克绍[5]三处桥头堡还可以守住,供最后一批殿后部队通过。3月23日,我下令撤离这几个桥头堡,3月24日到25日撤退结束。
萨尔―普法尔茨突出部特殊的自然条件适宜敌军行动,敌人选择了在第一时间发动进攻,却未能充分利用机会开展钳形运动。
敌人的坦克勇猛、甚至可以说鲁莽地进攻了第7 集团军右翼。显而易见,盟军采用的战术是快速发起一系列单独行动(可见他们摈弃了在意大利战场甚为突出的按部就班、步步推进方式),而且他们具备灵活的指挥能力,将坦克悍然投入到明明不适合大规模坦克战的乡村。我抱着在意大利乡村的类似经验,没有料到美军装甲部队竟赢得这么快,尽管部分原因要归结为德军精疲力竭,无力抵挡。然而令我惊讶的是,美军既然取得突破,却没有开拓利用这个短暂的机会,在空军支援下切断G 集团军群在几座莱茵河大桥的退路,进而将其歼灭。正是因为美军错失良机,G集团军群虽然损兵折将,令人痛心,但仍以相当可观的兵力撤回莱茵河东岸并据河而守,建立一条新防线。
对于盟军攻陷普法尔茨,当数他们的空军最功不可没。(www.daowen.com)
至于德军兵败如山倒,这是当初我同G 集团军司令和师长们谈话时始料未及的,我试着解释几点原因:
官兵们已经连续征战数月。三令五申“不准后退”的命令导致精兵良将和宝贵物资装备的大量损失,难以弥补。非但如此,希特勒还横加干涉,这是他对前线缺乏了解的明证,我们的时间就在等待他的指令被撤销或调整过程中白白流逝。战斗不是稳坐于办公室里就能指挥的。
完全适当地考虑到我军将士创下的彪炳战绩,过去几个月艰苦的防御战造成的巨大生理和精神压力也远远超出我基于亲自了解所预计的程度。提前恶化的形势和宽大的战线令我不可能走访前线单位,倘若我知道第7 集团军左翼侧和第1 集团军右翼侧的实际情况,我会更加坚决地要求希特勒更改我的任务,哪怕结局不会因此有本质不同。汽油和弹药配发量低得惊人,而且无论运动战还是决战,皆无法定时供应。美军的进攻来得太早,以至于我们的预备队还没完成集结。
允许撤离一部分西墙防线的命令下达得太晚,直到3月15日至16日晚上我才设法从希特勒那里获得许可,如果能提早一天,普法尔茨森林的溃败也不至于如此惨痛。
飞行员们不堪一击,莱茵河河谷的恶劣天气也帮不了我们。与之相对照的是敌人的空军势不可挡,普法尔茨的通讯已经很困难了,遭到轰炸更是雪上加霜。
然而,正因为局势如此绝望,我们弱小但忠诚英勇的师反而扛起了令人难忘的战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