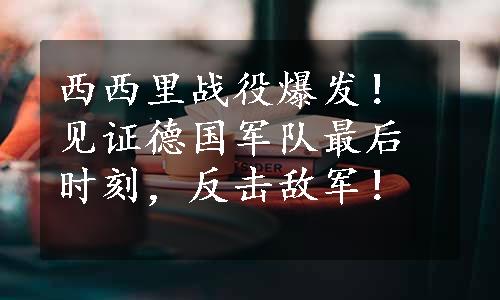
尽管之前已做出决定[2],但7月10日入侵发生的那天清晨,如果说我出手干预,通过无线电命令“赫尔曼·戈林”装甲师立即行动,那完全是为了亡羊补牢。一旦查明敌人的准确情况,所有参与反击的师必须进入战斗准备,最迟在午夜完成整队,以便能够赶到滩头发起反击。其他一些错误耽误了军队调动,浪费的时间再也无法挽回。尽管如此,“赫尔曼·戈林”师险些就要成功击退在杰拉登陆的盟军。
令人失望的事层出不穷,意大利岸防师完全失败了,无一能及时—甚至压根没有—向敌人发起反击,比如西南端的“拿波里”师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奥古斯塔的要塞司令甚至没等敌人攻过来就缴械投降。究竟是怯战还是叛变?墨索里尼曾向我保证要军事审判他们,但我一直不知道他到底兑现没有。与这一切相对应的是敌人压倒性的优势兵力,地面十个师携强大的空降部队和数千架飞机支援,它们基本上没遇到德国空军阻拦。
7月11日,尤其在我几乎无法与意大利集团军司令部里的冯·森格尔(Von Senger)将军取得联系后,我意识到,在司令部靠电话发号施令不可能解决前线的混乱局面。于是7月12日,我先下令将第1 伞兵师空投过来,然后便飞抵西西里,在森格尔将军陪同下走访了前线所有阵地。当晚我就见到第一批伞兵降落在卡塔尼亚以南,这场空降持续了多日,多亏英军战斗机死板地遵守时间安排,给了我军多次冒险调运的机会。
除了换来头痛,我的第一次西西里之行一事无成,我亲眼目睹意军溃不成形、战术紊乱,那都是缘于他们罔顾议定好的防守计划。西西里岛的西部没有继续防守的战术价值,唯有弃之,但即便如此,东部或者埃特纳山周围一个延伸出来的桥头堡也只能据守较短的时间。两个正独撑大局的德国师是不够的,想要尽快巩固“埃特纳防线”,急需增加一个师。好在我不用再提防盟军登陆卡拉布里亚,那曾是我的心头大患。
到7月13日上午,我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基本就所有事项达成一致,希特勒仅仅规定了即刻调来完整的第29 装甲掷弹兵师—后来的战斗中,他将为这份苛刻付出代价。第29 师直到7月15日才有少量部队渡过海峡。
15日到16日晚上,我来到西西里北部的米拉佐(Milazzo),交通工具是一架水上飞机,因为当时普通飞机已经不可能在那边完成降落。我现场向第14 装甲军军长胡贝(Hube)将军详细布置任务,让他务必在一条坚固防线上掘壕固守,哪怕初期做一定的退让。胡贝在白天几乎无法得到任何空中支援,作为补偿,我不惜违背空军组织原则,将重型高炮的指挥权交付于他,还催促第29 装甲掷弹兵师快马加鞭赶来增援。我又告诉胡贝正计划撤离西西里,因此他的任务便是尽可能拖住敌军。墨西拿海峡两岸正在加紧进行防御准备,现在都由他指挥。我又补充道,他无需忧心于掩护卡拉布里亚和阿普利亚,因为目前看来两地都不太可能是敌军主要目标。(www.daowen.com)
次日,我又花了一天的时间去视察前线、会晤古佐尼。会后我消除了心中的误会,并说动了古佐尼执行必要的撤退,因为我使他感到仍然有望阻挡英国第8 集团军。那天,我无意中看到英军舰队的猛烈炮轰,不禁叹为观止,后来的萨莱诺之战也存在类似经历,从此以后我改变了过去对海岸防御的看法。
第1 伞兵师的一位团长海尔曼上校回来报告时,我正在“赫尔曼·戈林”装甲师施马尔茨将军的战地指挥所,见到自己一度以为完蛋的海尔曼,我着实松了口气。原来他的伞兵们没有同翼侧德军建立联系便孤身降落在英军前线正面。随后的交战中,他们被蒙哥马利的部队包抄并围困,所幸承蒙幸运女神眷顾,成功击退了敌人。在英军后方实施空降的主意刚被提出来时有人认为太莽撞,违背了“军队实力必须合理匹敌于敌军”,这是一条同样适用于空降作战的基本原则。另一批伞兵降落在我军后方,意外捞到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因为片刻之后,英国伞兵也降落在同一个地方,我军顺势将其消灭。战果虽不起眼,但很大程度上干扰了蒙哥马利的进攻计划。[3]
总的来说,我如愿以偿。胡贝属于好钢用在刀刃上,又得参谋长冯·博宁这般人才辅佐。我略感扫兴的是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拖拖拉拉,压着在卡拉布里亚的第29 装甲掷弹兵师余部不放,第26 装甲掷弹兵师也迟迟无法投入卡拉布里亚作战,直到为时已晚。
和早期的地中海战役一样,西西里的行动指挥权名义上属于意军,实则在第14装甲军和南线总司令部手里。这段时期双方共同努力维持着并肩作战的姿态,彼此尊重,也没有发生私人冲突,这对胡贝再好不过了。我因自作主张,撤离西西里,坐了很长一段时间“冷板凳”,但相较于军队全身而退,个人得失何足斤斤计较。
胡贝以高超的技巧带领他的人马结束了迟滞战,安然撤离墨西拿海峡,足可证明身为军长的他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就。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