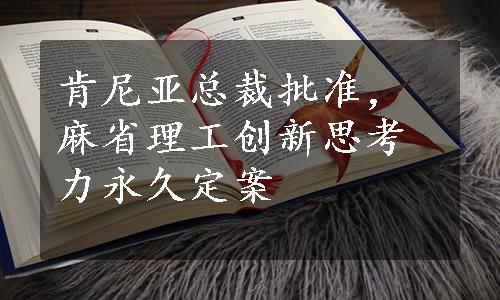
虽然得到塔塔的资金是一大进展,但是在2013年,我仍时不时地会在创业和博士研究之间摇摆。我的塔塔研究员合约规定,我必须在印度进行市场调查,但我目前在肯尼亚和一群农民有小型合作,该怎么办?难道我要弃他们于不顾吗?
“我拿一个粗俗的例子做比方吧!”MIT的导师对我说,“你现在的情况就好比你同时让两位女子怀孕了,其中一个的胎儿已有几个月大(那是肯尼亚),另一位的胎儿才几周而已(那是印度)。”
“当你和塔塔中心签约,你便已经承诺未来几年会尽心尽力照顾印度的研发项目。这完全合理,因为目前印度方面已经承诺会给你雄厚的资金及资源。反之,肯尼亚什么都还没承诺。”他继续剖析,“如果你在未来几年还坚持搞外遇,私下在肯尼亚经营企业,你说印度方面还会愿意再资助你吗?若你全心投入在印度项目的研发上,每年只有几个星期的时间去肯尼亚,肯尼亚方面还会认你为父亲吗?”
“我并不排除印度,我也认为用心探索印度的商机对我的未来大有助益。”我答道,“但是我已经在肯尼亚建立了许多人脉,也厘清了市场的巨大潜力,总觉得不能就此弃它而去。”
“那么你该为你的肯尼亚方案找一个寄养父亲了。”
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在未来几年不可能长期待在肯尼亚,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法便是找当地人合作。这是VMS的导师及朱斯特·邦森教授跟我说过很多次的事,我现在的创业重心不是要在肯尼亚当地亲自领导公司,而是寻找及帮助当地人才与我共同创业。但有些时候还是要亲身体验,才能理解他们的建言而有所开窍。
于是,我开始通过在肯尼亚的人脉为Takachar征才。我的想法是先聘雇一个在地的全职总裁,每个月付他一些薪水,日后我不在肯尼亚期间,会定期和他沟通公司的运营情况。最终目的是能够与肯尼亚乡下的农民合作,建立一个可以获利的制炭试点。我打算2013年6月去肯尼亚停留六周,全力找到当地的合作伙伴。
但是,我这个时候的最大问题是无法把任何一个想法专注完成。连我MIT的创业导师都说:“我给你的建言是两个字:专心!专心!专心!”
举例来说,在出发去肯尼亚的前三周,我忽然灵机一动:建立制炭试点是老古董的方法,为什么我不举办一场比赛,鼓励肯尼亚当地的创业者建立自己的制炭企业,通过几个月的评审后,最具潜力的创业者可以获得Takachar提供的一万美元奖金?一方面可以借此打开Takachar的知名度,二来也能创造更多当地的制炭企业。每个地区的挑战与市场特性各异,通过这样的竞赛可以促使当地人想办法解决问题。因此,Takachar何不转型为一个制炭企业竞赛的主办单位?
我和同事聊了这个想法,他们都很兴奋。我和肯尼亚的旧识聊起,他们也都很兴奋。接着,我征询了MIT主办全球挑战竞赛的人员爱丽森和奇利(Keely)。
爱丽森回信说:“我不认为这是个疯狂主意,但你必须慎思自己愿意投入多少时间及资源在这上面。举办比赛有很多细节,例如钱从哪里来?如何制订冠军的评断标准?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是很复杂的。还有许多关于管理人员的细节,你必须做好远端操控。我主办MIT全球挑战竞赛时,发现愿意帮忙的义工很多,不过也有很多人在你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令你失望。这不代表他们是坏人,而是每个人都忙得要命。假设你在肯尼亚主办的比赛正在进行,却有一半的评审突然退出,而你人在MIT,该怎么办?”
奇利也回信说:“除了爱丽森所说的,我还有另外两个疑问:第一,举办这个比赛是否适合当地文化?MIT本身就是个超级竞争的环境,因此很适合举办比赛。可是在其他场合,比赛的表现可能会完全令人失望。第二,你希望看到多少队伍参赛?我过去看过很多比赛,主办人花了很多心思,但比赛的主题太狭隘了,最后只有一两队符合资格。你会如何规划你的制炭挑战赛?它会受到当地广泛的瞩目吗?”
这些都是我在兴奋之余未曾想过的。我也和VMS的导师群提及这个制炭比赛的发想,他们完全不为所动。
“举办一场比赛就像同时养很多猫。”有位曾举办创业比赛也喜欢养猫的女导师如此说,“你喜欢养猫吗?”
“我认为你离成功很近了。”另一位导师说,“为什么现在要放弃你之前的所有努力而另起炉灶呢?”
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和仔细评估后,我承认这项制炭比赛想法确实让我心动,但MIT不同导师的论点更有说服力:举办比赛看起来很有吸引力,那是因为我还没有仔细深思其中令人厌烦的细节。
换言之,我觉得原来的Takachar计划困难重重,是因为我对它的所有可能风险和缺失早已了如指掌。所以,我决心正面迎战这些已知的挑战,继续执行原定的计划,即雇用肯尼亚人一起和我创业,在乡间与农民合作制炭。
2013年6月,我独自一人前往肯尼亚。以前,我都是和一群MIT的学生去,试图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研发项目或公司。但是身为全职的学生,我们只能趁每年1月和暑假的空当回到肯尼亚打理业务,我们不在的期间,当地的进度就会停滞不前,成果颇令人失望。这次暑假,我的任务不是去建立自己的公司,而是设法把自己的愿景传达给别人,激励他们相信自己也能采取行动。
我一抵达奈洛比,马上和八位可能对成立制炭公司有兴趣的人士碰面,还安排了所有人隔日一早驱车前往鲁姆鲁提观摩我在一年半前协助设立的制炭试点。我们一行人于中午抵达鲁姆鲁提,当地的森林协会派人来接我们,处长则开始讲起炭化的作业流程。一开始很多人听到农作废物可以转成炭,都是满脸质疑的表情。于是,森林协会的人员亲自为大家示范整个过程,将一堆玉米芯和玉米叶放入铁桶内,然后点火开始炭化作业。
最后,当打开铁桶看见里面全是货真价实的炭时,所有人不得不信服处长所言为真。“眼见为真(Seeing is believing)。”一位第一次看到这项技术的成员如此说道。其他成员在亲眼目睹了整个炭化过程后,似乎也看到制炭的前景和商机。
隔天早上回奈洛比的路上,大家都兴奋地谈论着。有两个成员一回奈洛比,当天就买好了铁桶,打算亲自尝试制炭。
期间,我也通过一位同事认识奈洛比某报社的资深编辑,他对Takachar很感兴趣。和他详谈之后,我发现他在肯尼亚人脉丰沛,也非常了解肯尼亚的待人处事文化,于是我邀请他担任我们在肯尼亚的导师。他首先要我找到高层政治人物的支持。
我告诉他:“我没时间搞政治,也没兴趣贿赂他人。”
“我不是叫你贿赂别人,那是违法的。我是要你的公司得到当地人的广泛支持。”他说,“你要知道,即使你的公司完全合法,如果哪天你冲撞到某个人,他们可以通过政治管道找出一条罕为人知的法律,叫你的公司关门大吉。所以你也必须有你自己可打的政治牌,以备不时之需。”(www.daowen.com)
他说肯尼亚总统最近任命了一位新的内阁环境秘书长,而这位秘书长和MIT有关系。他会通过这位内阁官员的家族友人,居间穿线把我介绍给他。
一周后,这位内阁秘书长的办公室主动和我联系,并且敲定了会面时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高层的政治人物,有点慌乱。
“我现在什么都还没开始,要和秘书长谈什么呢?”我问我的肯尼亚导师。
“你只需要介绍Takachar的前景,以及如何为肯尼亚乡间带来就业机会,也能帮助穷人和维护生态环境。这是不管谁执政都很容易获得选民支持的计划。”
“秘书长那么忙,我可以请她帮什么呢?”
“她才不会有时间帮你创立公司呢。你只需要认识她并得到她的祝福。如果哪天有人找你公司的碴,不管是乡镇还是县市政府,只要政治位阶是在肯尼亚总统之下的,你都可以向她求救。”
我终于开窍了。我发现以前去乌干达或加纳的乡村,第一件事便是去拜访当地的长老,得到他的欢迎及祝福,如此才能在他的村里做事。现在我要做的不也是一样吗?只是如今我要做的规模,是几年前的好几倍。
于是在约定那天的早上,我穿着西装前往秘书长的办公室和她聊了二十分钟。谈话中,她表达了对Takachar的支持。我的任务圆满达成。
一个周末,我坐了八个小时的车来到肯尼亚的蒙巴萨,和一位老朋友碰面。我也在想是否可以通过他在当地找个机构,于蒙巴萨市郊的乡村雇人来实现我的制炭计划?我花了整个周末和他计算营运成本,也造访了蒙巴萨附近的一个村落。
但我那位朋友前阵子试图振兴当地村落经济,通过他的组织在村落流通一种替代货币,结果遭控告伪造钱币。他和同事因而遭到逮捕,目前保释中,两个星期后要上法庭,因此他们很忙,没什么时间招待我。
“我劝你离他远一点。”奈洛比导师对我说。
“我了解。不过我相信他是清白的。”我回答。
“不管他是否清白,他在当地的行为必定惹火了一些人,才会有人想告他。”导师继续说,“如果你和他合作,不会有好下场。”
虽然当初和我一起去鲁姆鲁提参观制炭作业的有八个人,但是后来大都采取观望的态度。有心和我一起投入制炭公司的只有两人。我和我的导师找了时间一起去和他们面谈,主要想听听他们对于建立公司的想法。
最后我们录取了萨穆埃尔(Samuel),他是学农业企业管理的。他没有适合设立公司的地方,因此我把他介绍给在姆韦(Mwea)的同事。姆韦位于奈洛比东北方两个小时车程远的地方,盛产稻米,有成堆无用的米糠常常被火烧掉。我想利用我在肯尼亚剩余的时间,请萨穆埃尔为这个可能的制炭计划铺路,我也可以借此审核他的工作效率。
过了两个星期,萨穆埃尔报告说他开始在姆韦和当地农民合作,用一种新方法来炭化米糠。看来他的案子都有潜力,因此我小心翼翼地和他谈了薪水等事宜,并要求他每两周就把所有收据都拍照下来寄给我存证,我依据报销再汇钱给他们。偶尔他也必须寄相片给我,我的肯尼亚导师或其他朋友都可以随时到姆韦抽查当地的进展。制订好这些监督程序后,萨穆埃尔正式开始帮Takachar做事。
7月底,我必须从肯尼亚返回波士顿。登机时,我和其他乘客走出登机坪。奈洛比的晚风徐徐吹来,凉爽宜人,十分舒服。恼人的是,我的脑海里被各种不同的疑问盘踞着:我雇用这个人的决定是正确的吗?我要通过什么渠道确认他所报告的进展?他如果盗用我的钱,该怎么办呢?
我有一位MIT的日本同学,之前在肯尼亚的邻国坦桑尼亚设立了一家农民租用拖拉机的公司,结果因为太相信当地的合作伙伴,而被盗用了近十万美元。我要把我在肯尼亚的事业托付给一位只认识三周的人,似乎这是个疯狂的决定。
但是,有个声音在脑海响起:除此之外,我没有更好的选择。
我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我在MIT已开始为印度做制炭研究,所以无法花很多时间来肯尼亚创业。即使我或其他MIT的队友都来了,我们对肯尼亚的风俗人情并不熟悉。过去的一年已经尝试了几次,几乎是败兴而归。因此,如果我想继续在肯尼亚实现创业的愿景,目前只能靠当地的人帮忙了。
我在肯尼亚停留的时间只有短短六个星期而已,当然不可能为萨穆埃尔或其他人的人格和能力做完备的审核。我能做的,都已经尽力做了,剩下的就只能靠信任了。如果我要在短期内让Takachar在肯尼亚有所进展,信任是唯一的法门。
如果这次成功了,届时我不仅要帮萨穆埃尔投资设立一家制炭公司,也可汲取其中的知识和共享利润。万一失败了,我损失的顶多是当初从不同创新创业比赛中赢得的奖金。
因此,我把自己珍贵的Takachar婴儿,托给了只认识几个星期的肯尼亚人。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