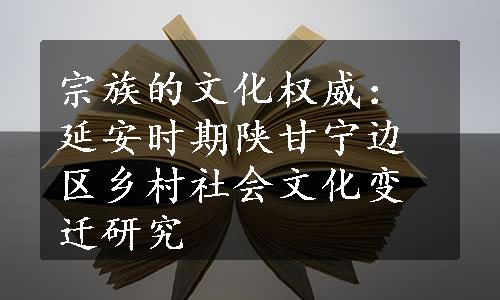
如果说乡绅在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获得是源自国家政权所授予的社会地位,从而呈现出感召性、法理性文化权威特征,那么乡老——乡村宗族中的长者的政治权力的获得是源于血统、年龄、资历等因素,从而呈现出传统伦理道德性质的文化权威特征。此外,乡绅在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获得不仅来自个人威望与德行,还来自其背后的宗族势力支持。中国乡村社会具有深厚的宗族传统,宗族在以陕北为代表的西北地区传统乡村社会政治结构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乡绅在乡村社会权力空间中,充当着官府与村民的中介者。而作为事实上的乡村政治掌权者,乡绅在利益选择上自然与其背后的宗族处于同一立场。乡绅与其所在宗族之间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关系。乡绅的出场需要本宗族的培养与支持,因此在乡绅成为乡村权力掌握者时,自然会将保护宗族作为自己的职责。
明清时期,封建国家在乡村推行以地缘为划分基础的甲里制,而乡村社会的宗族形成正是以地缘与血缘为基础的,因此国家层面的保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与乡村社会层面的宗族旁支重合。[24]乾隆年间合水县以乡村为基础整合户籍,县以下设两里十八甲。一里为一乡,东华里下设八甲,西华里下设十甲。里设里长,甲下设保甲,主要负责征税差役事务。[25]里甲设置的官方意义在于监管控制村民、维护地方治安。但这种规整的行政控制有效性显然无法与土生土长的乡绅为代表的背后整个宗族势力控制相比。如前所述,地方官府在向下级乡村征税差役时,还须主动与诸乡绅协商、定夺具体细则;即使是遇到乡里民事纠纷,也要先经宗族调解,只有调解不成才会最终经手地方官府。咸丰年间,清政府明文规定在宗族人口密集地“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立为族正”[26]。光绪年间,陕西实行的保甲制规定县上设一名士绅,分管四乡,各乡下设里,各里设一名里绅。[27]除了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设置外,还有自上而下的行政设置,即每十家为一牌,设一名牌头;每十牌为一甲,设一名甲长。牌头、甲长之外,在大姓宗族村落中再设一名族长。[28]
直到民国初期,陕西各地依然沿袭明清时期的保甲制度。1928年,陕西省颁布的保甲条例中规定了县—区—村—牌—甲—丁的行政单位。其中每五家出一丁,每十家为一甲,每五甲为一牌,每两牌为一村,每一村设一村长,村长负责定期训练民团。1932年国民政府又颁布新的保甲制度,由编查委员会在乡镇设立联保主任—保长—甲长—户长—家长。[29]
即使民国时期,国家政权在更新保甲制时,仍旧迁就了乡村以宗族聚集而来的自然村。这些时有调整的保甲政策仍然不会改变宗族村落的传统格局与权力自治习惯。乡村自治体系的维持需要乡绅,然而乡绅所代表的恰恰是其所在宗族组织的权益。乡绅因其文化知识的优势成为宗族中乃至宗族村落中的权力拥有者,而乡长或族长则是因其辈分、年岁、农事资历成为宗族中的领袖,成为保护本宗族成员以及与宗族相关村落的威望者。族长被宗族成员以及村落赋予的威望具体到权力空间中,则表现为对乡村政治、法律以及文化等各项权力功能。这种历史性、本土性的宗族权力习惯在本能上排斥外来力量,因此任何外力很难从他们手中分权。
宗族组织特色之处在于始终如一的聚族而居的村落格局。清朝年间,陕北榆林的叶氏宗族的居所就分布在程家峁、庙坪等四个村庄。直到民国,叶氏家族的姓氏以及村庄名称格局依旧,因此即使是行政意义上的甲,也终究还是与固定不变的宗族旁支系统重合。此种意义上的宗族组织实际上是传统农业社会中至关重要的基层行动单位。西北地区的宗族基本与村落重合,即宗族普遍居于同一村落。[30]明清至近代的这种聚族而居模式,经过世代繁衍,宗族血脉不断延伸,最终形成以宗族为核心的乡村权力空间,宗族成为传统政治机制的操控主体,历代政权推行的保甲制度下的保甲长皆从宗族体系中选出。保甲长虽然是乡绅的代理人,但二者都从属于同一宗族,都属于宗族势力的保护者。但宗族组织中的首领即族长也是宗族权力的捍卫者。这是因为族长身份的获取来自血缘、资历等传统宗族权威。因此,就宗族组织自身而言,其原始功用就是为本宗族提供保护。宗族内部权力集中在宗族精英手中,宗族精英便致力于整合宗族内部的向心力,在保护宗族利益的同时也使得国家减少对宗族所在乡村的利益剥削。因此宗族精英的存在实际上是宗族权力与国家权力得以并存的重要原因。20世纪30年代的西北地区税种繁多,其中包括河水费、水利费、印花税等30 多种税目。[31]此外,各乡村还要承担各种临时性的摊派杂费,连村中富户都担负不起。由于宗族利益受到严重侵害,乡村中的宗族长老多次组织抗议活动。宗族中的族长因为其传统权威,更多的是在乡村权力分配、道德维护、化解冲突等方面发挥作用,毕竟族长权力的象征和约束来自祖先崇拜,具有很强的地方自主性。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利益受到严重侵犯,政府成为地方的压榨者,不堪重负的乡村宗族开始以村庄为单位,共同联合对付官府。1922年,神木在举办乡村庙会的过程中,县政府派税警胡作非为,趁机无理讨索税款,作为当地乡绅的贺懋昭出面劝说,但税警不但要挟其上缴昂贵会税,而且动用武力驱散庙会,忍无可忍的贺懋昭集结其他担任庙会会首的乡绅以及乡民将税警赶出庙会会场。结果警役以袭警的罪名将贺懋昭抓进监狱。在此背景下,同宗族的各村绅士联名具保,最终以乡民摊派公粮、新建军营马厩、开设粮草站为交换条件,将贺懋昭保出。[32]由此可以看出,乡绅所代表的不仅是其所属的宗族利益,还代表其宗族所在乡村社区的利益。因此,宗族成员在维护宗族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宗族所在乡村社区的利益。宗族精英在为宗族以及乡村社会服务甚至对抗官府时,又进一步提高了威望,加强和巩固了他们在乡村社会的权力。(www.daowen.com)
清朝末年各地开始出现团练。西北地区团练的出现主要用以对付回民起义、土匪侵扰以及当地动乱。当时各县政府举办的官方团练主要由当地生员负责。团练成员基本都是抽出农闲时间,集中起来,统一配备刀枪。国家对地方团练的默许是出于缓解岌岌可危的统治危机,而对地方乡绅及其宗族组织而言,则是处于捍卫切身利益,维护其乡村统治权。此外,宗族组织为了防御当地动乱,建立大量堡寨。其中米脂县杨家沟马氏宗族修建的“扶风寨”使得整个宗族组织所在村落以及附近十几个村落都免于动乱侵扰。民国五年,米脂的李氏宗族带领团练击退土匪,自此米脂宗族团练声名远扬,使得曾被视为“难治之区”的米脂成为“盗贼惧其名而不敢相犯”的地区。[33]
晚清政府迫于时局压力而着手推行地方自治。1908年颁布的《自治章程》中专设“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明确将镇乡作为基层自治单位,以5 万人口作为乡与镇的分界标准。不久,各地纷纷成立自治机构,且自治机构从省级到乡级基本都有士绅掌握。其中陕北米脂高氏宗族精英不仅在陕西省参议会身居要职,甚至在国会也有一席之地。民国时期,国家对乡村政权的强化空前,但新型保甲制中规定的乡村行政职能仍是由“乡望素孚者充任”[34]。地方自治的兴起,使得西北宗族精英逐渐将具西方民权色彩的政治制度与传统的宗族基础相结合,提出宗族自治建议,将国家的衰落归因于宗族的落后。因此,西北地区的乡绅等宗族精英主张整合宗族力量,而实现宗族自治的途径便是承袭中国家族的伦理道德,“人人有族,族族有人,立爱惟亲,立敬惟长,结团基础为自治垣墉”[35]。
封建时代的宗族其实是政治、法律单位,某种程度上具备司法机构的职能。无讼传统下的宗族、乡里纠纷首先交由宗族首领即族长仲裁,这样宗族便不再是天然血亲团体,而是被赋予了私法性质的组织。西北地区的乡村社会中,宗族精英成为民间纠纷的权威调解者。例如宜川的乡绅张肇雯“蔓讼多年,纠结莫释者,得君为之调和事遂寝”[36];米脂的乡绅高照初在解决宗族内部纠纷时也颇具威信,乡里“愿踵君之门,得一言以定衡”[37]。宗族乡里纠纷的调解其实反映的正是宗族精英对乡村社会权力的把握,涉及土地、婚姻或者经济债务纠纷,都会需要宗族精英的裁量与定夺。宗族私法实际上同时也是封建政权权力的必然延伸。宗族设有专门的族法族规,旨在规范宗族及其所在乡村社会的行为规范,必要时惩治损害宗族利益以及乡村社会利益的族人。洛川屈氏宗族专门设有木板做成的刑具,长三尺,宽一寸,主要用以处置违背族规者。[38]再如民国时期,陕北榆林石湾乡李氏宗族成员李怀恒长期偷盗、勾结土匪,导致乡村鸡犬不宁,族人多次劝诫却屡教不改,后来宗族协商决定实行族法,将其手脚砍去。事后其妻将宗族告上县政府,但县政府不准其状,不久李怀恒去世。[39]由此可见宗族私法的严苛与残酷程度不亚于国家公法,也正因宗族面对宗族成员严重越轨、道德败坏行为做出“不近人情”的裁决,从而使得宗族权力在乡村社会中具有震慑作用,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此外,宗族组织中最严重的惩戒手段就是将违反族规者驱逐出族,被削籍出户者则再也无法接受原属宗族的保护,甚至族谱上也不会给其以记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