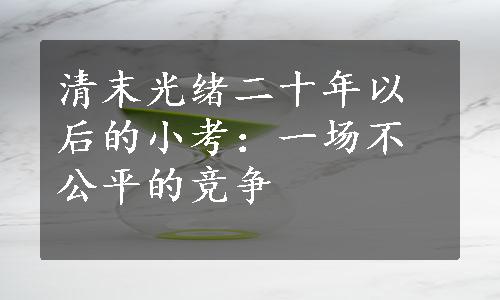
小考在光绪二十年甲午(公历一八九四年)以后,已经遭受轻视了,因为上上下下都知道国力日弱,欲整顿内治,欲避免外患,决非学问浅薄的、不知时务的、连“豆腐都换不到”吃的秀才所能为力。所以当时有提倡兴办学校者,有提倡出洋留学者,有提倡改试策论者,亦有提倡废除科举者。这许多事,后来虽然经过戊戌年的一度改而不改,变而不变,后来虽然经过不少波折——这许多事,后来无不逐渐一一举行。但到了今天,国家依旧不强,外患依旧未除,做过旧八股的人,又做起新八股来了。
做过旧八股的人,又做新八股——我倒是一个实例。我于二十岁(光绪三十年甲辰,公历一九〇四年)入泮(进秀才)。那年科举虽尚未废,然已改试经义策论。不过我十四五岁时已有人教我读“时文”(八股)、做“时文”,我的秀才不由八股换来;但我深知它的作法,到此刻六十岁,我仍能明白全篇的结构:破题,承题,起讲,起股,中股,后股等等,所以我敢称自己为“做过旧八股的人”。但是为什么我是个“做新八股”的人呢?八股在今日——不,八股在清末——已视为无用之物,无益于国,无益于身的文字。现在我常常在刊物上所发表的议论与感想,有几个人要看?能够有益于国家么?可以有益于身心么?我的文字既不合科学原理又绝无美术趣味,岂不是等于废话,等于八股么?
本篇言清末的小考,我离题了。让我“言归正传”罢:
小考就是考秀才。但考举人,考进士,不称大考;考举人叫作乡试,考进士叫作会试。我没有赴过乡试,没有中过举人,当然不能会试,当然不能中进士、点状元。乡试会试的情形,我一点都不知道。我所知道的,只有小考并且是清末光绪二十年以后湖州府属的小考。
小考分三试:(一)县试,(二)府试,(三)院试。县试在各县举行,府试院试则在府城举行。院试,亦称道考。
我们湖(州)府,共有七县:乌程,归安,长兴,德清,安吉,孝丰,武康。我家世居城内,居于首县乌程。程安两县名额不多,而“士子”(文童)较多,不易获取。外县“士 子”不多而名额较多,容易获取。但当时定例:属于甲县者,不得投考乙县,否则犯“冒”考之罪。所以当小考盛行之时,往往发生一件极不公平之事:首县之失败者,反较外县之成功者为佳,其差别决在师生(老师与学生)之上。某学台莅某府(不是湖州府)的时候,看到三个士子的三本卷子,一本都不通,一本都没有完篇,他自忖道,“那一县的文化太差了。然而朝廷的定额是十六人,现在只有三人来考,非全取不可。这三本卷子,一本都不通,一本都不完篇。……好,好,把他们都取了罢!让我来批。”
他在最好的一本上,批了“放狗屁”三字;在其中的一本上,批了“狗放屁”三字;在最劣的一本上,批了“放屁狗 ”三字。
他的“幕宾”在旁微笑而问道,“请教这三个批语有何不同?”
学台答道,“不同,不同,很不同。放狗屁者,尚有人性,他偶然放一狗屁;狗放屁者,固然是狗,但他不以放屁为主要之事;放屁狗最劣,他非独是狗,并且以放屁为正业。”
闲话少说,续谈小考——县试、府试、院试:
(一)县试。——县试亦称县考,分三场:头场,复试,终复,地点大概总在县署内。县试的考官,是知县(县长)。唱名,封门,……等等仪式,无不一一举行,但士子在归号后,无人查察,无人监视,任你翻书,任你枪替,全不遭受干涉。其原因是,县考无非形式,被黜者,仍得过府考。
(二)府试。——府试亦称府考,亦分三场。考官是知府。地点在我们湖州,因为府署太小,借用右文馆。右文馆(俗名“红门馆”)是专为学台而设的正式试场。
府试亦不严格——可以带书,可以枪替。府试被黜者,亦得过院试。但是县考府考在前十名者,学台无不录取,一则因为这十个人的程度总比较好些,二则因为府县官的面子,也不得不完。我在二十岁第二次出考那一年,府县考都在三名前;第一次出考(十七岁春),名次也不低,在前五十名的所谓“头图”内。但是因为提复(解见后)时,误解了题目“孟献子(即仲孙蔑,鲁大夫)请城虎牢以副郑”,未曾获取。
(三)院试。——院亦称道考,分正场、提复、终复三场。正场甚严,要收检,受监视——不准夹带,不准枪替(此二字作“捉刀”解)。头场被黜者,全无秀才的希望,只剩文童的空名。
提复更严。场中人数既少,监视之力愈增。非独不准夹带,不能翻书,并且按时按刻要完篇(三百字以上),要交卷。不完篇者不取,迟交卷者夺去。我们考在十名前的,更加苦闷。我们“吊”在大堂上,时时刻刻受道差的怒视,并且学台自己也坐在堂上,东看西看地查察我们,有时他还要跑到我们桌子边来看我们起稿,看我们誊清。
我复试的题目是“有心哉击磐乎”。那一年的“大宗师”(学台)姓陈名兆棻,性情似乎比较前科张亨嘉和平些;监视的道差,也没有像张氏那样多。我的远戚,因为年轻,被“吊”为幼童,也在大堂,坐在我前一排,他趁监视者远离之际。轻轻道,“月哥(我在二十岁前,以‘月船’为字,‘越然’是后来改的。我的考名是‘之彦’两字。)救救命!题目解说不出。救救命!写一、二十个字给我。”(www.daowen.com)
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哀求,我听得心乱了,写了五六十个字,揉做一团,置于桌边,轻轻道:“写好了,在桌边。小纸团,自己拿。当心,当心——要当心道差。”他快得很,一举手纸团失踪。那年他果然入泮,不过他穿“红靴子”(末一名)。
或者问道,“然则在那种谨严的监视情形之下,枪替亦非绝对不能?”
是呀,是呀!就是在我入泮那一年的正场中,也发生一件破纪录的枪替事件。据说有一位姓沈者,年已三旬,屡试不售,那一年的题目(正场)“是或一道也”,他又不知出典,无法动手,旁座刚巧有个健于文者,并且是姓沈的“熟人”。沈对他说道:“你替我做一篇,可不可以?替我做一篇,随你什么条款(条件)”。那人道:“可以,可以,每字一元(一个银元)。”沈道“算数(决定),算数。不进(入泮)怎样?不进半数,好么?”那人道,“算数。”
后来发榜,沈姓被黜。沈付半数,那人不受,说道,“我的文章,不会不进学的。我恐怕你误誊了,写了白(别)字了。待学台去后,原卷拿出来看,再定夺罢。”
卷子拿出来的时候,果然发现许许多多别字。那人因为每字一元的关系,多添“之”字(总写得半真半草)。沈姓性急慌忙,误视了,以为都是“三”字,都误写了。沈姓未曾入泮,请人评理,又评不过。只得忍气吞声地依照每字一元的“润”格,白费三百二十余元。
插入的故事,未免太长,我当立时停止,继言院试的最末一场 ——终复。
终复也有叫作大复试者。那一场完完全全是形式,学台固然也要点名,也要封门,也要出题,但不收检,并且你所做的文章(包括八股、经义、策论、五言诗)不论怎样不通,你不会被黜的;就是你抄篇刻文,也不妨大事,你总是一个秀才。我是个胆小人,在大复试时当然不敢抄刻文。我静坐默思,对于题目看了又看,看了又看,一句话都没有,一个字都写不下去。我已经是秀才了,我乐极了——全身发抖。后来我不知道自己写些什么,怎样完卷。但是我们同乡中也有胆大的人,就是后来大革命家沈虬斋(事实见拙著《六十回忆》中的《辛亥革命》篇)。他在终复场中不做文章,誊录全部《三字经》!他被罚——三次停科:不准乡试。
最末,我还有几句话:
取得秀才之后,倘然没有经过“岁考”,不能进乡场、考举人。这种新秀才,倘然要进乡场,应当先考“遗才 ”。岁考是下一年或者下一科,与考秀才同时举行的。遗才当年可考,实在是乡场的预试;不亲去者,可托门斗(教官的司事,教官亦称学老师)请人代替。
岁试分别一、二、三、四等。一等前几名或可补廪。列入四等者,不准乡试,但可考遗才。我考进岁试,真的列入四等。我所以列入四等的缘故,因为我有两件错误:(一)我好好的做成一篇理则论,开首四句,每句四字——自以为老到得很!我自言自语道,“这几句话,不像我做的——太好,太妙。此刻新学已经盛行,让我在它们上面加几个字罢,加——斯密亚丹曰——五个字罢。”不料后来将落卷取出来的时候,看见阅卷者(想非学台本人)在五字之旁打了一个大墨棍!后面的文章,恐怕他一句也不看。(二)我做英文翻译时,不用“子曰”(The Master said),而用“孔子曰”(Confucius said)。不知哪一位阅卷“大臣”以为错了,以为不合《华英四书》的语调,也在“孔子曰”之下,用朱笔画一粗划。同时,我代我的谱兄全录《华英四书》,完成一本翻译卷,倒考取一等五名。这位阅卷者,岂不是拿了《华英四书》硬对的么?
我没有考过遗才,我无志“上进”,没有取得举人的志愿。我当时最大的志愿是想学西文,想做个科学家,或者外交家。
确然,确然,上面的“最末”有三四百字,太长了,不像“最末”。让我换一个形式相像的“最末”罢:
最末,科举为国家旧时求取人才唯一之途。我在上面所讲,并非科举或者小考的全体,我讲我所知道的、亲历的。欲研究科举制度的全体者,可阅《学政全书》。
原载一九四五年五月《风雨谈》第十八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