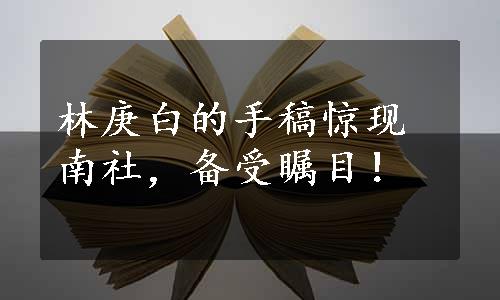
不久之前,大儿祉民在朋友家中发现林庚白的著作——诗集一册及日记数册——都是未刻手稿。他借来给我看。我粗粗翻阅,见诗有极雅者,记有极奇者;本拟抄录数十行于此,以表现他的文字,后想那两种稿本,都是他人的“财产”,未得允许,不敢冒昧。庚白的诗,从前常在各杂志中发表,本刊阅众,想已见过。他的日记,虽然没有刊行,然所记的无非会朋友,吃馆子,拟电报,写情书种种“鬼混”而已(“鬼混”二字是庚白自己的用语)。但几几乎每日总有一句妙语,就是“夜梦璧”三字。璧是女性,不知何姓,也不知哪一位女士的闺名。……我渴意要晓得庚白一生的事迹,但真是难找。《中国人名字典》专收死人(古人),当然没有庚白之名,就是《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索引》,也没有的姓氏。后来想到柳亚子的《南社纪略》,果然在二百三十三页有“林学衡,字浚南,号愚公,别号庚白,福建闽侯人 二一九”一条,又在九十四页有“林庚白,原名学衡,字浚南,一字众难,别号愚公,今以庚白行,福建闽侯人,中国同盟会会员,现任立法院立法委员”一条。我甚为得意 ……
写至此,适舍亲希平兄来访。我问他:“你知道林庚白一生的事迹么?”他立刻答道:“林庚白,名学衡,字众难,福建省闽侯县人,一八九六年生。北京大学卒业,中国大学露文学专修馆教授,历在众议院秘书长。国学造诣极深,后转向左翼。所著有《庚白诗存》《走哪一条路》《赤裸裸的我》《王女士》《人鉴》等书。一九四一年底死于香港。”
关于庚白的事迹,恐怕这是最完备的“报道”了。希平兄知识既富,记性又强,真是国内的学问家呀!
希平兄走后,我又翻阅《南社纪略》,见二百三十二页有“周越然,原名之彦,字越然,浙江吴兴人 四四八”一条,知道我自己也曾做过南社社员。当时南社“……以研究文学,提倡气节为宗旨”,文学气节……我真惭愧!
南社成立于清宣统元年(公历一九〇九年),第一次雅集到者十七人,其中有同盟会会员十四人,可见革命空气的浓厚。南社的“魂灵”是东南大诗人、大文豪柳亚子。亚子先生近来不作韵文,不作文言,改写白话。他在《纪略》一百二十三页上说道:
新文化运动发现之初,文言和白话的争论,盛极一时。我最初抱着中国文学界传统的观念,对于白话文,也热烈的反对过;中间抱持放任主义,想置之不论不议之列。最后觉得做白话文的人,所怀抱的主张,都和我相合,而做文言文去攻击白话文的,却和我主张太远了。于是我就渐渐地倾向到白话文一方面来。同时我觉得用文言文发表新思想,很感困难;恍然于新工具的必要,我便完全加入新文化运动。
这是亚子先生改写白话文的原因,也就是他革命的精神。但他终究是文言专家。我在购得的《南社记略》中间,发现夹藏着亚子先生遗下的手稿两纸,都用的文言。
这不是文言么?亚子先生虽不因书法著名,但他的笔法很好。
我把他的原稿影印数行出来罢:(www.daowen.com)
柳亚子手稿
上稿大概写于他离开上海之前。亚子先生的神经衰弱,从民十六年就开始了。他自己说:“……在短时期中间,神经兴奋,像火一般的狂热,什么事情都高兴做,并且一天能写几千言的白话文和几十首旧体诗。而在长时期中间却神经麻木,像冰一般的奇冷,甚么事情都不高兴做,并且不论诗和文章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见《南社纪略》一八〇页)
我谈南社,竟把林庚白丢了。然而不丢也不可;除了柳亚子的《南社纪略》和钱希平的《自由报道》外,我全然找不到材料。不过关于庚白的死亡,沪上有一种传说。让我把它写出来:
庚白精于命理。他推算自己的八字,知道在民国三十年必遭兵灾。他又推算他夫人的八字,知道绝无危险。他们当时在重庆,常有被炸之虞。他怕死,所以千方百计地跑到香港。等到十二月八日发生战争,他自知必死。然而事实恰恰相反;他与他的夫人,居然安安稳稳地度过了。他以为那是夫人命好;他靠夫人的福,所以不死。他们在战争中,同坐并行,形影不离。
战争告一终结之后,他们俩常在近处散步。一日傍晚,夫妇俩人行至街角时,忽听得“托买来”的猛声。这是停止令。他们不懂;他的夫人先奔了。士兵疑她为奸细,开了一枪,臂部略伤。庚白自己也奔了。士兵又开一枪;他中枪而死。
上面的故事,出于沪上某名公之口,想必可靠。
原载一九四三年六月《风雨谈》第三期(夏季特大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