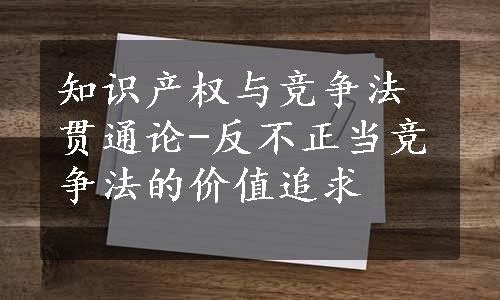
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是反对经营者出于竞争的目的违反市场交易中诚实信用的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攫取他人竞争优势的行为。因此,它首先保护的是受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的善意经营者的利益,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是公平竞争,以维护商业伦理和公平竞争为己任。反垄断法则是从维护市场的竞争性出发,目的是通过消除限制竞争的现象,保证市场上有足够的竞争者,促进竞争自由,以便使交易对手和消费者在市场上有选择商品的权利。只有当市场上出现了垄断或者垄断趋势的时候,政府方可干预市场,干预的目的是降低市场集中度,调整市场结构。反垄断法所追求的价值理念是自由竞争,目的是保障企业有自由参与市场竞争的权利,提高经济效益和消费者的社会福利。反不正当竞争法侧重追求竞争中的公平,同时兼顾效率;而反垄断法更强调追求竞争中的效率,同时兼顾公平。在德国竞争法中,“制度保护”(Institutionens⁃chutz)防止企业“限制自由竞争”(Schutz der Wettbewerbsfreiheit gegen Beschränkungen durch Unternehmen),“正当性保护”(Laut⁃erkei5tsschutz)维护“公平竞争”(Schutz der Lauterkeit des Wett⁃bewerbs)。但考虑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利益保护的这些自由有关的前提,竞争功能考虑的经济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被立法所拒绝,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对任何形式的意识形态化”[16]。
正是由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存在密切的联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垄断立法进入高潮,在各国和地区的立法例中,两者有不少是共存于一部或几部立法之中的。例如,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以及确保公正交易法》就包括“垄断行为”“不正当的交易限制”和“不正当的交易方法”三部分。
按照这种观点,“一方面,反垄断法以维护自由竞争为天职,原则上禁止一切限制自由竞争的行为。另一方面,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维护正当的竞争,反对不正当的竞争,其实质在于限制自由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规范的是竞争者具体的竞争行为,强调对竞争者本身私权利的保护,有利于保障静态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可以说是商事或经济领域的侵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在总体上不涉及市场竞争结构以及竞争的充分有效性,是一种“营业警察法”,旨在净化竞争秩序,使经营者、消费者免受虚假、欺诈性的竞争行为之弊。反垄断法从根本上规制市场竞争秩序,因此反垄断法有利于实现动态的交易安全,主要不是为了维护个别主体的具体权益,而是基于有效竞争的理论,刺激竞争的开展,力求产业组织的优化和市场结构的合理化,提高市场绩效,保证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产品的最低价格和最佳质量、促进工业的最大进步。职是之故,基于不同的理念,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为己任,主要关注于市场上企业间的相互竞争行为;而反垄断法则关注于竞争者之间的协调行为,以期防止市场上形成排除竞争或者严重限制竞争的局面,所以某种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例如竞争者之间商定商品或者服务的价格,因为没有损害任何竞争者的利益,并不构成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违反,同时,某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例如假冒商标或假冒专利,因为不会影响市场竞争结构,不会减少市场上竞争者的数目,亦不被视为违反反垄断法的行为。易言之,反垄断法和不正当竞争法从两个不同的角度保障和促进竞争:前者主要规范限制竞争行为,创造一个开放的竞争环境,后者则主要规范不正当竞争行为,引导、规范具体的竞争行为。限制竞争是避免或减少竞争,是竞争的对立物,而不正当竞争则并不排斥、限制竞争,其在承认并允许其他竞争对手参与竞争的前提下,采取不正当、不合法的手段造成竞争过度或不当,仍然属于竞争的范畴。是故,反垄断法则主要是保护社会公共秩序和由此保护市场的“公正且自由”的竞争秩序,旨在解决市场中存在的竞争不足问题,使市场的经营活动充满活力。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实质在于维护基本的商业道德,解决市场经济活动中存在的“诚实信用”问题和由此产生的相应的侵权问题,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犯。
愚见以为,这种观点表面上可以成立,貌似壁垒森严,但经不起推敲,泾渭分明的划分过于低估了问题的复杂性。不正当竞争确实是一种侵权行为,即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但是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行为。在不正当竞争中,行为人不仅侵害了作为竞争对手的其他经营者的利益,而且也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它除了损害作为一般民(商)事主体的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以外,还直接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机制——竞争机制,竞争本来是一种奖惩兼施(通过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而不正当竞争却破坏了这种竞争性制裁和奖励的市场机制。通过假冒他人驰名商标等不正当竞争方式,产品往往质次价高的行为者不仅有可能逃脱竞争失利的惩罚,反而可以侥天之幸弋获利润,安分守纪的企业却为此遭受声誉上和经济上的损失,甚至被挤出市场,以至于造成优者不胜、劣者不汰,劣币驱逐良币的局面,致使正常的竞争机制无法发挥其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和反垄断法一样保护竞争的机制。反垄断法从宏观上防止竞争不足,保持经济具有“有效竞争”的活力,提高本国企业和整体经济的竞争力,但确保市场主体的多元化也很有可能会削弱竞争力。反垄断法对于大企业的并购不无掣肘,并不见得都以效率为考量,对于中小企业的进入壁垒的破除也并非不出于公平的考虑。在某些情况下,公司合并可能并不会减弱竞争,而是通过更具效率性而降低了成本,以至于这些合并的收益有时被称为“合并效应”。征诸经验研究的结果,美国昔日反托拉斯法被严格实施,甚至不惜采取拆分的手段,事实上对于经济的发展不利,后来出于效率的考量,这种高压势态才逐渐得以扭转。德国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实施最为严格的国家,其实对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限制较然易见。截至目前,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已屡经修订。从本质上讲,它针对妨碍行为,因此要保护效能竞争,遵循制度保护和个人保护的思想。制度保护作为匿名的监视和控制机制强调竞争维护,个人保护理念机制旨在确保市场参与者行动和决议的自由。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主体不仅包括竞争对手,而且包括作为“效能竞争”公共利益的主体的消费者和公众。从这个角度来看,反不正当竞争法很明显是服务于个人和制度保护的。因此,德国法学界认为,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存在统一的保护目的的基础,使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实质性互动。效率与公平并非截然两橛,此非竞争法两大法域异同之肯綮所在。
在世界上,只有德国、卢森堡等少数国家对利诱性销售行为进行非常严格的限制,而其他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采取原则许可的立场,仅对其中违背竞争法基本原则的行为,即不正当利诱性销售行为进行一定限制。2001年6月29日,德国联邦议会废止了《折扣法》(Rabattgesetz)和《附赠法》(Zugabeverord⁃nung)。但是由于在德国可以依据一般条款对一切违背“善良风俗”原则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提起诉讼,并且先前就已有大量依一般条款对“诱捕顾客”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惩治的案例,因此德国实际上并未放松对不正当利诱性销售行为的规制。“反不正当竞争中心诉C&A时装两合公司案”(Zentrale zur Bekämpfung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 v.C&A Mode KG)即是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2002年1月1日,新的欧洲货币单位欧元开始使用。在举国同庆新年之际,考虑到欧元的引进,德国第四大纺织品服装连锁店C&A Mode KG宣布,从2002年1月2日至5日,授予使用借记卡或信用卡购买其旗下184个专卖店任何产品的客户以20%的折扣,从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广告宣传促销活动。销售商和消费者担心在2002年的最初几天新流通货币的现金量供应不足。因为在此前的2001年12月25日及26日的圣诞及元旦许多人都放长假,私人银行向广大客户及在商业交易中的货币供应较为紧张,所以C&A计划在新年头几天内向选择信用卡非现金交易方式的顾客进行大幅减价。这一行动既能够纾解在收银台因非现金支付产生的延迟,从而节省经销商和部分客户的交易成本,同时也可以刺激顾客解囊购买(在“假日经济”过后的年初第一个月份通常是交易淡季,生意冷清)。基于反不正当竞争中心(Die Zentrale zur Bekämpfung des unlauteren Wett⁃bewerbs)和保护公平竞争协会(Der Verein zur Wahrung des laut⁃eren Wettbewerbs)的申请,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通过临时禁止令叫停了C&A的这一打折行为。反不正当竞争中心将C&A的这一打折行为定性为“特殊促销活动”。C&A辩称,此举是出于方便德国法定货币从马克平稳过渡到欧元的考量。被叫停后,在欧元引入第一天避免顾客在收银台排起长龙,成为店家抗辩的理由。店家拒绝停止打折促销活动,逆势而为,变本加厉,一意孤行继续打折至1月5日,俨然具有负隅顽抗的意向。德国工商协会(Deutsche Industrie-und Handelskammer)同意反不正当竞争中心的观点,认为《折扣法》和《附赠法》虽然已被废除,但如果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规定的特殊促销活动,该打折行为仍然是非法的。按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除夏季和冬季清仓销售以及定期的周年促销,其他特别促销活动本身是被禁止的。借口欧元引进而提供折扣,并没有改变其非法性。德国零售商总会(Hauptverband des Deutschen Ein⁃zelhandels)认为,C&A不应该有精确描述的折扣限制。不寻常的高折扣和客户的限制范围均符合法律秩序,但是,其时间限制不符合法律秩序。倘若服装连锁店给所有使用信用卡或借记卡的客户提供折扣,不将此优惠限制于特定时间段内,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停止提供折扣,促销就不会引发争论。按照德国零售商总会的观点,价格临时改变将迫使消费者改变日程安排,以便冲到专卖店享受降价优惠。在1月4日,杜塞尔多夫地方再次禁止C&A所作出的新优惠,并威胁服装连锁店将对其科以25万欧元的罚款。反不正当竞争中心再次向法院申诉,认为C&A做了修订后的优惠仍明显破坏临时禁令。被告在深化和补充此前提出的证据、主张废除折扣法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关于特别促销活动的规定应被重新诠释,系争销售活动无法被包含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7条第1款的禁止范围。此外,禁止为期几天的各种品种20%折扣,至少与《欧盟条约》第49条不兼容。2002年3月27日,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商事第四庭维持禁止令:初步禁制令申请者的要求成立。杜赛尔多夫地方法院对该行为予以禁止的判决经媒体报道后遭到广泛的质疑,引发了在欧洲大陆的人们对德国和欧洲竞争政策目标的公开激烈辩论,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法律的呼吁如鼎之沸。法律不能成为紧身马甲,经济法的本性就是要讲经济性,不能将效率置之不顾,捆绑经营者的手脚,使之徇然若迂拘之儒。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该案发生不久后便俯顺舆情进行修订,表明对于效率的重视不亚于反限制竞争法。(www.daowen.com)
反不正当竞争法涉及的是通过诸如误导顾客获得优势的行为。通过达成卡特尔协定或垄断以获取卡特尔或垄断利润,则违反了卡特尔法。后者也不是基于效率,而仅仅基于限制竞争行为的存在、创造或运用。由此可见,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否定性判断存在共同性,均以一个普遍的效率原则为基础,违背效率原则的行为在根本上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无论是按照分配正义原则,还是按照交换正义原则,从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协议或者垄断中获利的行为都是不适当的。按照费肯杰的观点,在包括反限制竞争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内的一般竞争法中,一般效率原则构成了非价值判断的依据,而法律归属乃关乎“效率保障原则”(Leistungssicherungsprizip)。与此不同,与经济法相关的法益归属中的非价值判断,尤其是在工业产权保护和著作权法中,以对被赋予的主观权利的侵害为基础。[17]在反对竞争禁阻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保护的竞争,决不仅仅单纯涉及效率。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被分开来的。经济竞争作为价值、作为效率刺激和作为效率表现,在概念上是从作为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意义上的“经济引擎”和作为创新工具和分配机制等使用的经济竞争中分离出来的。即使在有效竞争意义上的经济竞争本身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图像是无可非议的,出于法律的原因对于其作为法律的指导图像的修正仍然是必要的。这里涉及竞争的单一或多元目标问题。尽管市场经济体制讲求公平,但仍无法保证公平。“一方面,由于市场能体现人们以及思想的那种非个人的、相对客观的过程,因此它能较充分地获得公正,尤其是当把它与那些为发挥这些作用而产生的那种并不完善的制度相比时,更是如此。但另一方面,由于具有不同条件的人们对市场的非个人筛选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起点和天赋以及不同的交好运或坏运的机会,因而产生了不公平。”[18]故而,西方经济学有句名言:“效率经由市场,公平通过政府。”这揭示了效率和公平所属的不同分工领域。把垄断放在效率的标准上加以审视,以效率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自然可以使执行竞争政策具有明确的目标。但其间的偏颇也昭然可见。
事实上,对垄断的批判有着悠久的传统,在西方历史上甚至可以追溯到视垄断为贪得无厌的罪孽的中世纪,这种对垄断的指责自然出于分配原因而不是出于效率的考虑。在提交后来作为《谢尔曼法》通过的议案时,参议员谢尔曼呼吁:“既然我们政治上不再容忍国王的权利,那么经济上我们也不应该允许那种阻止竞争、任意制定商品价格的强权。”[19]这显然具有煽情的色彩。尽管芝加哥学派在反托拉斯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波斯纳等人辩称反托拉斯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经济效益和经济福利,但最初反托拉斯法提出时,国会议员大多是律师出身,不可指望他们具有更为深层的经济上的考虑。美国最高法院布莱克法官在1945年的判决指出:“《谢尔曼法》依据的前提是,不受限制的竞争将产生最经济的资源配置、最低的价格、最高的质量和最大的物质进步,同时创造一个有助于维护民主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环境。”[20]德国奥尔多自由主义学派对欧共体竞争法的社会政治价值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按照该学派的观点,竞争法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而且具有政治功能,是创建民主政治的基础。反垄断法的价值是多元价值的集合体,至少可以被分成基本价值和终极价值。反垄断法规范企业经济行为,经济效益自然成了其重要的价值,但经济效益的内涵远较竞争效益的内涵丰富。反垄断法的效益价值包含了对所维护的经济关系的效益和反垄断法制度的法行为的本身的效益两方面。正是这样,欧盟竞争法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三大目标。欧洲学者之所以使用范围更广的“经济效率”一词代替“竞争效率”,就是为了使欧盟竞争法的经济和社会目标能够充分囊括从经济增长、增强经济竞争力、促进就业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分配的公平、对消费者的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等方面。易言之,出于法律的原因所期望的竞争保护可能不仅仅涉及效率,而且关乎中产阶级的保护、欧盟统一市场政策、发展性援助的目标等等。竞争也许并非在所有情况中都是在经济学效率意义上的“有效的”。
随着经济学对市场垄断与效率之间关系分析的深入,以美国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资本集中未必反竞争,高利润未必是反竞争的结果,反而可能是高效率的结果。规模大和市场份额高的企业本身并不必然违法,相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往往是市场竞争的幸存者,是具有效率和活力的表现之一。基于此,反垄断法的目标应该定位于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其规制重点应放在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经营行为上,以防止这些经营者滥用优势限制市场竞争。受到芝加哥学派的影响,美国反垄断法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的规制从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在德国,为了适用《反限制竞争法》第22条以及解决滥用评估的困难,彼得·乌尔默提出应该采纳“效能竞争”的概念:当一个对其他企业都开放的行为并不是以较好的效率为依据,而是以效率以外的实践为立足点,则令市场控制者承担滥用权利的责任。联邦卡特尔局出于管辖职权的原因而对此颇感兴趣,在1977年的工作报告中以冗长的论述阐明这一问题:“因为市场控制企业通过更佳的效率以获得竞争领先也是被竞争秩序所接受的,边界可以仅划定在非效率的实践。”[21]彼得·乌尔默和联邦卡特尔局的观点是基于事实上建立在普遍效率原则上的一般竞争法的推衍,是基于对第22条滥用市场控制地位和效率关系的误解。尽管效率思想在竞争法中作为否定性评价的一般指南,不正当优势以及卡特尔和垄断的收益并非基于效率,但该法域所基于的一般的否定性评价的理据并不能推演出事实上的“效率”和“非效率”的划分,并由此断言《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条的不正当性评断、《反限制竞争法》第22条的滥用权利判断、《反限制竞争法》第37a条第3款的竞争妨碍判断均取决于此。将“正当”等同于“效率”对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应用是不恰当的。赔本销售和不适当的广告等非效能竞争,在原则上也是正当的。与此相反,为排除在这种意义上的非效能竞争的卡特尔按照《反限制竞争法》第1条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EWGV)第85条第1款却是违法的。如果人们为了防止非效能竞争而允许卡特尔的话,那么将会产生汹涌澎湃的竞争妨碍的结局。这也是彼得·乌尔默所不赞同的结果。引入“效能竞争”这样一个如此宽泛的概念,并不适合于卡特尔法部分的领域。
在市场上的单纯依赖削价阻抑竞争对手尚不构成违反善良风俗,这毋宁是市场竞争的常态,但是有计划地摧毁特定竞争对手的削价、以少数商品削价作为诱饵的欺骗消费者的削价、通过大规模的馈赠或者削价营造不可克服的进入壁垒,损坏市场关系的竞争,便可能成为不正当竞争。然而,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正当竞争的边界对于大企业和小企业是一体适用的。这在卡特尔法中则存在着不同,在这里大企业在某些情况下是被禁止的,不以具有道德上的可责性为必要条件,而小企业则是被允许的。“宙斯所能做的并不意味着公牛也能做。”(Quo licet bovi non licet Jovi.)就一般而言,这种规制源于卡特尔法的基本思想,即弱势企业被允许,而市场支配和市场优势企业则被禁止。即使竞争行为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上合乎效率,但在卡特尔法上可能构成大企业滥用其市场控制或市场强势位置。这与此种大成问题的竞争措施的效率特性并无关系。关键的只是一个企业在竞争行为的介入方式,大企业由于较诸小企业规模庞大,可能在市场上造成其他影响。效率正义的概念因此对于评价《反限制竞争法》第22条和《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EWGV)第86条市场控制或市场强势的企业滥用权利行为的评估在原则上是可能脱离和拒斥的。只要明文规定的滥用权利存在,市场控制或市场强势的企业即使通过更好的效率获得竞争秩序中的领先地位也是不能“被接受”的。市场控制企业可以通过诸如“正常”的批发折扣等,以便与效率原则相符合,但当这样的行为将小的竞争者逐出市场或构成进入市场障碍时,则是不允许的。忠诚回扣最大的反竞争效果是类似独家交易排除效果。占支配地位的经营者通过追溯回扣人为地提高了顾客的转化成本,可导致与排他交易类似的约束效应(「吸引効果」,suction effect)。如果有问题的忠诚回扣覆盖市场,仅妨碍竞争者规模经济的达成和有效率的流通手段的获得,在市场上提高竞争力的成本。[22]一个大企业相对于一个小企业的位置取决于滥用权利的界限,而非竞争领先是否“获得更好的效率”。所以“边界只能划定在非效率的实践”也是不正确的。这个界线毋宁说是横贯于效率正义实践和非效率正义之间的。易言之,“效率”是与市场权势两相独立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