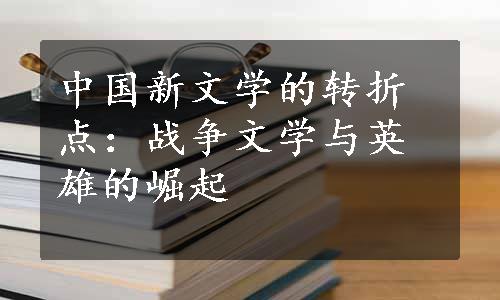
《陇海线上》甫一推出,就引得“民族主义文学”阵营一片赞誉之声。有人激赏其为足以与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相颉颃的“伟大战争小说”,它“将亲临战地生活,及战争之真面目,冲锋陷阵之状况,士兵之心理,描写尽致”。[10]更有人认定这是一篇压倒雷马克《西线无战事》的力作,此乃作者亲身投入战斗后的纪实,因而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1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论者之所以将《陇海线上》与《西线无战事》相比较,原因在于后者是风靡世界的“步兵底史诗”,“可算是巴比塞底《火线下》以后最伟大的战事小说”。[12]这部小说“在中国也可称盛极一时”。德文版单行本问世不到一年,中国就先后出现了洪深、马彦祥(现代书局)及林疑今(水沫书店)两个译本。据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也在上海南京大戏院热映,连映十天还是场场爆满。[13]1930年春,郑伯奇、夏衍等人主持的“上海艺术剧社”还曾将《西线无战事》改编为同名话剧在上海北四川路东洋演艺馆公演,一时“颇为轰动”。[14]而雷马克紧随《西线无战事》之后推出的姊妹篇《战后》在中国也是一纸风行,先后竟然出现了光华书局等七个中译本。[15]
由此看来,“民族主义文学”阵营普遍将《陇海线上》视为一部优秀的“战争小说”,不过与雷马克的“非战”迥异,他们鼓吹的则是“主战”。就在《陇海线上》发表的几个月后,曾有论者猛烈抨击以《西线无战事》为代表的非战论调,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反军阀、反封建、反帝都需要正义之战,为唤醒民族意识,文艺的首要而急切的任务就是“关于民族求独立自由的战争底讴歌”。[16]朱应鹏也激烈抨击“文艺上的非战运动”,认为“战争至少在现代是绝不可避免之事,‘化干戈为玉帛’,不过是一个白日梦而已”,“如果说为民族求出路而战的话,那么战争也未始不可以歌颂,并且就现在的中国情形而论,似乎我们还没有‘非战’的资格”。[17]
而“民族主义文学”阵营之所以形成如此共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往的中国新文学中缺少“主战”的战争文学以及以“尚武”精神为核心的英雄叙事,相反“在文艺上反对战争,已经成为时髦之事”[18],就连那些流行于沪上的外国电影,也“多采非战主义,讥讽兵士的生活”。[19]而考究起来,这种“非战”主义的流行,一方面固然缘于“欧战”之后西方反战思想在中国的流布,然而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在经历多年的军阀兵燹之后,“大众对于战争发生厌恶的心理”。[20]1927年的《小说月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英雄》的讽刺小说,主人公“张军需”只有在捉奸与通奸的床笫之间方显“英雄”本色。[21]即使到了“北伐”时期,讨伐军阀的统一战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媒体也开始宣传参加“国家之兵”的爱国义举,[22]但笼罩在国人心头的战争阴霾却难以散去。而此时“战争文学”的代表作——孙席珍的中篇小说《战场上》虽以“北伐”战争中最为重要的汀泗桥战役为背景,但其主人公黄得标却是一个“老于行伍,笨而胆小”的底层士兵,小说仍以细腻的“战争恐惧”书写见长。[23]
但逢《陇海线上》发表之时,正如《前锋月刊》编者所言,在此弱肉强食的世界局势之中,面对中国风雨飘摇的国际地位以及日趋消极和沉闷的民众精神,中国正热切呼唤着“富有兴奋刺激性的战争文学”。[24]而《陇海线上》以亲历者身份直接、深入地叙述了“中原大战”,正好满足了“民族主义文学”对“战争文学”与“英雄”的期待,因而一经发表就被树立为标杆和旗帜。(www.daowen.com)
《陇海线上》这部小说不仅对战争有着写实性的描写,它更为当时的人们呈现了一个英雄的谱系。在这当中,投笔从戎的主人公“我”无疑是位英雄,不过作为一位军校新兵,“我”是在战争中认识战争、在战斗中学习战斗的“成长者”,而那些久经沙场的白俄军人才是每次战斗必打头阵、披坚执锐的主力,更是“我”努力学习的榜样。他们大都英勇善战:有“不怕死,专门做无畏的冒险”的佘干科;有虽然皮肤白嫩、神经敏锐、爱修饰、好虚荣但却是征战好手的驾雀罗夫;而小说中最为英勇的白俄军人当数哥萨克巴格罗夫,此君虽然在太平时期是个“最酗酒闹事的坏蛋”,在战场上却是“不怕死的兵”,但巴格罗夫并非匹夫之勇,他是训练有素的职业军人,此人“生长于俄属的黑龙江省,一世以兵为业,举凡老兵所应有的常识,他都应有尽有”;除此之外,排长谢立洁则体现了另一种更为重要的职业军人素养——严守军令,正是他“发出的严厉的口令,好像责罚的棍子般,将我一切偷生怕死的思潮完全驱走”。
白俄军人是行动勇猛的斗士,但同时他们内心更保藏着对于战友和祖国的深沉情感。在小说中,叙述人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描述“我”与白俄军人的友谊,但“我们”的友谊并非来自某种意识形态的感召,而是在激烈战斗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袍泽之情。巴格罗夫常在行军的间隙照顾“我”,严寒中送上毯子和酒。一次行军中,“我”不慎出现驾驶险情,多亏谢立洁排长手疾眼快拉住“我”的摩托车,否则一定会摔下山崖,粉身碎骨。而当部队给养不能及时送到,士兵们因饥饿而叫骂之时,又是谢立洁排长自掏腰包,让大家能够果腹。不过,虽同为战友,白俄军人却是漂流在外的异国人,因而,每当夜晚露营的时候,那悲伤的怀乡之曲总是让人感动至深。佘干科高歌的《白蔷薇》“将艳丽而失望的音波送到每个人心中的最深处”,谢立洁“那沉重的Baritone歌喉”更是让“我的灵魂也是多么的受了深巨的刺激”,唱出了“故乡的惓恋,亡国的悲哀,以及流浪漂泊者的心情”。而对于这位与“我”关系最为“密切”的排长,“我”既钦佩又同情,钦佩他持重、睿智和过硬的军事本领,同情他漂泊的身世和亡国的悲哀。[25]
由此看来,这些白俄军人凭借“英勇善战”的战斗能力,“关爱战友”的袍泽之情,以及“眷怀祖国”的民族精神成为军人的典范,他们是“中原大战”中更为功勋卓著的“讨逆”英雄,也正是因为这重英雄身份,他们才获得了参与乃至主导《陇海线上》这一“革命”文本的正当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