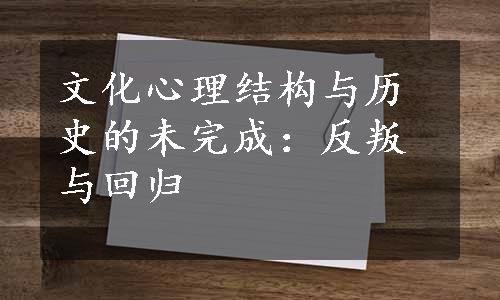
黑娃的结局令人唏嘘,但其意义在迄今为止的评论中并未得到充分讨论。在此悲剧之前,他已经经历了巨变:从土匪变为儒家传统中的“好人”。他最后的回乡祭祖,既是向传统文化思想的忏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然而,黑娃的转变显得太突兀,以致我们只能自己推断他的改变的心理因素。
儒家文化对其潜在的影响是我们首先考虑到的。黑娃毕竟是在白鹿原上长大的,他耳濡目染的是“乡约”的礼数,他从小接受的就是“耕读传家”的儒家教育模式,感同身受的是儒家文化无处不在的精神影响。也许,他无法跨越这种自小的尊卑长序关系。因此,有评论者认为:
文化是根无形的套绳,其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却又无任何踪迹可言。当他成了儒家文化的背叛者,文化也给了他沉重的心理负担。他的放纵,他的发泄,实际都是在力图摆脱儒家文化的影响,所以当再次面临选择时,黑娃自动地选择回归儒家文化是必然的。[34]
对此,陈忠实自己的解释是:
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不能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以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35]
从作者自身的创作角度出发,黑娃的信念无疑是恪守儒家文化的。为此,作者这样描写他:
迎娶秀才的女儿,是黑娃向儒家文化迈进的第一步。他残忍地摒弃以前的旧习性,将自己捆绑在炮筒上整整五天五夜,汤水未进,成功戒烟,显示了文化给人无以伦比的精神动力。他在知书达理、温柔端庄的妻子面前所感到的自责、畏怯、空虚、愧疚,是对自己荒唐过去的否定与懊悔,更是面对儒家文化理性光芒时的真实心理写照。而为了弥补这种心理落差,黑娃选择了学习,他师从大儒朱先生,抱着为“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的信念,晨曦舞剑,闲时读书,与朱先生畅谈人生。他牢记古代圣贤们的哲理,强迫自己具备成为好人的素质,诚心实意地学习并吸收着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也使得他“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出一种儒雅气度”,真正完成了人生的蜕变,拥有了“白鹿”所具有的洁净、善良、仁义、真诚等美好品质。
遵循着作者的思路,评论者这样认为:“他的这种自觉反抗只是自己本性盲目的一种表现。他只是认为是白嘉轩和祠堂乡约让他被白鹿原所不容,失去美好的生活,却不能从根本上去思索造成自己这种生存环境的根源和自己参加革命反抗的意义。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盲目的反抗、缺乏意识的反抗导致了他的反抗的失败。最后还是倒在了自己‘回归’的人生之路上并跪在了朱先生的脚前,竟然死在窃取了解放后第一任县长的白孝文的手中。可以说他终身反抗命运,最后还是屈服于命运;他反抗宗法礼教,最后还是成为朱先生的关门弟子,这也为他的自我觉醒并向往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最终他还是成为了一个盲目的反抗者。”[36]
然而,在我看来,黑娃的“转变”只有我们结合九十年代以来的时代才能得到理解。换句话说,他的“残余心理结构”实际上是当前时代的心理结构的回声,是由于历史的“未完成”的投射。而另一方面,辩证的认识在于,他死于皈依传统文化和仕途顺利之际,这不但表明传统封建治理的冷酷(它让我们想起宋江的结局),也暗示他的皈依不合时宜:现代性的演进,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资本主义自利原则(他的死是白孝文为了自保而设计的)没有让传统道德有生存的余地。
这个未完成的历史与黑娃的结局紧密相关。白孝文自从被逐出族门,沦为乞丐,他一方面成为“(男)人”(八十年代以后流行的人性话语——而这一话语是自相矛盾的:同样自信的族长白嘉轩的“雄风”显然远超过此时的他,因此他要到此时才能为人不过是观念的投射);另外一方面却丢掉了任何伦理道德观念,生存成为最高道德(讨饭的时候被作为反面教材给孩子们展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侮辱,可饥饿使他对饭食以外的一切熟视无睹,能够“忍辱负重”)——在这个意义上,他象征着失去旧的传统世界后,无新的道德可遵循,不择手段以自保的一群。与其说他是“封建残余势力附身的代表”,不如说他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www.daowen.com)
因此,他上升的过程让我们想起西方许多描写现代资产阶级人物不择手段往上爬的经历:在担任保安团营长时,为邀功拼命地抓共产党;而当黑娃(三营长)和二营长被作为共产党代表的鹿兆鹏策反之后,他已是势单力薄,他认为自己如果不同意起义的话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死,当即当着兆鹏的面表示愿意起义,“其实我早就琢磨着想找你商量这事了”。他不但翻脸不认人,而且心狠手辣,身为张团长的心腹,为了消除兆鹏和黑娃的猜疑并保全自己,他毫不犹豫地向张团长开了枪,而且把致命的一枪补在了后者的脸上!其手段非同一般。[37]经过钻营,他最终得以出人头地并且当上了县长。他陷害黑娃可以看作是他报复家仇,也可读作是作为一个阶级的复仇。为了功名利禄,他可以出卖任何人,包括儿时最铁的玩伴;可以欺骗任何人,包括前来求情的白嘉轩。论者敏锐地看出,他所做的一切“貌似不合常理,其实它是儒家文化中非人道一面扭曲的表现。保守,势利,惨无人道……以血淋淋的自残和残他的方式”[38]表现出来。但这一论点没看到他最终变成了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一个心狠手辣、狡诈阴险的政客。
黑娃的向儒家传统的回归象征着传统文化心理的残余;而他的冤死象征着历史的未完成;白孝文没有交代的结局的意义作者却没有明示。显然,二者间有着值得探讨的深意。有的评论者认为,黑娃的冤死和白孝文的升迁“象征着封建残余力量对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威胁”。但是如果问起白孝文(可能)的结局,我们很容易判断,这个潜进革命队伍的无道德观念的个人主义者(由于其阶级出身,也由于其在反动政府中的经历),无法逃过往后的政治运动,无论他怎么狡诈地掩饰。如果是这样的话,作者的设计——善无善报、恶无恶报——表达了他什么观点?
这个观点就是现代史无非是“折腾”的历史观。这个观点由小说里的传统智者朱先生清晰地表达。他曾经明确地将现代中国三股势力统称为“鏊子”。
白嘉轩向姐夫朱先生详细说了他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土匪白狼就是黑娃!”
“噢!这下是三家子争着一个鏊啦!”朱先生超然地说:“原先两家子争一个鏊子,已经煎得满原都是人肉味儿;而今再添一家子来煎,这鏊子成了抢手货忙不过来了。”
白嘉轩听着姐夫的话,又想起朱先生说的“白鹿原这下变成鏊子啦”的话。
那是在黑娃在农协倒台以后,田福贤回到原上开始报复行动不久,白嘉轩去看望姐夫企图听一听朱先生对乡村局势的判断。朱先生在农协潮起和潮落的整个过程中保持缄默,在岳维山回滋水、田福贤回白鹿原以后仍然保持不介入不评说的超然态度,在被妻弟追问再三的情况下就撂出来那句:“白鹿原这个成了鏊子啦”的话。白嘉轩后来对田福贤说这话时演绎成“白鹿村的戏楼变成鏊子啦”。白嘉轩侧身倚在被子上瞧着姐夫,琢磨着他的隐隐晦晦的妙语,两家子自然是指这家子国民党和那家子共产党,三家子不用说是指添上黑娃土匪一家子。[39]
作者对朱先生的“超然”并没有给出什么评论,但在他的洞察世事变迁的超人能力上,作者的描写显然让他呈现为一个哲人、圣人。这尤其在他预见死后自己坟墓将被扰动,而预先给那些“捣乱者”留下名言“折腾到何时为止”,这让“学生和围观的村民全都惊呼起来……”[40]。然而,惊呼的不是学生和村民,而是其时的作者和整个社会:在这个渐成社会主流的舆论和意识形态下,中国现代史是一部折腾史,“不折腾”成为去政治化的八十年代里,后革命世俗社会向全球资本时代的后社会主义过渡的主流“共识”。这个小说,正是在这个历史大转折中出现并得到评价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