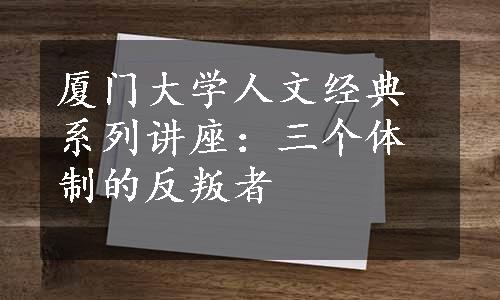
“纵使社会革命的势头再猛烈,它也只是宗法制消退的催化剂,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因。宗法自身的腐朽和落后致使它在社会革命的压力下无法自支,白鹿村的村民们开始了挣扎与反抗,宗法在白鹿村内部开始呈现出礼坏乐崩的衰式。”[30]形形色色的欲望驱使着芸芸众生投身于各种社会事件、人事纠葛、党派斗争。这个分裂在统治者内部和草根社会同时发生。
即将成为新一代的族长白家长子白孝文原是白嘉轩按照传统精神培养出来的理想的族长接班人,他在祭祀祠堂时举止端庄得体,在族人中树立起威望。但他并不像其父亲那样,把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自己的一种内在需求。在被小娥诱惑受罚之后,他丢去了宗法理想。曾经坚不可摧的神圣宗法已经不能有效笼络住人的心性,彰显出破败之势。小娥不仅给予他肉体上的极大愉悦,还使他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白孝文的这句话不是他的“破罐子破摔”的自暴自弃之语,而是表明了他在失去宗法枷锁,精神上获得自由后的某种“自然”感觉。这些是他在过去的森严的等级生活中无法得到的。此时的他身败名裂,继而卖房卖田,甚至落到沿街乞讨、被恶狗追食的地步。但是,白孝文的反叛并不是对旧社会自觉的反抗,而是饱受压抑后的不自觉的爆发。这表明他在“欲望”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新的为人处世的“道德”在生成中,他的命运并不就此终结,而是还有待发展。
不但新的一代族长难以继承祖宗基业,而且奴仆的下一代也难以保持“忠孝”。田小娥的相好是黑娃,后者是“白鹿原上最好长工”鹿三的儿子。忠仆鹿三的幸福的奴隶意识曾经意图传之于下一代:他对儿子说:“黑娃,爸说你听着,你到嘉轩叔家去熬活:爸回咱家来,忙时做咱家的活,闲时出去打零工。”他总以为父辈是白家的长工,自己和儿子也应该是。但这个被认为理所当然百世不易的“天理”却受到了后代的拒绝,而且这个拒绝并非受到外在“怂恿”(如党的“翻身做主人”的教育),而是来自于一种“本能”的反抗。这种反抗甚至自黑娃小时就开始,以致显得令人不解。
黑娃从小倔强、执着、反叛、生性好动而不安分守己。宁可去山上割草也不愿上学堂念书,表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怪脾气。作为苦水里长大的孩子,他蒙着主子的德政(白嘉轩亲自劝鹿三让他读书,这个始料未及的举动让鹿三感激涕零:“黑娃你要实在不好好念书,我把你狗日……”),自幼就和两个族长的儿子一起上学。在周围都是富家子弟的情境下,他的心理差距巨大。白嘉轩的“好意”出于培养对礼教有意识忠诚并以“学识”来维护的下一代(鹿三还只是无意识的,他显然不满足于此),但白家的资助却让其自尊感到不安:白家兄弟的冷面也让他感到别扭,所以他主动搬凳子远离白家子弟,而和更可亲的鹿家兄弟靠在一起(这个细节其实暗示了白家子弟将成长为传统的卫护者,而鹿家子弟将成为和他结盟的社会新力量)。但鹿家大公子鹿兆鹏的给他的“冰糖”和“水晶饼”让其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所以第一次吃冰糖时,“呆呆地站住动也不敢动了”,“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起来,竟然哇地一声哭了”,贫穷的他无法想象有这么可口的食物;他发誓“以后有钱了一定要买一桶冰糖吃”!而吃水晶饼时更“觉得身上又开始颤栗,而且迅速传导到全身”,而咬牙直接把它扔进了草丛,免得他“夜里做梦都在吃,醒来流一摊涎水”。以至黑娃最后沦落为土匪打家劫舍时,命令弟兄们用手掏出吞到嘴里的冰糖,往装冰糖的洋铁桶里浇了一泡尿。对于贫乏的悲哀使得他无法获得占有的幸福感。这一情节充分宣泄了他作为贫苦人的一种本能的仇恨。然而,这些出于“自然人性”话语的描写虽与此前历史小说的阶级压迫书写迥异,却让读者很难明白他反叛的“天然性”,相反觉得是种怪异之举。
如果说这个细节暗示了他的不同寻常的性格,那么他拒绝到白家打工的理由却更明白地露出他“天生反叛”的苗头。他对地主有一种本能的仇恨。他虽从小就“知道白家对自家好却总是怯惧”;因此,到十七岁时,他主动担起了家庭重担,但坚持到外边去打长工,而不在白家干活,因为“嘉轩叔的腰杆挺得太硬太直”。这是他对传统文化的畏惧、逃避和反抗。他想摆脱这种精神上的压迫,以彻底摆脱白家在他心中所造成的自卑,树立起自己的自尊。(www.daowen.com)
他去离家很远的郭举人家做长工,在郭家,听到了郭家小妾、实则性奴的田小娥的“泡枣”事件,激起了弱者之间的怜悯,产生了由衷的同情。而当小娥引诱他时,这位力图自尊自重的青年陷入了为难:一方面他割舍不了与小娥的感情,一方面又碍于主人的知遇之恩和儒家的“忠义”思想而自愧自责。当携带小娥逃离了郭家,小娥的父亲答应了黑娃的求婚,两人得以结合的时候,黑娃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是当他把小娥带回原上,不但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见不得乡亲们的面,还被父亲撵出了家门。尽管这样,黑娃还是固执地遵从了自己的感受,选择了对抗,栖身在村东头的一孔破窑里享受着家庭的温馨。但接着外界的力量又把他卷入了农民运动,以及其后的被追捕的厄运。战败后他只好上山当土匪,喊出了“堂堂白鹿村出了我一个土匪”的痛哭声。他的忏悔般的自责表明他的反抗一直是无意识的、盲目的,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命运:保安团招安,他又做了保安团长,开始寻求另一种生活,娶贤妻、拜恩师,并对自己的过去,对和小娥的爱情给予了彻底的否定。他回乡祭祖时,更表现出与白孝文的本质不同的真诚的悔过。他的这些行为都反映了他反叛中的无意识性。正是这种无意识性,使他感到无所适从、彷徨、失落,于是希望从传统文化精神中寻求某种慰藉;也正因此,他不但被传统收编,也被传统所转化成的新道德所害,最终成为政客阴谋的牺牲品。然而,上述的叙述都只是基于小说文本的初步分析,在下面进一步的剖解中,这个人物描写将被质疑。
旧体制的垮台最终需要来自于体系内部的自觉的反叛者。因此小说中的第三位反叛者始终自觉自立,她就是白家的大小姐、为白嘉轩所钟爱的白灵。如果说,书中的其他两位女性和黑娃一样,都在不自觉的反抗中被体制杀害——鹿兆鹏的被家庭强加的媳妇畏惧于传统礼教的威力,只能让越燃越炽的情欲之火吞噬自己的理智,在理与欲的矛盾挣扎中走向疯狂,最后被父亲冷先生下重药毒死(以遮掩丑闻);田小娥因不甘于屈辱的境地,大胆追求欲望的满足而得罪传统礼教,惨死于公公之手(它们都让我们想起了路翎四十年代的《饥饿的郭素娥》和曹禺的《原野》[31])——那么白灵则是一位新“新女性”。因为她既不同于不敢越出礼教的雷池一步的前者,又不同于叛逆行为主要局限于情欲层面,且必须依赖男人来进行反抗,缺乏自主性与独立性,几乎出于自己的本能而为之的后者。她既有对情欲选择的自主性(五四文学的“新女性”主题——自始至终就对“父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礼教戒条持坚决反抗的态度,理直气壮地敢于和鹿兆海私订终身,当她后来发现鹿兆海与她志不同道不合时就毅然决定分手,大胆地与志同道合的鹿兆鹏结成患难夫妻),也有自己的生存能力、生存方式,不必像小娥那样不停地为自己寻找生存的依靠。她有主见,实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实现了自己的独立地位。甚至不仅仅如此,她的反抗的最高境界是对既定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反叛——她甚至已经超越了丁玲所创作的“后五四文学”中“革命女性”对革命事业的异己和陌生感,把革命理念作为人生和理想之本。如果说,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白灵和鹿兆海这一对情侣用投硬币的方式决定各自的政治选择,白灵选了国民党而鹿兆海选了共产党,还只是对“理念”认识不深的尝试,那么在国共分裂后,当权的国民党政府抓到共产党员就塞进枯井的行为刺激了白灵,让她在大是大非面前重新选择了共产党,宁愿过着危险的日子,却是完全有意识的(由理论支撑)的信念。
小娥和白灵都是那个时代里头对旧的体制、精神、心理等所有观念的背叛者。但白灵的背叛是自觉的,她拒绝缠脚,进城接受新式教育甚至与家庭决裂去参加革命,主动地、自觉地参加革命,表明她不但接受了五四新文化,更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新的理论,因此她的背叛在态度上很坚决,在行动上也敢于公开地与父亲对抗。她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绝不妥协,始终捍卫着自己的个体意识和个性尊严,敢爱敢恨,包括她对兆海和兆鹏的再选择,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官员,她扔出了手中的砖头!她的自觉精神表明她是全新的具有反叛精神的“新女性”。
叙述者告诉我们,白嘉轩曾经觉得当对待这个拒绝他的指令的女儿时,他似乎面对的是“一个与他有生死之仇的敌人”。反叛者的出现预示着传统世界开始内部崩塌的过程。尤其是统治者内部的堕落和叛变表明,这个体制再也无法依靠白嘉轩这样的阴阳两面的铁腕统治加以维持了。巨变已经在发生。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