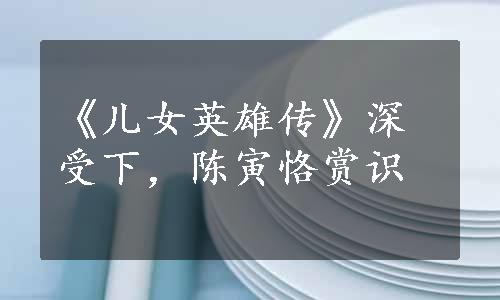
对一部小说的兴趣有相当程度的个人原因,这其中有个人身世、经历、知识结构以及欣赏趣味等,有时候与小说本身获得的一般社会评价并不相同,所谓有一千个人即有一千个莎士比亚是也。但在中国现代学者中,对一部旧文人的小说有大体相同的评价,却不能简单说是欣赏趣味所至,而其中必定包括了复杂的因素。
陈寅恪认为中国旧小说中《儿女英雄传》最好,甚至“转胜于曹书”,这个评价是目前已知的对《儿女英雄传》的最高评价,当否可以讨论,但陈寅恪这个见识却不能不引起研究者注意。一个中国第一流史学家的意见,总有它的道理,哪怕是个人偏见,也必有引人深思之处。
陈寅恪自己讲,他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是有感于中国长篇小说结构不如西洋长篇小说精密,也就是中国长篇小说结构失于简单,他举了《水浒传》《石头记》《儒林外史》等书,认为“其结构皆甚可议”。但对《儿女英雄传》,却认为“殊为例外。其书乃反《红楼梦》之作,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然其结构精密,颇有系统,转胜于曹书,在欧西小说未输入吾国以前,为罕见之著述也。”
从陈寅恪这个看法判断,我们或许仅能看出他是由纯粹技术角度来肯定《儿女英雄传》,这个观点与冯友兰的看法相同。冯友兰也认为《儿女英雄传》思想不行,但描写有特点,有现代西方小说的手法。这也差不多是当时喜欢《儿女英雄传》的新学者们的基本看法。
应当说陈寅恪对《儿女英雄传》的评价,除了小说在结构和叙述上的长处外,对于小说的内容,陈寅恪也没有像他同时代人如鲁迅、胡适、冯友兰等,认为写法不错而思想完全不行。我们要注意,陈寅恪谈及《儿女英雄传》主题和思想时,只是说“世人以其内容不甚丰富,往往轻视之”,言外之意似有此判断失之简单的意味。陈寅恪关于《儿女英雄传》的所有记述中,从没有否定此书思想内容的观点,这虽然不能说明陈寅恪就完全认同此书的思想,但至少说明陈寅恪对此书主题和思想内容并不像世人那样反感。这是个人阅读趣味,但也有个人身世之感。
陈寅恪认为《儿女英雄传》是“反《红楼梦》之作”,这个看法其实并非陈寅恪独创,而是延续了胡适的观点。这里尤需注意,陈寅恪谈论《儿女英雄传》最多的时候,恰是1954年批判胡适运动前后,他肯定胡适对《儿女英雄传》的意见,可能也暗含了对这位老朋友的怀念。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对《儿女英雄传》的看法是“其情况盖与曹雪芹颇类。惟彼为写实,为自叙,此为理想,为叙他,加以经历复殊,而成就遂迥异矣”。[14]与胡适观点大体相同。
1925年,胡适为亚东书局刊印《儿女英雄传》写序,他肯定这部小说在语言上的成就,认为“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同时也肯定本书有相当丰富的社会史料,但胡适也指出这部小说的思想非常浅陋,“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做的如意梦”。胡适说“依我个人看来,《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肯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15]
陈寅恪深赏《儿女英雄传》,其实有他自己的身世之感在其中。作者文康是旗人官宦子弟,此点与陈寅恪的身世大体相同,以往研究陈寅恪的学者都倾向于认为陈寅恪身上有遗少气息。陈寅恪也说过自己“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16]《儿女英雄传》恰好成书于这一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儿女英雄传》叙述的家庭情景及女性表现与陈寅恪自己的经历和理想相合。
《儿女英雄传》中的安学海是一个理想形象,他饱读诗书,刚正不阿而又通达人情。在文康笔下,安学海是一个理学先生,是一个好官,他教育子弟也是以科举正途为晋身之阶,从不搞歪门邪道。此点与陈寅恪的家世背景也相符合。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有科举经历,陈三立还是进士,陈寅恪一度在祖父身边,从小在旧家中长大,“父执姻亲多为当时胜流”,虽大家族而其乐融融,所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之处有切身体会。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明确表达:“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犹希腊柏拉图所谓说的Eid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17]他晚年撰写《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于知恩当报一类小事均记忆极深。[18]
《儿女英雄传》是文康构建的一个中国旧家的理想世界,虽然其中偶有因果报应和“作善降祥”的情节,偶失荒诞,但因为书中文康将自己及家族的真实经历写出,叙述得相当真切,所以在文化理想上暗合陈寅恪的思想境界,而常常引起陈寅恪的怀想,这可能也是他习惯用本书材料作为考证工具的原因之一。(www.daowen.com)
陈寅恪对他早年学生中不能坚持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一事,非常敏感。1954年3月,陈寅恪开始写《钱柳因缘诗释证》,在本书第一章“缘起”中抄录了多首自己的诗。其中有1963年冬天写的两首,其中一首有两句:“高家门馆恩谁报,陆氏庄园业不存。”这两句诗常为研究陈寅恪的人提起,一般认为这是陈寅恪对当时“学生批判老师”的感慨,此诗后一句是陈寅恪著述中常出现的典故。
陈寅恪著作中,经常引述唐代李亢《独异志》中的一个故事。崔群是贞元八年名相陆贽所取进士,与韩愈同榜。后来仕至宰相,为官清正。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崔群以礼部侍郎知贡举,录取进士30人。崔群夫人李氏曾劝他置一点庄田,“以为子孙之计”。崔群笑答:“余有三十所美庄良田,遍在天下,夫人何忧?”而崔夫人却反问“你不是陆贽的门生吗?”崔群回答说:“是啊!”崔夫人说:“往年你身为知贡举,却派人告诉他儿子陆简礼不要应举,以免引起非议。如果门生真是美庄良田,那么陆氏这一庄算荒废了。”崔群闻听此言,很觉对不起自己的座主。陈寅恪中山大学《唐史讲义》中“科举制度及政治党派”条,抄录了崔群的故事和白居易的原诗。白诗最后两句是:“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酬恩。”[19]
因为陈寅恪对自己学生迎合时代非常反感,这样的现实情景最容易唤起他早年阅读《儿女英雄传》中门生对座主情感的记忆。所以才有1950年9月18日给吴宓的信中那样的感慨。《儿女英雄传》此回叙安学海在山阳县河工知县任上,为人陷害,后得学生乌明阿重金帮助,陈寅恪向吴宓提这个典故,意思甚明,他的学生指望不上,而“有财力足以济人之急者皆已远走高飞”。了解这个背景,则能理解陈寅恪1954年给科学院答复中“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20]一段话的深意。
陈寅恪深赏《儿女英雄传》,是他在心理上认为小说虽以理想笔墨写出,但与他感受过的真实生活相近,而他对这种生活始终保持温情回忆。《儿女英雄传》一书中,以中国正统文化为基本底色,无论男女,无论为官为民,忠诚信义和保持节操是作人的基本道德,“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这恰合陈寅恪“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境界”的判断。
另外一个细节是陈寅恪对待女性的态度。1949年后,陈寅恪旧诗中凡涉及女性主题,均出于真挚赞美,他说自己晚年“著书唯剩颂红妆”,看花听戏经常发出的感慨是“西江艺苑今谁胜,不是男儿是妇人”[21]。《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的主旨都是赞美女性,而这一主题恰也是《儿女英雄传》中的主题,在此书中无论金凤、玉凤,还是安学海、邓九公身边的女性,个个都是“温柔儿女家风”,这与陈寅恪一向推崇的“家风之优美”极相符合,这可能也是陈寅恪深赏《儿女英雄传》的一个深层心理。
陈寅恪晚年多讲崔群故事,其实还隐含一个判断,即女人常常较男人更有见识,其中暗含了对1949年之际陈夫人、妹妹陈新午决断的钦佩和自己没有离开的悔恨之意。陈寅恪的去留问题曾引起过争议,主要是因为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当年出版时曾有删节,后出的《吴宓日记续编》中其实已将此事言明。1961年9月3日的吴宓日记中说:“陈序经畅谈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论张伯苓、仲述兄弟及何廉;又详述陈寅恪兄1948年12月来岭南大学之经过(由上海来电,时序经任校长、竭诚欢迎)。到校后,约在1950年一或二月,筼嫂力主往外国(欧、美)或台湾,竟至单身出走,至港依David及其诸妹,序经追往,遍寻,卒得之于九龙一无招牌之私家旅馆,见筼,与约定‘必归’。序经乃先归。俟其夫妇感情缓和,乃遣人往迎归。”[22]此处David即俞大维是陈寅恪的表弟也是妹夫。1952年2月,陈寅恪有《壬辰广州元夕收音机中听张君秋唱祭塔》,其中第一首:“雷峰夕照忆经过,物语湖山恨未磨;唯有深情白娘子,最知人类负心多”[23],表达的也是对女性的赞美和钦佩。
陈寅恪深赏《儿女英雄传》对待女性的态度,此点与周作人的看法相合。周作人说:“《儿女英雄传》还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的,近来重读一过,觉得实在写得不错。平常批评的人总说笔墨漂亮,思想陈腐。这第一句大抵是众口一词,没有什么问题,第二句也并未说错,但是我却有点意见。如要说书的来反对科举,自然除《儒林外史》再也无人能及,但志在出将入相,而且还想入圣庙,则亦只好推《野叟曝言》去当选矣。《儿女英雄传》作者的昼梦只是想点翰林,那时候恐怕正是常情,在小说里不见得是顶腐败。”[24]周作人还认为《儿女英雄传》“对于女人对态度颇好,恐怕这或者是旗下关系”。
周作人一向反对道学,但对《儿女英雄传》中安学海的形象却表示赞同,说他“通达人情物理,处处显得大方”。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