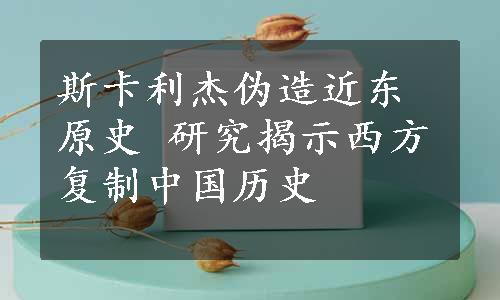
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之一”的斯卡利杰本想“出淤泥而不染”;但却陷得更深,而成为杜撰历史的“集大成者”。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对于现在的寻找古代和历史的知识倾向,(我)发誓彻底鄙视之”;他宁愿冒险犯错,也不想收集那些无根据的古代废物,来填满脑袋。然而,他和他的同仁都只能是倾向于“人文主义处方”(the Humanist prescriptions),去不厌其烦地模仿历史。[14]这特别是指,斯卡利杰最先揭露安尼乌斯(Annius)伪造古埃及和巴比伦,但到最后却又采用之。
启迪斯卡利杰发生思想转变的“灵感”(从而接纳假的古埃及和巴比伦),是文明与历史的“虚幻源头”。对此,属于主流西方的葛拉芙顿教授写道:斯卡利杰没有设法拒绝“真的”波洛修斯(Berosus,公元前3世纪,著《巴比伦—迦勒底史》),他以前视之为假的。没有(莱顿大学)学者指导他,怎么从其大部分内容都是伪造的文献里,找到可信的文字,是什么启迪他的呢?
答案是清楚的和肯定的:16世纪的早期,在荷兰的弗里斯兰附近,一些学者设想了一个“原史模式”(Model Urgeschichte);他们宣称:有三个印度绅士,弗里索(Friso)、萨克索(Saxo)和布鲁诺(Bruno),在公元前4世纪离开故国,师从柏拉图,并与马其顿的菲力浦和亚历山大战斗;然后定居在弗里斯兰。他们驱除土著巨人,建立了格罗宁根(荷兰地名)……在1600年左右,上述荒诞的故事惹火了被斯卡利杰所崇拜的人文主义批评家埃梅厄斯(Ubbo Emmius,1547—1625年),他批评道:弗里索和他的朋友仅是寓言,是源于杜撰的资料。然而,佩特里(Suffridus Petri,1527—1597年)捍卫如此弗里斯兰神话,把它翻译成拉丁文传播;他宣称,古代文献现已丧失,但是大众民歌一如早年罗马和日耳曼的《布兰诗歌》(Carmina Burana),久闻于李维和塔西佗的作品中,即便是正规的历史学家都不具有之(引者按:诸如此类的传说被构想为西方文明的“源头”)。
佩特里主张,即使包含寓言的大众传闻,也不可被牺牲掉;“一个好的历史学家不应该因为是寓言,就简单地弃绝古代,而是通过净化寓言来认识古代。”一句话,口语传统需要批判性地吸收。斯卡利杰了解这番辩论,它试图提炼荷兰的原初神秘,就像斯卡利杰自己试图提炼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重要的是,斯卡利杰本人的反应:他赞扬埃梅厄斯(摈弃传闻),却模仿佩特里(发掘传闻)。以宽容与折中的态度对后者,于是,佩特里推荐弗里索(印度绅士)预示着斯卡利杰接受了公元前4—公元前3世纪的“传奇人物”波洛修斯(“巴比伦史学家”)和曼涅托(“古埃及史学家”)。(www.daowen.com)
斯卡利杰(按照弗里斯兰“原史模式”)发表了“巴比伦原史”(Babylonian Urgeschichte),当此之时,他捍卫它,鼓吹其创作至少就像李维所展示的古代故事那样值得尊重。……这是由神话变形为真事。他使用伪造的和幻想的工具,制作出“真实的”古代近东,将其融入西方传统之中。(Scaliger……used a forger's and fantast's tool to integrate the real ancient Near East into the Western tradition.)
即使这回的伪造者是佩特里,而不是安尼乌斯(Annius:伪造了古埃及史家曼涅托和巴比伦史家波洛修斯的残片),那么,他(斯卡利杰)也是一个伪造者,并且从语言学的知识世界提供了征服性的利器。[15]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