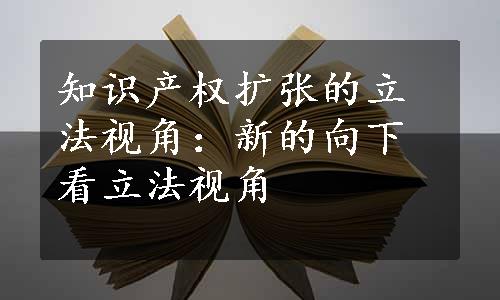
在前文第一编中,我们针对中美两国所出现的知识产权扩张现象,从所涉及的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守法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制度分析,并且对于二者之间所存在的立法动力传递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剖析与勾连,进而概括出:虽然在中美两国,与知识产权扩张相关的本土国情迥异,但两国在推动知识产权扩张的问题上,可以说都表现出了十分积极的立法姿态,以及存在着大致相同的法律与立法观念;而这一切从更深的“源头”上看,是因为双方分享着一个共通的“向上看”的立法视角。
虽然近三十年来,对于推动知识产权在整个国际范围内的不断扩张,“向上看”的立法视角一直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但事实上,该立法视角的局限性也较为明显,面对社会各界有关知识产权扩张的各种质疑,其并未能实现所预期的、理想化的、同时也是基础性的观念性整合。例如,在美国社会,各种批判的声音可谓是不绝于耳,甚至是形成了诸如“知识产权怀疑论”、“反知识产权论”等影响深远的社会思潮;[1]而在我国,如权威学者所指出的,自改革开放以后重建知识产权法制以来,在有关中国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水平的价值判断上,不论是在政界、商界还是在学术界,也可谓是存在着相当广泛的各种争议等。[2]
虽然国内外有关知识产权扩张的争论,不能不说是头绪繁多、异常复杂,但其中最为折磨人的一个问题为:如果说自19世纪下半叶始,知识产权法就已经从某种形而上学的统治转向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制度演化路径的话,[3]那么,恰是在能否实现决策者所期望的功利目标的这个关键问题上,人们的认识较难达成某种理想程度上的共识。如前文所分析过的,就中国而论,虽然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有其理性根据,主要是借此可维持在欧美的商品出口市场,但这并非意味着,就可以不去正视这种政策选择以及利益交换的“代价”,很难否认的是,中国并非是获得了一切利益。即便是对美国这样的知识产权强国,作为知识产权扩张的始作俑者且最为坚定的支持者而言,该扩张究竟给美国的国内经济以及国际竞争力带来了哪些真实影响,至少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看,其实并不存在某个令人信服的最终答案。[4]以上这些疑问提示我们,或许,不论是针对知识产权的制度扩张本身,还是隐身其后的“向上看”的立法视角,都存在进一步予以讨论或调整的必要。
还可以再假设一个罗尔斯式的例子予以更为形象的说明。假如一个非洲的穷人和一个美国的富翁,都处在“无知之幕”的背后,由他们自由想象某种理想的软件价格。并不能排除前者会想象,一套类似微软操作系统的软件会价值1000美元,当然也并不能排除,后者会想象即便是这样的软件,最好是能以盗版的价格来获得,因为软件的复制边际成本几乎是零,更何况,比尔盖茨已经是富可敌国,为什么不能将软件的价格大幅降低。双方之所以会形成和自己的原有身份完全不同的想象,是因为当走出“无知之幕”之时,很有可能,上帝就将双方的真实身份进行了对调,而每一方当然都希望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双方也要考虑到“如果上帝不玩这样的游戏”的情形,那么双方能进行的这第二个想象,其实也就是今天的相关社会“现实”,即那些处于知识经济边缘的穷人,不停地抱怨软件等商品的价格太高,而那些处于知识经济核心的富人,则继续唠叨着侵权该如何根治。
不论上帝如何玩上述的游戏,看似都可以得出:一是某种软件价格是否合理,关键看做出价值判断一方处于什么样的真实社会地位;二是目前的软件价格更可能是不合理的,因为现实中并非是那些穷人,而是那些富人依照他们作为强者的“想象”,在操控着软件的价格;三是就软件的“合理”价格而论,应该是介于上述两种极端情形之间的某种妥协性的价格,并且依据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存在着多种变化的可能。并且,还可以将该分析“推而广之”,针对不论是软件的合理价格其背后起决定作用的版权制度,以及其他同样复杂的专利法、商标法等主要制度,还是整个知识产权法律体系及其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以至于处在更深层面的“向上看”的立法视角,或许都可以进行这样的罗尔斯式的怀疑,这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所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如前文所述,从“向上看”的立法视角的构成来看,其集中表现为:在关注的主体上,主要是那些特定的“重要”的社会成员;在关注的焦点上,主要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以及意识形态的构建;在关注的解释上,主要是在笼统的爱国主义下双方的“各说各话”。而所论的对该立法视角的怀疑或调整,关键是要打破这种既有的“定式”,或者说在横向、纵向两个纬度上都要进行拓展,具体而言:在关注的主体上,除了那些“重要”的社会成员之外,还应增加普通民众以及公共知识分子;在关注的焦点上,除了制度扩张与意识形态建构之外,还应扩展至对其背后的正义、效率、妥协等问题的拷问;在关注的解释上,除了“爱国主义”和“各说各话”之外,还必须在“真实”、“完整”的国际环境下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拟进行的对知识产权扩张的立法视角的研究,由于理论关注的重点被放置在对现实的中美经济关系、国际竞争力消长等经济基础变化的考察,对非重要社会成员和不发达国家等边缘声音的倾听,对知识产权的制度史及权利特色等制度局限的正视上,相较于“向上看”的既定视角,它可被概括为一种全新的“向下看”的立法视角。(www.daowen.com)
[1]曹新明:《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反思》,《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6期。
[2]吴汉东:《中国知识产权法制建设的评价与反思》,《中国法学》2009年第1期。
[3]从近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来看,以19世纪50年代为界,可以大致将该法的演进史区分为前现代法和现代法。前现代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对在该法保护对象中所体现的智力劳动或者是创造性劳动更为关注,智力劳动在当时知识产权法的许多方面,事实上都起到了“枢纽”作用,总体上运用的是古典法理学的语言、概念和问题。但在现代法中,不再把注意力集中在,或者是智力劳动,或者是无体财产本质这些问题上,而是更多关心诸如图书对于读者大众、经济的“作用”等,也就是说,现代知识产权法主要运用的是立法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语言。参见[澳]布拉德·谢尔曼、[英]莱昂内尔·本特利:《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演进》,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页。
[4]如前文所述,美国著名学者波斯纳曾明确表示,迄今对于知识产权扩张的解释,至少是在法律经济分析的学术领域,仍属于一种“最重要”的未竟事业;尤其是,该扩张是否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净”收益,这一点也尚未得以确证。参见[美]威廉·M.兰德斯、理查德·A.波斯纳:《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金海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535页。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