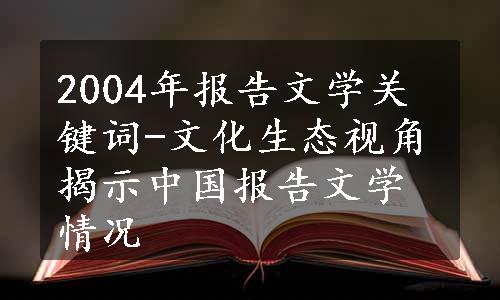
二、2004年报告文学关键词
关键词1:报告文学年
王 晖:2004年刚刚穿越21世纪的时间隧道,学界对于各式文体的创作与批评的年度回眸就已经或正在进行。我以为,这样的回眸最好不要成为例行公事、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而应真真切切地寻找文体年度流变的亮点、焦点和难点,以年度之“一斑”,窥文体整体发展之“全豹”。具体到报告文学,我的总体印象是,尽管这种文体遭遇到2003年底至2004年初“生存还是死亡”的严峻拷问,但后来的岁月证明报告文学仍然拥有良好的存活生态,三大奖的如期开奖就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在2004年里,代表专业水准的第二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体现大众意识的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届正泰杯大奖和倾注政府行为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先后公之于众,形成一股报告文学“旋风”。它们充分显示出当下报告文学文体对社会各阶层的影响力,以及社会各阶层对报告文学的热切期待。如果说,1988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创作震动文坛,形成“后文革时代”第一个“报告文学年”,那么,2004年报告文学大奖的隆重出台,是否预示着又一个“报告文学年”的到来呢?
丁晓原:我非常赞成你持这样的批评态度,在我这里也是一样。我们这次对话的标题,表明了这种价值指向。你指称2004年为报告文学年,我基本同意你的命名,但这需要作出某种界定。如果将它置于报告文学的史程中考量,这样的说法似乎不成立。大家认同的报告文学年是1936年和1988年。但如果“就年论年”,或将它放在新世纪的文学大背景中评估,那么2004年确实可以被视为一个报告文学年。其标志之一就是报告文学三大奖的同年并开。当然,这三大奖还存在着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三大奖之间功能分区不明确,如徐迟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出了专业奖的水准,还很难说。你上面所作的形容,还只是我们的理想。二是有些获奖作品的公认度不够,如鲁迅奖应该是报告文学的最高奖,而实际上一些获奖作品差强人意。同时有的优秀作品则人为地落选了。但是,三大奖本身说明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在既有数量规模,也有品质的可观。另外,我们之所以总体肯定现在时态的报告文学,是因为在文学普遍地边缘化的语境中,报告文学以其文体的独特,以其入世的精神,依然处于影响受众视听、牵引社会关注的某种“中心”。所谓报告文学年,也就是说报告文学作品不仅在文学界内有所影响,而且也在社会获得反响的年份。2004年的一些报告文学确实具有这样的影响力。典型的例子就是何建明的《永远的红树林》和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前者的各界反响,《光明日报》已作过专门报道。后者的影响,据浙江省作协郑晓林说,《中国新教育风暴》等报告文学,成为浙江图书市场最热销的书。2004年的优秀的报告文学大写着现实中国,参与了时代核心主题的建构。
关键词2:跨世纪作家
丁晓原:你现在差不多是一个职业化的报告文学研究者。我不知道你在观察报告文学创作时,有没有一种新人无多的失望。就这两年报告文学获奖作者看,新人只有李春雷、闾丘露薇、左赛春等数人而已,而且他们尚不具有全国性的影响力。2004年有一位写作了《灰村纪事》的作者朱凌,她对于题材的选择把握、对于题旨的思考开掘,都显示出作者写作报告文学的潜力,值得我们关注。报告文学作者后继乏人,这部分地由文体的特殊性造成的。作为一种最不自由的文体,具有较大的写作难度;而且报告文学的写作成本相对较高,在经济中心主义的背景中,年轻人不写报告文学也就可以理解的了。在这样的情势中,报告文学还保持了良好的局面,我们不能不感谢一批跨世纪的报告文学作家。就2004年的创作看,支撑报告文学大局的是何建明、王宏甲、黄传会、蒋巍、长江、曲兰、张雅文等,他们的报告文学从20世纪写到了新的世纪。何建明是其中最为勤奋的作家之一。2004年他有两篇(部)作品可谓本年度重要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在我的阅读视野中,他的《永远的红树林》,以文学颇具召唤力的叙说,在报告文学,乃至在整个文学界,第一次直接、正面、迅捷地表现了我们时代的核心主题,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的时代内容。这篇作品所写的人物及其事迹,包括“红树林”的寓意,无不指向并演绎着科学发展的时代命题。可以说,《永远的红树林》所言说的主题就是我们时代的主题,体现了报告文学作为“时代的报告”的独特价值。另一部长篇“红色经典”《部长与国家》,除一如既往地呈现出作者擅长于宏大叙事的写作风格外,作品还表现出作者对于写作创新的努力。作者在打捞历史故事,还原历史画面时,注意“写出革命领袖人物的人情、人性和人样”。作品的结构也富有动感,将当前情景与过往人事,通过闪回、叠映等手法加以组合,现场感真切。蒋巍也是2004年度的报告文学代表作家。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以《在时代的弯弓上》等一系列立意改革的作品享誉文坛的报告文学家,曾经有一段时间从我们的视野中淡出了。但这两年他又以固有的激情道义重返报告文学阵地。《你代表谁》,题目就充满了报告文学感,获得中国报告文学第三届正泰杯大奖。其长篇《渴》具有显见的题材拓展意义,并且关于水的困境、水的意义、水的解困的叙写、思考令人沉重,让人感动。年末发表的《牛玉儒定律》,及时地报告了“感动中国”的时代先锋,再现了保持共产党人先进性的市委书记牛玉儒的可敬形象。
王 晖:关于何建明,我想多说两句。他的《永远的红树林》是2004年度反映可持续发展这类题材中的一个亮点。这篇记录青年经济学者梁言顺博士从事“低代价经济增长”研究的作品,深切地应和着“科学发展观”的时代主题,其人物描述的视角和方式颇具当年徐迟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对陈景润表现的韵味,它通过书写一个人和他的理论,展示经济增长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性难题,其现实意义不亚于破解“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性的数学理论难题。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擅长于长篇大论的何建明仅用一万二千多字(相当于《哥德巴赫猜想》字数的一半)就将人物的个性简洁有力、生动传神地活画出来,这不仅是作者对自我的超越,在长风日盛的报告文学界,此举也如清风拂面,令人为之一爽。我还特别感慨于作者哲理性思考的进一步深化,我把这看着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逐渐成熟起来的标志。
与何建明相似,王宏甲也是跨世纪作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2004年度出现了大量的触及对学校教育教学及其考试方式的描述,以及对青少年成长环境表示忧思的报告文学文本,其中《没有不成功的孩子》(李振斌)书写了一个平凡父亲在“目标、爱心、恒心和汗水”这一针对性极强的教子理念指导下助子成才的感人故事。《一个中考学生家长的日记》(顾颐)则真切地道出当下应试教育氛围里为父为母的疲惫、无奈与艰辛。而《窃心大盗》(祁建)中对青少年网恋负面影响的调查,《欲说还羞性教育》(曲兰)中对因性教育缺失所造成的青少年之性蒙蔽、性盲目、性羞涩和性犯罪等问题的揭露,《只有一个孩子》(杨晓升)中对独生子女因意外伤害致死的详述,都表达了作家们的深切的忧思。这中间,我以为王宏甲发表在《中国作家》上的《走向新教育》一文有其新气象。作品从特级教师王能智发现和实施“探究式学习”教学法取得成功的个案描述入手,对具有工业化教育特征、以单纯获取知识的灌输式教学为主体的现行教育教学模式提出质疑和批判,呼吁向新经济教育方式转型——因为“对于成长中的孩子,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重要!”个案描述的丰富性及其语言的生动性,使其比作者数年以前所写的《智慧风暴》要更为感性一些,因而也就显得更加灵动可感。
我同意你“新人无多”的判断,不过,有些“新面孔”,我觉得还是值得我们记住的,譬如刘继明。刘本为小说作家,此次他却以51万字的超长篇幅为我们展示出三峡工程在近百年的时空里由伟人梦想化作现实存在的宏大纪实。作者将有关三峡大坝的梦想、论证与论争、生态与战争威胁考证、移民和工程建设五个方面的内容联袂推出,于张弛有度、详略分明、知感交融之中,演绎成对“梦之坝”的全景叙述。可以说,它是目前报告文学界诠释三峡工程的最完全读本——一年前何建明写过《国家行动》,十二年前卢跃刚写过《长江三峡:半个世纪的论证》,但他们仅分别侧重于三峡移民或三峡工程论证、论争等内容的叙述。然而,我更感兴趣的还是作者的创作理念、对描述对象的认知和切入的视角。刘继明说“我所理解的报告文学,绝非是长期以来流行的那类热衷于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穿凿附会和满足公众窥视欲的‘纪实文学’作品。因此,我希望这部书具备一种整体性的思辨力量、较为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浓郁的人文地理色彩;在对真实的历史与现实事件(人物)的把握上,尽量回避那种通俗故事式的表达,而更应该注重言说方式和思想意义上的彰显。”这就使得其文本并非一个世界级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过程的单一性描述,而是成为对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和经济流变的整合式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刘继明无疑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界一匹颇具实力和潜力的“黑马”。(www.daowen.com)
关键词3:检视生活
王 晖:关注举国注目的热点与焦点固然是报告文学作为“世纪文体”所应承载的主要内涵。然而,与2003年相比,2004年缺少诸如三峡截流、抗击“非典”、飞船上天等冲击人们注意力的重要事件。因此,除却上面所说的热点与焦点外,对日常生活的检视和反思就成为这一年度报告文学的一个关键词,这多少表明这一文体关注与再现生活的视野正在逐步扩展开来。在林林总总的书写中,我倾向于推举那些深具人文关怀、主持社会正义、心怀人类良知、善做文明批判的用心之作。因此,我以为有这样一些文本值得注意:一是对婚姻和男女情感内容作描述的,如《天下婚姻》(黄传会)、《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涂俏)、《情感幕后》(石英君)等。黄传会在这部长篇文本中,以共和国三部《婚姻法》的制定、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为线索,串联起50多年来中国大陆公民婚姻恋爱观念流变的曲折历程,以此体现“民众对个人私生活自主权的关注,立法者对个人私生活自主权的重视”的基本理念。涂俏以卧底方式深刻体察了“包二奶”这样一种伴随市场经济出现的畸形婚姻状态,并十分冷峻地揭示出二奶们自虐式寻求“美好人生”的令人心悸的生活内幕和内心真相。石英君则通过中国第一位隐私热线主持人的手记,直击当下人们情感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以此透视时代变迁之风云。二是对医疗及某些流行疾病现状的关注。如触及当下医疗与人伦关系敏感性的《安乐死:情与法的撞击》(熊国英等),描述心外科专家刘晓程以惊人之举关怀心血管病人、震撼中国亟待改革之现行医疗体制的《4万:400万的牵挂》(张雅文),以及揭示乙肝患者艰难的生存现状的《你,“澳抗阳性”吗?》(长江)等。此外,还有关注食品卫生安全的《民以何食为天》(周勍)、关注城镇下岗职工生活的《涅槃》、揭示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与潜规则博弈的《灰村纪事》(朱凌)、直言厕所改革的《厕所革命》(郝敬堂等)、思考交通安全问题的《中国,车祸之痛》(徐江善)、描述北京反扒窃斗争的《京城反扒行动》(宇向东)、再现吸毒贩毒危害和缉毒警察英姿的《毒品凶猛》(张西)、直击海外中国劳工生活的《太阳灼伤的土地》和《幸福的荒漠》(林因等)、追忆领袖和高级干部生涯的《在毛泽东的身影里》(张一弓)和《部长与国家》(何建明)等。
丁晓原:你将“检视生活”,作为指说2004年报告文学的一个关键词,这是十分符合实际的。2004年的报告文学,部分地成为了回到日常生活的言说。一般地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更适合于报告重大现实题材的文体,大题材有时可以产生大报告。2003年的中国可谓大事不断,报告文学对“非典”、“神五”等这些重大题材都作有快速的反映。2004年除了一些重大的矿难等灾害频频发生外,社会整体稳健地发展着。重大题材对于报告文学,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我们并不能说题材绝对决定着报告文学的写作;同时我们对所谓的重大题材,需要作辩证的认知。一些看起来寻常的事情,往往蕴含着重大的报告价值。报告文学并不是大众文学,但是它应该贴近大众的生活、报告民生、体察民情、传递民声。2004年度发表的《民以何食为天》、《厕所革命》、《天下婚姻》、《你,“澳抗阳性”吗?》等作品,就有这样的意味。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在材料的内化处理、在语言表述等方面,应该说还显得有些粗糙,但是以长篇的规模,将“中国食品安全现状”的严峻问题推至读者面前,其题材、立意的价值是颇为重大的。“食”是平常之事,但它又事关着“天”——关乎每一个人生命,也关乎民族国家的命运。而作品所呈示的景象是食品问题“十面埋伏”,防不胜防,大众开始生成某种“食品卫生恐怖”心理。由此可见,《民以何食为天》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话题。通常而言,厕所是难登文学的大雅之堂的。郝敬堂、张红樱两位作者,不仅以厕所为叙写对象,而且竟然冠以宏大的“厕所革命”的题目。只看题目,觉得作者似乎有小题大做、招揽读者的嫌疑,但如果你认真通览作品,便会深感厕所问题其实是一个最人化而又最易为人忽视的问题。说到底,厕所问题是一个文明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民族连温饱之事尚未解决的时候,是根本不会想到把厕所列为需要“革命”的议程的。长江的《你,“澳抗阳性”吗?》,报道的是1.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的生存状态:他们背上的十字架太过沉重,“健康人”视其如洪水猛兽,他们自己也在人面前活得太累。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与周围世界之间筑有一道人为的“墙”。长江的这篇作品表现出对弱势人群的关注与同情。以上所述多篇作品表现出的对大众日常生活遭际的倾心,体现了报告文学作家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的立场与情怀。这种风气值得肯定,并且是需要发扬光大的。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年份,各种纪念文章很多,谭楷的《家乡的事》以视角的独特和选材的自出,成为其中的优秀之作。在作者看来,“深情的颂歌,沸腾在平民的热血中,不朽的丰碑,矗立在百姓的心坎上”,“发生在广安这块土地上的巨变是中国巨变的缩影,也是小平丰功伟绩的组成部分”。作品副题“从一座村庄,几个农民看一代伟人”,此中可见全篇构思。几个小标题“无言的梧桐树”、“邓家老院子”、“牌坊新村的‘老实龙门阵’”、“幺舅的‘好福气’”、“欧阳晓玲之歌”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叙述邓小平的“小故事”及其家乡的大变化。以百姓视角观照伟人,将伟人置于日常生活中反映,这样的写法对于同类作品的写作是有启示意义的。
关键词4:报告文学病
王 晖:2004年度报告文学在日益强大的全媒时代艰难前行,能有所作为实属不易。但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仍不能不再次重申,目的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在不少文本中仍然存在带有浓厚的小说式虚构与想象的描述,此现象在某些大力推崇报告文学的知名期刊中也未能幸免;第二,篇幅冗长、不加节制、堆砌个案、不善剪裁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三,对一些重大的社会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缺乏表现;第四,从某些知名期刊2004年全年所发作品来看,其登载的“报告文学”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亚流文学”,甚至可能连“文学”都谈不上,充其量是些为企业或个人作粉饰的文字广告而已,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愤懑和悲哀。以上这些近乎老生常谈,但对报告文学而言,如不加以克服,则会有诸多不利。
丁晓原:我对你上面列举的几个问题,颇有同感。在我看来这些问题似乎已经成了有害于报告文学健康发展的痼疾。虚构是报告文学的天敌,故意地编造无疑颠覆报告文学文体的存在,目前自觉或不自觉的臆想式“报告文学”并不少见。脱离内容实际的注水作品,也有悖于报告文学的文体规范。报告文学是新闻文学,新闻性其中就意味着快速报告和快速阅读。呼吁精短报告文学成了2004年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可见此类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了。我阅读2004年报告文学,在为这一年创作新收获感到兴奋的同时,又为本年度报告文学整体上存在的平面化而遗憾。平面化,具体表现为作品故事(材料)多而思考少,缺乏作家主体对报告对象的心灵内化和思想穿透,很少有作品带给我们深度的震撼;一方面作品题材的跟风趋同,如写三峡(移民)、教育等作品较多,而另一方面,一些为百姓关注也联结着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的尖锐题材却乏人问津。
王 晖:你所言极是,譬如“反腐”。尽管它仍然是2004年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中的关键词,但报告文学中有分量、有深度、有震撼力的作品仍显匮乏。描述河北程维高浮沉的《失控的权力场》(秀灵)和披露吉林李铁成受贿案的《卖官记》(文辛),是其中可以一提的文本,但它们大多有这样的通病,即仅止于案件叙述,而缺少对人物言行及事件深层内涵的发掘,视角的独特与话语的精彩更难以与几年前杨黎光所作的《没有家园的灵魂》相比。
丁晓原:我想,这正说明报告文学作家在承担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方面还有所不足。报告文学家的胆识是以他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担当为前提的。就这一点说来,2004年的报告文学还远不如央视的一些新闻主题性节目,敢于突入现实前沿进行富有勇气和识见的报道和评说。一般来说,国家主流新闻媒体需要更多地遵守意识形态管理的潜规则,言说的自由度相对要小一些。而报告文学作家则可在不自由的文体中,拥有较大的选题的自由,特别是表达深度思考的自由。如报告文学作家认同作如此观,那么倒是应该反求诸己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